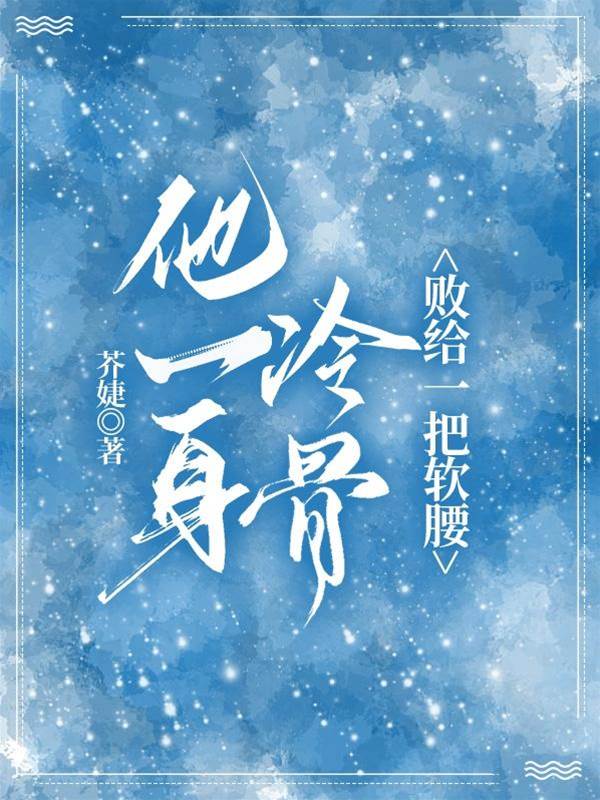《獨寵舊愛·陸少的秘密戀人》 你儂我儂,忒煞情多【5000】
t市霧氣瀰漫,大雪終於停了,整座城彷彿籠罩在冰雪之中,朦朧冷清。
跟阿笙同往杉磯的人前不久打來了電話:跟丟了。
陳煜說:“先生,我已經讓他們改道去韓家了。”
醫院裡,陸子初怕驚父親,拿著電話走出病房,一陣靜默。
半晌,語調輕淡響起:“就這樣吧!”
哪樣?他沒說個明白,陳煜也沒問,時間剛及凌晨,陳煜一通電話打來,雖說沒驚陸昌平,卻驚醒了韓淑慧。
韓淑慧夜間睡著,原以爲陸子初已經回去了,沒想到一睜眼還在病房裡,待他重新回到病房,忍不住開口道:“你爸爸有我照顧,沒什麼不放心的,快回去休息吧!”
陸子初站在*前,看了父親一會兒,這才拍拍母親的肩,轉朝外走,路過一旁的傢俱桌案時,腳步微頓,那裡放著兩個玻璃瓶,其中一隻裝著黑巧克力,另外一隻裝著五六的小星星。
誰送來了的?回頭看了一眼韓淑慧,正幫陸昌平汗,也便收回目離開了。
……
驅車回去的途中,陸子初給阿笙打電話,聽到的聲音,懸著的心這才放了下來。
阿笙言語異常,陸子初沒聽出來,因爲前方傳來一陣哭聲,陸子初思維片刻停滯,凝神去,凌晨送喪,快趕上拍鬼片了。
每個人的手臂上都纏著黑紗,還有人在腰間紮了麻布腰帶,煙火齊鳴時,陸子初把車停下來,了眉心。
果真是生死無常。
阿笙在電話那端也聽到了這邊的哭聲,只不過很微弱,問陸子初:“誰在哭?”
生死這種事太晦,陸子初找了藉口,好在隆冬風聲嗚咽和哭聲差不多,就這麼敷衍過去了,又淺聊了數句,不問歸期,不問在哪兒。
Advertisement
他說了,只要回來就行。
沒有回到海邊,記者會結束後,已經讓薛阿姨親自去海邊把他和阿笙的東西全都帶到了風景別墅。
回去已經是凌晨兩點多了,驚了家裡的傭人,陸子初眼見他們穿著睡,打著哈欠站在家門口迎接他,蹙了眉:“都去睡吧!”
傭人大都散去了,薛阿姨接過陸子初外套的時候,給他倒了一杯水,簡單詢問了陸昌平是什麼況,聽說沒事,寬了心之餘,薛阿姨轉上樓幫他放洗澡水去了。
薛阿姨放好洗澡水出來,見陸子初已經喝完水上樓,薛阿姨叮囑了幾句,原本要轉離開的,但走到門口忽然想起一事來,又轉走到了*頭櫃旁,拉開屜取出一件東西來。
“下午我收拾顧小姐服的時候,在外套口袋裡發現了這個。”薛阿姨把一隻u盤遞給了陸子初。
陸子初接過來,舉到眼前看了看,u盤這種東西出現在任何人上都不奇怪,但阿笙隨攜帶……奇怪。
……
這趟杉磯之行,沒有人是真正的贏家,全都輸的徹底。
“韓愈”這兩個名字曾經簽署在各大文件尾頁,每一次都是沉穩利落,唯獨這次,簽署落定,換來的不是名利喜悅,而是撕心裂肺的痛。
有東西破而出,疼的不過氣來,過往歲月,曾經近在咫尺的幸福剎那跌落深淵,摔得碎骨。
除了把緒掩藏在蒼白的臉間,韓愈似乎再也找不到可以宣泄的方式。
緣盡緣散,有些事,錯了一瞬間,也便錯了一生。
這次是真的緣盡緣散了,斬斷,彷彿早就設定好的結局,婚姻起步杉磯,止步杉磯,滄海桑田之後,誰也沒能全而退。
Advertisement
太害怕把再次進死衚衕,孩子因他間接早夭;顧清歡因他間接死亡;因他間接去世……這些人裡面太怕有一個。
他用最慘烈的方式走進霾,此去經年,是人非,方纔醒悟,他一直以爲自己可以控制一切,凡事收斂小心,銳不可擋,殊不知唯一擺不平的就是:。
,可以給,但不能要。
杉磯黃昏散去,有一種乾乾的冷,一同走出來,明明很近,靈魂之間卻已離得那般遠。
近距離呼吸,千言萬語哽在間,韓愈出口竟是艱無比:“有什麼話要對我說嗎?”
“沒有。”
大街上人來人往,冷暖喜悲,兀自會。於他人,無關痛。
“我有。”韓愈沉默一陣,只默默道:“這輩子沒機會在一起,下輩子只盼最先給你溫的那個人是我,可以讓我爲你邊的誰。”
“……”阿笙靜靜的看著他,不說話。
那雙眸子散去了霾,塵埃褪盡,所有的晦全都紛紛化開,這一天,似乎等了太久太久……
韓愈移開眸子,深吸一口氣:“在杉磯逗留*吧!一起吃頓飯,明天我送你回國。”
語氣小心翼翼,深怕會拒絕一般。
街道上,顧笙眼眸漆黑冷寂,烏潤潤地彷彿浸潤在溫開水裡,著說不出的沉靜清。
“天總會亮的。”
阿笙嗓子啞了,但落風中別有一番從容隨。
他和和平坐下來吃頓飯,又算什麼呢?面對他只有痛,他面對又何嘗不是傷?
何必。
風吹了的長髮,阿笙裹大,朝街頭走去。
韓愈看著的背影,彷彿所有喜悲全都爲了過往雲煙,那些癡纏不休的過往,那些無法訴說的淚,轉瞬間在杉磯上空灰飛煙滅。
Advertisement
那天黃昏,頎長拔的男人,大步追上子,在對方愕然的神下抱著,右手扶著的後腦向他的口。
他說:“顧笙,韓愈這一生虛虛假假,連他自己也看不清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但他你是真的。”
時間停止了,空間凝結了,蠱人的話語從他裡道出,男子面徹底撕裂,出眼眶,滾燙的淚就那麼砸落在了阿笙的脖頸。
他說:“我不會再傷你,但此生不見……我做不到。”
他曾經出手,把安放在掌心裡,後來某一天變了一隻鳥,長出了翅膀,忽然就這麼飛走了……他不了。
就這麼被他摟在懷裡,這個男人有著英俊冷漠的臉龐,爲人事不留餘地,卻在面對前妻時眼神深痛。
路上有撞見,笑笑走遠了。
這對大概以爲他們很恩,殊不知此生都不會再在一起。
被他環抱的子,靈魂顛沛流離太久,已經很有人能夠再帶給毫悸,心寂靜。
……
三樓室,陸子初給自己倒了一杯水,這才彎腰把u盤好,待他走到沙發前坐下,巨大的屏幕上緩緩展現出最清晰的畫面。
——年輕子,神恍惚,穿著長和帆布鞋坐在椅上,斜斜的靠著門框,閉上眼睛時,沒有眼淚。
那水最終沒有送到陸子初的邊,被他放下了。
……
疼的睡不著覺,輕聲喚:“子初,子初……”
韓愈從書房走出來,手向的膝蓋,幫把一點點拉直。
在*上慢慢睡,姿態平靜。
月照在*上,他從背後抱著,把臉在的背上:“我是韓愈,不是他。”
Advertisement
……
他送給了一束花,把花別到漆黑的髮邊,對著鏡頭無聲微笑。
單薄的,警惕的眼神,但很。
……
那天,他在廚房裡做菜,也不知道在客廳裡發生了什麼事,急著了一聲:“阿笙——”
韓愈手被菜刀割傷了,頓時流了出來,畫面切換,把他的手指含在了裡,看著他的目疼痛而溫暖。
……
陸子初的眼神,彷彿海洋中漂浮的孤舟,似乎隨時都能沉沒海底。
不看了。他是這麼告訴自己的,但眼神卻僵在了屏幕上。
沙發上,韓愈辦公的時候,蜷著,枕在韓愈上,宛如孩子般,他把毯蓋在上,俯親吻的脣時,擡手環住了他的脖子……
陸子初定定的看著,流涌上腦海,以至於滿目猩紅,有一戾氣似乎到了極限……
那夜,順手便可拿在手裡的水杯“砰”的一聲狠狠砸在了屏幕上,迴避的過往那般真實,讓人不過氣來。
拔掉播放一半的u盤,揚手一揮,吞沒在了漆黑的夜間。
那u盤,幾日前阿笙沒勇氣看完,到了他這裡,更是不願多看上一眼。
獨自走到臺上,天空泛著濃濃的白,陸子初全的力氣竟支撐不住的重量。
他看著白茫茫的樹林,寒風吹打在他的臉龐上,一片生疼,心裡更是酸煎熬,忽然意識到這座龐大的城市現如今還在沉睡之中。
腦海中出現了的臉,說:“子初,我是你的。”
陸子初忽然清醒了,男人上一個人,不管再如何聰明,行爲舉止有時候都會變得尤爲簡單。
他在前一秒扔掉了u盤,卻在後一秒拿著手電筒,凌晨時分艱難的尋找著。
那麼極力藏,不願他知道,若是回國後發現u盤不見了,難保不會多想。
這一找足足找了兩個多小時,甚至驚了保安也過來幫忙找,人人都以爲那u盤裡面有著陸氏公司最重要的文件,誰能想到不過是滿滿的心傷。
是什麼力量支撐一個男人在面前一再卑微退步,陸子初尋找u盤的時候,把所有的淚全都重新吞到裡,耳邊反覆迴響的不過是的繾綣之語。
【你儂我儂,忒煞多;多,熱如火;把一塊泥,捻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碎,用水調和;再捻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
這詞果真有療傷功效,念得多了,心也就平靜了。
“先生,您看這是不是您要找的u盤?”
不遠傳來保安的聲音,u盤落他的手中,他無聲握,似是累了,扶著雙膝緩緩蹲在了地上,卻是良久都沒有再站起來。
躺在雪地上,看著灰濛濛的天,陸子初角有了最淺淡的微笑。
“過去不重要,不管發生什麼,我們都要永遠在一起。”
一句話,比雪花飄落還輕,裹進寒風裡,然後徹底消失不見。
……
韓淑慧沒想到陸子初會那麼早就來醫院。
“回去沒睡覺嗎?怎麼氣這麼差?”韓淑慧關心問。
金融界力大,更何況陸子初還要掌管陸氏那麼大一個公司,連續好幾年都不曾出國散過心,就像被事業麻痹的人一樣,常年無休假。
有人說他是勞碌命,只有親者方知,他這麼近乎自的工作,跟耗損生命沒什麼區別。
“睡了幾小時。”他不願多說,目無意中落在一旁的桌案上。
比起巧克力,陸子初更興趣的是另外一隻玻璃瓶。
摺疊的小星星塞滿了玻璃瓶,五六,很漂亮,當然……多有點稚。
年人是不會花費心力做這種事的,但對方很有心,不僅是陸子初,就連韓淑慧也覺到了。
韓淑慧給陸子初倒了一杯水,見他在看那兩隻玻璃罐,就解釋道:“放在門口,都是護士拿進來的,也不知道是誰送的。”
韓淑慧起先疑,拿給陸昌平的時候,陸昌平也覺得有趣,就擱在了房間裡。
吳奈這時走了進來,剛好聽到這句話,拿著病歷夾,好奇的瞄了一眼那罐小星星,忍不住笑了,打趣道:“依我看,送這些東西的人,可能是陸叔的慕者。”言罷,同的看著韓淑慧,“慧姨,雖說我陸叔人到中年,但魅力不減,出去一趟,依然可以把小姑娘迷得神魂顛倒,你可要小心了。”
猜你喜歡
-
完結336 章

大叔,愛你蓄謀已久
從一開始程安心裡就清楚任景西愛上誰都不會愛上她,可卻還是無法自拔的為之沉淪掙扎,但夢總有醒的那一天。 就好比大學畢業典禮后那因醉酒而不該發生的那一晚。 後來,任景西說他要訂婚了。 意料之中,情理之外。 可程安不是一個好人。
61.3萬字8 269187 -
完結2217 章

壞壞小嬌妻:夜帝請躺平
天哪!為什么乳腺科會有男醫生! 在看見臨窗站著的那個大帥哥的時候,林菀感覺自己快暈過去了——嚇得! “這位小姐,你還站著干什么?到你了,脫吧。” 脫…… 林菀傻乎乎地看著他。 “不要讓我再說第三遍,脫。你不脫,我怎么檢查?” OMG!要讓男人摸自己那個地方,這也太太太…… 十五分鐘后,林菀紅著臉從醫院跑出來,哭了,第一次親密接觸,就這樣獻給了毫不認識的醫生。 讓她更沒想到的還在后面,這個男人竟然是……
405.9萬字8 34085 -
連載2011 章

厲太太有點甜
一場鬧劇,養父一家以還恩情要挾她代姐嫁給雙腳殘廢的厲大少爺。聽說他對女人沒興趣,這樣只要她完成任務就能完美退場了。可是,誰來告訴她,白天寵她入骨,晚上卻化身為狼的男人,真的是外面說的不近女色的閻大少爺嗎?還有他的腿……是什麼時候好的?最後,她抓狂:「厲先生,請離婚。」他步步將她逼到角落裡,靠近她耳邊:「老婆,你答應要照顧我一輩子的,可不能始亂終棄。」
373.3萬字8 39084 -
完結420 章

替補老公逼上門
三年婚姻,宋風晚被丈夫和妹妹聯手出賣。 所有人都以為她會就此跌入谷底。 不料她轉頭就甩出證據,不僅腳踹渣男,手刃賤女,還遇到那個傳說中冷酷如閻羅般的商業帝王傅寒崢。 月黑風高夜,她一步步逼近,對他笑的嬌軟而魅惑:「乖,幫姐姐一把,姐姐養你」 從此,原本被人唾棄的私生女搖身變成了女首富,追求她的人從城頭排到了城尾,就連不要臉的前夫也出來求複合。 正當宋風晚拄著下巴考慮要選哪個好的時候,傳說中如閻羅般冷酷的傅寒崢終於站出來:晚晚�
73.5萬字8 7555 -
完結16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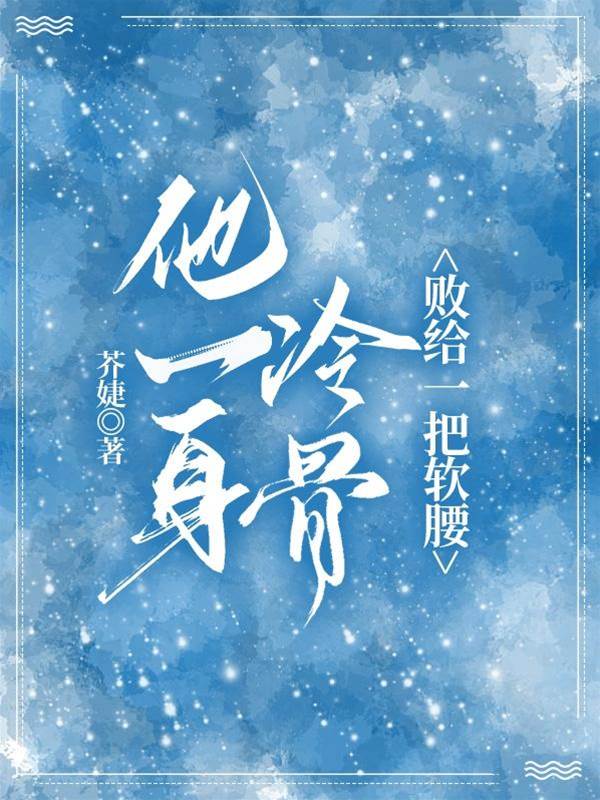
他一身冷骨,敗給一把軟腰
(雙豪門 先婚後愛 強強聯手,白切黑女主vs忠犬型霸總) 傳聞南家三小姐攜肚逼婚,傅二爺不甘被拿捏,打著去母留子的主意。 殊不知,南三小姐也是一樣的想法。 滿身鋒芒,眉骨裏寫著冷硬的傅二爺帶人殺上門。 南笙一把細腰,纖若春柳,穿著素色旗袍,笑意溫婉,“二爺,這婚,你結嗎?” 傅二爺:“……結!” 後來,傅二爺求了一枚平安福 ——願吾妻笑意燦然,母子均安,歲歲無憂。 再後來,傅二爺吃醋,氣的半夜暴走,跑到街上和南笙家人打電話告狀,滿臉委屈。 “這些男人哪有我對她好?!” “我有錢,長得好看,還會疼老婆,她為什麼還要看外麵的野男人?!看我還不夠嗎?” …… 婚後第一天,傅墨言麵容陰鷙,難掩嫌棄:“她不是我老婆!” 婚後第一周,傅二爺怒到極致,“我傅墨言就算是瞎了眼,也不會喜歡一個有三個未婚夫的女人!” 婚後第N天:傅二爺勾著南笙的腰,又纏又膩,“老婆,寶寶,醫生說現在是備孕的好時間,我們什麼時候再生一個兔寶寶?”
29.9萬字8 96521 -
完結225 章

言少別作了,明小姐她又去約會了
【雙潔 骨灰級追妻 禁忌】白日裏她是他的秘書,夜裏他跟她是一個屋簷下的危險關係。他遊戲人間,風流薄幸,對她隻有報複,永遠都不會愛上她。三年期滿,明予打算結束這段荒唐的關係。可男人卻將她強勢壓製,“予予,當初是你先招惹我的。”後來,他要與別的女人步入婚姻殿堂,他以為她會鬧,甚至搶婚,卻怎麼也沒想到,她頭也不回地離開了。離開言蕩的明予一躍成為所有人望塵莫及的明家大小姐。有人問起她對言蕩是否餘情未了,她唇齒嘲諷作者:“浪子回頭這種戲碼,早就不流行了。”他原以為她隻是在跟他鬧,直到親眼看到她跟當紅男模回了家,燈光熄滅,她整夜都沒有出來。言蕩差點死在那個雨夜……
46.8萬字8.18 1808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