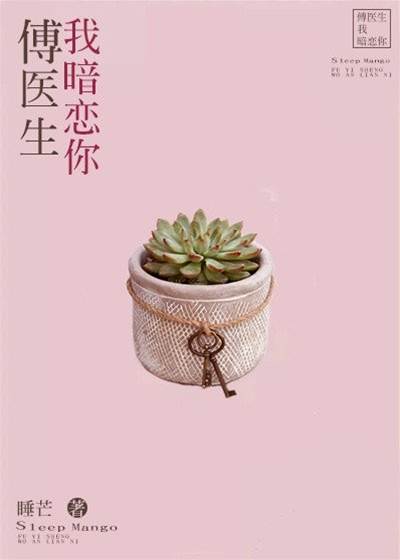《我是卷王穿越者的廢物對照組》 124
“爲什麼這麼問?和累也許無關。”
謝無熾在這片空的寺廟裡,四下張。
殘跡磨滅。時書:“我覺得,你從旻區回來後,天天忙著整軍,修築武備,收割糧食歸倉,一直不太開心。”
四壁除了纂刻經文,還有異聞傳說。謝無熾不答反道:“這面牆壁上,記錄著這樣一個故事:某個王朝爭權對抗時,一位廢太子的後人被徵召宮爲了監國攝政王,夙興夜寐,誠心爲民。”
時書靠在石椅上:“怎麼了?”
“這攝政王患眼疾,一旦憂勞甚劇便會失明。但後來異族侵,攝政王仍然親征戰場,保家衛國,與人同舟共濟。只是得勝之日,累到眼疾復發,卻被臣迫害,搶了功勞不說,還誣陷他要造反。”
時書:“哦?後來呢?”
“後來,他雙眼失明,在寒冷的異地逃亡,隨軍的髮妻帶他四求生,吃過糙饅頭,也住過最簡陋的客店,還藏在別人府邸中靠妻子賣畫謀生,嚐盡心中苦楚……所以再與軍隊匯合後,開始了復仇之路。”
“接著,他造反功,當上了皇帝。”
故事講完,謝無熾轉開視線。
時書盯著壁畫上的繁字:“這故事爲什麼記錄在寺廟裡?”
“他造反前在佛堂誦經數月,得到天命,所以能。因此記錄。”
“……”
一陣沉寂,謝無熾著佛像,一素淨的長袍,迎風獵獵,不知道在想什麼。
“佛像仁慈,普度衆生,可這寺廟恰好確實是鬼怪最橫行。”
謝無熾步履徘徊,回到時書旁:“這攝政王得位溫和,和平政變,一是他統高貴,二是攝政數年早在朝中縱人脈,進京城時舊故親自開的城門。但除此之外的改朝換代、權勢轉移,會異常腥。”
Advertisement
時書心中,慢慢明白:“你……”
謝無熾眼底映著煌煌神佛低眉的凝重和素淨,沉默的仁慈,在泊中匯:“驚濤駭浪的狂瀾涌起,幸運的捲者能乘坐浪頭,不幸的人則被水淹死。”
“這場滅世的洪水,很快就要來了。”
-
時書被抱著回到行轅大府門,睡意朦朧中和他說話:“謝無熾,你知不知道,我很喜歡去屯田的村落閒逛。”
“爲什麼?”
時書:“因爲每個人都在幹活兒,修房子修院子挖土。和舒康府的大疫,大盛府的雪夜,還有狁州的山海都不同。在那些地方走來走去,開闊敞亮,我心很好。”
謝無熾正他的手,聽到這句話,頓了一頓:“時書,這三年,你也到很多創傷,是嗎?”
“我不知道……”
時書困得無法思考,振作道:“但如果和你一直待在這裡,我準備在這片田地裡奉獻我的青春——”
話沒說完,謝無熾頭低下去,和他額頭相抵:“乖寶寶。”
“好寶寶。”
“小狗寶。”
時書哼了聲:“我纔不是狗,我不玩這個。”
謝無熾深的眸子看他,出微笑。時書被親了好一會兒,親懵了,捂著脣。
時書:“你……”
謝無熾額頭抵著他:“寶寶。”
-
接下來的幾天,軍營中爲兩城收割的事奔忙。謝無熾去了前線幾乎半個月,指揮和安排事務。
勸導異族歸義於王朝,可謂大功一件,軍營和軍之間波譎雲詭,暗流洶涌。而普通士兵並不知道皇帝的任命,聽到角鼓聲便衝戰場廝殺,軍大部隊往界河旁靠近,有人從一系列行爲中管中窺豹,猜測到割城池正在進行,軍營中洋溢著沸沸騰騰的喜氣。
Advertisement
連綿不絕的黃泥道路上,時書剛從屯田地回來,安置好新的流民累了一整天,杜子涵在旁:“突然想起來,謝哥多久沒回來了?”
時書:“半個月?”
“什麼人哪這是,讓你一個獨守空房。”
時書看他:“你半夜來找我出門,爬樹摘果子,烤魚烤,不是說幸好他沒在嗎?”
杜子涵:“我只是提醒你,謝哥回來了不要說這些事。”
“……”
兩個人上灰頭土臉,恰好途經溢出溪流,杜子涵去洗手,手掌心的繭子被磨得通紅:“流民越來越多了,中楚府那些百姓起義稱王,流民就往燕州逃過來。天天打灰幹活的,不知道讀的是土木工程。你也差不多。”
時書:“沒辦法,人總不能一輩子不幹活不工作。”
杜子涵看他:“能。人能。”
“…………”
不是。時書頓了一下,也到水坑裡把手上的灰塵洗乾淨,這時候,旁路過幾個醫藥局的人,弓著腰在河邊清洗草藥,被飄揚的蘆葦擋住了半邊子,聊天聲不近不遠傳過來:“我聽說,平將軍的銳鐵騎都開拔去了界河,我看這收復永安府和部府不是空來風啊!”
“這等機大事,你怎麼知道?”
“我前幾天給中軍帳外那些幕僚看病,偶聽他們閒聊到的。還聽說,東都的太監急得跳腳,說國丈老爺的軍隊還沒到,收復山河的不世之功怎麼讓謝將軍獨吞了?簡直豈有此理,哈哈哈哈!”
“你聽到的還真不。”
“可不要出去說啊。東都那羣吸蟲,就知道不勞而獲搶功。要真有其事,謝將軍幹得大快人心!”
“……”
時書把手洗的白白淨淨,慢慢目睹兩個藥醫離去:“謝無熾在北軍的名聲,沒得說——回去了!”
Advertisement
杜子涵:“你老公今晚不在家,不然到仇軍營睡去?”
時書思考了一瞬,懶洋洋笑道:“可以啊,睡大通鋪很不錯,晚上一大堆天可以聊,就是最近降溫,後背靠著地乾冷,睡著太冷了我去!”
“這麼著才暖和吧?那我們找宋思南。”
“走走走。”
時書直起腰,忽然想起了一個溫很高的人,一到冬天靠著他睡覺就暖和。但這個人,最近忙著大事,除了例行給他寫信,倒是沒什麼聯繫了。
“怎麼還不回來……”時書嘀咕出了聲。
“駕!籲!”眼前忽然出現一匹快馬,正在邊走邊查看,見到時書猛地勒住馬繮繩,跳下馬來:“二公子!小的找了半晌,歸義的宙池王一路顛簸到咱們這兒來了,謝將軍讓二公子易裝,速去大營門口接人!”
時書:“我哥回來了???”
“是!謝將軍”,時書轉頭看杜子涵:“那什麼,我陪個人——”
杜子涵出個“我都懂”的表:“回去吧,今晚的大通鋪了你照樣溫暖,你趕去履行你的職責吧。”
什麼職責?陪謝無熾睡的職責嗎?
時書:“哎,子涵怎麼說話呢?”
時書一邊擡手想和他說個一二三,表示自己不那麼重輕友,但雙已經準備跑路了,指著他邊說邊後退:“我警告你不要誹謗我。”
杜子涵痛心疾首:“你看看你,被他玩的跟狗一樣!”
“…………”
不多說,跑路。
時書哪管這麼多,翻騎上馬朝中軍大營疾馳而去,心跳到了嗓子眼。一回到大營,立刻換上更嚴肅的禮服,和其他人一同在營門等候這支勝利之師。
北方秋天轉瞬即逝,天邊黃雲漫漫,連天衰草。正式外場合中黑茫茫一片的武將和衛兵,氣氛肅穆凝重。遠遠看見天際盡頭顯出旗桿,接下來是一匹一匹的駿馬,如螞蟻一般陳列。
Advertisement
在他們背後,儀仗隊兵馬綿延不絕,到有人探頭探腦觀看。
時書也在觀,忽然。出現了一襲拔的影,謝無熾披狐裘,一馬在前踏雪凌霜,姿極爲持重森嚴。旁棗紅大馬坐著的正是宙池王。同時諸多旻人軍馬被北軍引領而去,場面紛紛。
時書喜悅有加:“謝……”
歸順的異族首領宙池王下馬,對他納頭便拜:“多謝二公子言而有信!”
“快起來快起來,這是你和家兄就國事做的商議,與我無關。請進去坐。”
宙池王後,一素的元觀跟在後:“二公子……”
時書:“你也請坐,你們一家人的奴籍我哥勾銷掉了,從今以後是自由之,接下來的事,但看你們的造化了。”
元觀點頭,眉眼幾分不足之癥的虛弱。軍營響起簫鼓之聲,擊打雅樂,迎賓宴會正式開始。
衆人魚列進宴席,時書等到謝無熾的角過旁。好長時間沒見,謝無熾上染了硝煙氣味,和他沒說幾句話,便被衆人簇擁坐在軍帳最前段的位置飲酒,一清貴鶴氅,神沉靜端重。
時書早習慣他在人前慾的模樣,從來不給人砸場子,也明白當前場合的嚴肅。
“這次共襄盛舉,玉歸義之事,全靠謝將軍主持大局。吾等蕞爾蠻邦,歸順於景軍麾下,不勝榮幸。小王敬謝將軍一杯……”
“……”
酒席上,一片歌頌謝無熾英明神武之聲,謝無熾則淡淡地禮讓道:“仰賴陛下聖明,纔有如此事。”暫時不與朝廷爲敵。
正常的社場合。時書雖是元觀牽頭歸義大事的主要原因,但三兩句話帶過,衆人忙於奉承有實權的謝無熾。場之事,歷來如此。
時書酒到中途,只覺得無聊,見周圍沒人看見,摘下一枚葡萄往謝無熾酒杯裡扔去。
“咚~”
謝無熾掠開眼皮,時書俊臉上淺笑,對他彎了彎細長的手指。謝無熾緩緩拿起筷子,撿出酒杯裡的葡萄,吃了。
時書:“啊?真吃了?我倆談說還是一如既往的噁心。”
謝無熾不說話,明顯意味著,比這噁心的還有。
“……”
將軍、大員、政要口含天憲,面上沉穩地對話。時書吃了一會兒便已酣飽,心想:“這宴會場面,跟電視劇裡居高位的聚會一樣,也算是見世面了。不呆了,回營帳了。”
時書率先回了謝無熾的起居帳,夜昏黑,忽然聽到馬匹甩鼻子的聲響,走出門去。
謝無熾在一陣夜風中走來,旁兩匹高頭大馬:“走。”
終於獨。時書好奇:“去哪兒?”
“帶你看看北軍的大營。”
“當然可以了。不過謝無熾你剛回來,也不說和我敘舊,”時書翻爬上馬,“直接就帶我去——啊——”猛的一聲慘,馬匹已被催,在夜風中狂奔。
涼風霎時吹了滿臉,時書勒馬繮繩:“幸好我弓馬嫺,不然被你嚇暈了嗚哇哇!”
兩匹馬在前,護衛在後,踏著秋霜一路往燈火通明的營寨中奔去。今日犒賞三軍,畢竟收回了永安府和部府,何等幸事,眼前的木柵上桐油裡火沖天,反在士兵的盔甲上,映照著一片喜氣洋洋。
謝無熾:“這是北軍大營,嫡系控鶴軍一部分駐紮在燕州,其他的駐紮在各軍事據點,屬於北軍的銳部分。”
時書:“我知道,銳鐵騎!士兵嚴格考覈才能隊伍,軍紀和戰鬥力都非常強悍。”
馬匹繼續往前,馬蹄踩著黃泥水,時書眼看越來越悉的一路,馬蹄踩著黃泥水:“這不是找宋思南的路嗎?”
“沒錯,仇軍營就在這裡,練兵一年多,騎兵步兵和弓兵都有。”
時書沒明白他怎麼突然帶自己看兵,冷風吹到耳頸裡來,不過很難得夜裡和謝無熾出門,走過這一路綿延的軍寨,心倒很不錯。時書大聲道“駕!”,馬蹄在火中肆意地奔跑,很快離開了仇這裡。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