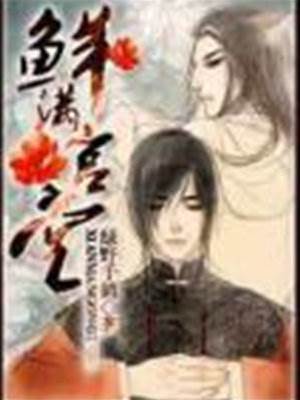《我是卷王穿越者的廢物對照組》 17
煨在鍋裡,醬咕嚕咕嚕冒泡。
染醬油紅,香氣四溢。
紅燒下鍋,還燉了土豆排骨,謝無熾道:“現在不當和尚了,可以大塊吃大口喝酒,你多吃點,看看能不能長。”
時書一下被他搞得不知道說什麼好,等盛上飯上桌,悶著頭吃不說話。
吃了一口,又一口。
一筷子,又一筷子。
謝無熾:“對你好點兒,就老實了。”
“……你會不會說話。”
完,見謝無熾放下筷子,在屋檐下的小桌旁,側頭去看桃花樹林的濃綠繁蔭,神自若。
算了,這沒法噴。
***
在流水庵的幾日,都是收拾院子,拔除雜草,不多久,這房屋也算有模有樣。
沒幾日世子宴請府的門客喝酒,名頭說是賞柳,其實是慶祝前幾日“滅佛”拿到軍餉,他在陛下跟前了稱讚,在朝廷羣臣眼中也一改廢世子印象,風無限。
“哇!好熱鬧好豪華……”
時書驚歎。
他的席位和謝無熾同列,桌上擺置著燒燒鵝切牛水果拼盤,時常有人到席位前來。
“謝兄,初來世子府,以後大家就是好朋友,來喝一杯喝一杯!”有人說。
“客氣了。”謝無熾將杯中清酒飲盡。
這不飯局嗎?
時書對飯局可沒興趣,裡塞著牛乾,正嚼著,那人又笑著轉過臉:“這位小公子,在下也敬你一杯。”
時書:“……你好你好。”
該死,我們青大學生就是不懂拒絕。
喝完,等人走了,時書才問謝無熾:“世子府的人這麼友善?”
謝無熾垂眸:“都是久混場的老油子,場自有場的規矩,無利不起早。這羣人目前不清我的背景世,但世子倚重,恐是把我當新貴,纔來打招呼。”
Advertisement
他提醒時書:“收起你那副小狗眼,看誰都是好人。”
時書:“……”
“你纔是小狗眼。”
被當謝無熾的弟弟,別人敬他的酒,講禮貌都把時書一起敬了,時書喝一口清酒便耳朵紅,膝蓋頂謝無熾的:“謝無熾,我不想喝酒。我只想好好吃飯。”
“不會喝酒?”
“我爸媽不讓我喝,況且酒有什麼好喝的,又辛辣又苦。”
謝無熾:“呵,你爸媽把你養的很安全。但這種社場合,酒有酒的好,觥籌錯也有它的意義。”
又有人來舉杯邀請,謝無熾替時書擋了回去,袖子拂開:“家弟年紀還小,暫不飲酒。”
觥籌錯,舉杯對飲。世子府奢靡,大殿巍峨高聳,檐角相疊,漢白玉的欄桿曲折。竹管絃吹拉彈唱,也有伶人長袖善舞,在舞臺的中間蝴蝶一樣翩翩而來去,花紅柳綠迷人眼。
時書:“頂級權貴家庭……周家莊種田簡直像夢一樣了,人和人的區別,比人和狗的區別都大。”
時書轉過臉,本以爲謝無熾也會一樣,對繁華景象百般觀,但他坐姿端正,專有豔伶人向他拋眼,只是平靜地低頭端起了酒杯。
時書:“哥,這麼淡然嗎?”
謝無熾:“聲犬馬,早看厭了,沒什麼意思。”
時書:“沒意思?你在現代不會是開跑車去酒吧包場,一大羣模圍著你跳舞,你大把大把撒錢那種爺吧?”
謝無熾嗤笑:“從哪兒看到的畫面?”
時書:“刷視頻。”
“還好。”
“???”時書歪著頭,“還好是神魔意思?真的?”
謝無熾端起酒杯,盯著淺綠的清酒,一字不發一飲而盡。
Advertisement
他上自然而然散發著,被優渥的家境所滋養的斂。
時書嘖嘖了兩聲:“除了穿越,這輩子一點苦沒吃吧?”
宴會持續了幾個時辰,中途無聊,時書單手撐著下:“可不可以走了?”
“都沒離席,不是大人,不要第一個走。”
時書百無聊賴,見正前方卻有一位二十六七歲左右的青年文人,清俊文雅,眼中似有孤獨之氣,在人羣中病眼憂鬱,落落寡歡。
他往時書這張桌子看了好幾次,觀察謝無熾。
不過這場宴會似乎令他失,起,朝世子作揖:“學生家中還有俗務,先請告退了。”
世子擺手:“知道你不好,文卿,回去吧。”
裴文卿起,退了出去。
耳邊響起一些竊竊私語:“這裴文卿,還是一如既往地清高,不合羣。”
“世子不用他言,壯志難酬吧。喝酒喝酒!”
時書:“他怎麼先走了?”
謝無熾留意這人背影,詢問:“裴文卿?”
曾興修恰好來喝酒,說:“他啊?他父親就是當年大名鼎鼎的‘新學’領袖裴植,因在納江南稅一事上直言進諫,犯陛下,被當廷杖殺了。裴文卿呢,本來是東都有名的神,父親下獄,恰好在他禮部會試第一時,本來有人說他能連中三元呢!結果被父親牽連,革去了,不許再科場。那以後家破人亡,每天慪氣吐,跌進泥淖,只好來世子府當了門客。”
時書聽得心震,曾興修放低了聲:“這裴文卿,和他父親一樣管閒事!總想著管國家大事,滿是想法,但世子不聽他的呀!謝兄,他聽說你收繳相南寺度牒籌來軍費,這才赴宴,想看看你是不是同道中人,不然以他的子,寧願在院子裡下棋也不來呢。”
Advertisement
謝無熾:“原來如此。”
“謝兄,還沒請教你是哪裡人士?”那曾興修爽朗熱,和謝無熾攀談。
時書乾脆把席位讓給他:“你坐你坐,我去個衛生間。”
曾興修:“衛生間?”
謝無熾:“方言,他去解手。”
“……”時書也不解釋了,離席。
一路詢問,才找到茅廁。桶裡盛放著清水,時書掬起來洗了把臉,把耳朵得發紅,酒的昏脹氣去除,腦子清醒了一些。
不過回去卻找不到路,約聽到吹吹打打的聲響,時書朝著聲音的方向走去。
走到一座荷花池旁,時書聽到有人咳嗽,轉過臉,看見一截單調的青,人站在一株樹底下,用帕子掩著臉咳嗽。
時書走近看清,正好是那多愁多病裴文卿。
他低頭咳嗽,時書眼睛好,看到一塊鮮紅的點時,想起剛纔曾興修的話:“你還好嗎?”
裴文卿把帕子揣袖中,搖頭:“無妨。你是門客謝無熾的弟弟?你謝時書?”他笑了笑說,“你們兄弟,容貌真是俊,宛如兩塊璧玉。”
時書一直坐在謝無熾旁,這羣聰明人,看一眼的臉就不會忘記。
時書:“你要回你院子?”
裴文卿:“嗯,今天天氣冷,出門吹了風不太舒服,咳嗽了幾聲。馬上就到了。”
時書左看看,右看看,裴文卿邊也沒跟個人,像是朋友也沒有。
“我送你回去。”
裴文卿:“不用,就到了。”
時書:“走吧,不麻煩,舉手之勞而已,你咳那樣子嚇人的,應該拿點藥吃吧?”
裴文卿神似有容,也不再說什麼,轉頭,繞過殿閣樓臺,樹林走廊,時書邊走,邊把一旁的樹枝擺出個形狀,踩兩腳。
Advertisement
裴文卿看好幾眼:“你這是做什麼?”
時書:“哦,我怕回來迷路,先做個記號。”
裴文卿笑了,又回過去。
停在一家小院子前,世子府闊綽,修建了不供門客居住的庭院,他和其他人住同間院子。不過今日世子宴請,衆人都不在。
時書:“需不需要我幫你找大夫?”
“不用了,有藥。”裴文卿說,“你且回吧。”
“那我走了,拜拜!”
回去的一路慨,時書辨認著自制的路標,回到宴會場地,也將此事拋於腦後。眼前的謝無熾被幾個人圍著,將一杯一杯的清酒倒腹中。
但並不算被灌酒,許多人在說話,謝無熾垂眼,單手挾著一隻白瓷酒杯,姿勢如玉山傾倒,神迷離有了醉意,但這些人說的話一句都沒放過耳朵,信息全捕捉進腦海。
時書聞到濃郁的酒味:“謝無熾?你喝了多?”
“還好,盡興而已。”
座上,世子終於熬不住,被下人扶去睡覺了。謝無熾起,道:“回去吧。”
他神自若,唯獨眼中似有迷,不過步履卻十分穩當,往流水庵回去。
暮降至,眼前出現了小院子,彎曲的路和桃樹林。
進屋時,時書見謝無熾擡起,鞋子卻在門檻上踢了一下:“你醉了?”
謝無熾坐上椅子,單手撐起下顎,看著時書。
時書也坐上椅子:“累死了,社結束,下次我不想去了。”
說完,見謝無熾臉似乎並不太好,他彷彿是很能忍痛的人,到這時,眉心慢慢蹙起。
“你怎麼了?”時書問。
謝無熾平淡道:“我有胃病,酒喝多了,會胃痛。”
時書一下從椅子裡彈起:“你現在胃疼了?”
“剛纔起,疼了會兒了,現在很疼。”
看他神平靜,完全不像在忍疼痛。但謝無熾給人的覺正是如此,他如果面痛,倒像裝的。這樣面不改,纔像真在忍痛。
時書拎起茶壺倒水:“怎麼不早跟我說。”
謝無熾笑了一笑,垂眸,不知道想到什麼。
“有時候,疼痛很爽。”
時書:“……………………”
“謝無熾,你這個大瘋子。”
時書倒了溫水,遞給他:“喝!祖宗!”
“流之類的痛楚,爽到,會讓人上癮。”
謝無熾接過水杯,縱然面不改,但眉心還是有淡淡的痕跡。時書忽然覺得他,好像那種要強的小孩。
時書到他跟前,俯下:“你很痛嗎?以前我爸爸喝了酒吃蛋炒飯,喝蛋湯,蜂水。我去給你炒個飯。”
兩個人之間的距離很近,謝無熾上的酒味,都染上了他的灼熱。他擡起下,失焦的瞳仁和時書對視:“你會做飯?”
時書:“我只會蛋炒飯。”
“還不錯。”
“……”
“不想吃直說。”
“不想吃。”
“——爺,你還真夠直接啊。”時書撓撓頭髮,想著要怎麼辦:“不然你去牀上躺著吧?這麼疼起來也難的,而且這裡沒有特效藥,估計你要疼一段時間了。”
謝無熾:“沒事,我習慣了。”
“……”
怎麼覺哪裡怪怪的。
謝無熾的緒,也沒有那麼穩定了。
“我扶你上牀躺著?”時書問。
“沒用,躺著也不會緩解。”
謝無熾站起,一隻手搭在他手臂:“今天上廁所那麼久,去哪兒了?”
“我遇到了裴文卿,他咳,我就送他回院子了。”
廂房更暗一些,沒有點燈,謝無熾踩著地往前走。從前到後屋讓一扇竹篦擋著,時書到跟前時說:“謝無熾,擡腳,你別踢到了。”
謝無熾繞過去,進了放牀的地方。這幾天也沒能買出一張新牀,時書不想睡那剛死過人的屋,但謝無熾去那屋呢,時書又心想這屋不乾淨,結果就是在牀邊加了一副新榻。
他倆還睡一屋。
謝無熾坐在榻上,嘎吱一聲。
時書給他拉被子,膝蓋抵著爬上去,把被住的被子一角給拽了出來,再拉上來罩住謝無熾,把人蓋得嚴嚴實實的。
“你先躺著,我又想到一個辦法,可以給你熬小米粥。總之你先吃點,能緩解就緩解。”
被子掖手臂後,姿勢像在擁抱。
時書很白,耳朵下的筋微浮起,更顯得鎖骨蜿蜒,年氣清雋,滿是健康的活力和年輕氣息。
至之人。
傍晚的黑暗,聞到相同的氣息,記憶就會復甦,這被稱爲普魯斯特效應。謝無熾目晦暗,緒一瞬間的鬆懈,那個藏著罪惡和暗的閘門被打開,搖搖墜,裂開一道隙。
時書準備走,謝無熾的手從被子出。
“時小書。”
時書:“怎麼了?”
謝無熾漆黑如潭的眼,一瞬不轉,臉上是平靜的微笑:“我好疼。”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39 章
危險老攻太寵我
18歲的溫時初,高考狀元,名校錄取,演技一流,相貌精致,未來前途無量。 26歲的祁驍,冷戾陰暗,心狠手辣,外人提起他的名字聞風喪膽,見到他殘廢的雙腿害怕到下跪。 倫敦一夜,輪椅上的交織纏綿,祁驍把溫時初空運回國,從此分道揚鑣。 四年後,祁驍再遇溫時初時,溫時初懷里抱著個奶萌奶萌的小娃娃,那分明就是縮小版的自己,是他的兒子沒錯了!某個風和日麗的下午,祁驍一身正裝,包圍了某家不到二十平米的破舊小房子。 “你好,我來接我老婆兒子回家。” 溫時初穿著睡衣,懷里抱著個叼奶瓶的崽子,滿目冷意︰“誰是你兒子?明明是我十月懷胎生的!” “真的,這是我小時候的照片,不信你比比。” 溫時初︰“不好意思我臉盲,有種你現場生一個試試。” 祁驍笑了︰“好,現在就試試。” 祁驍拍拍大腿︰“那麼現在,開始吧,自己坐上去。” 【陰鶩霸道控制狂偏執攻VS盛世美顏雙性生子受】 避雷︰生子文。 攻前期腿有毛病,坐輪椅,以後會恢復。
30.9萬字8.18 25533 -
完結101 章

閃婚
本文又名《老公超了我爸成了首富》《包租公的閃婚生活》 謝琰和認識一個月的顧遇琛閃婚了。 顧遇琛哪哪兒都好,簡直就是在謝琰的審美上跳舞。 美中不足的是,結婚一周了,兩人都沒上本壘。 這讓謝琰不得不懷疑顧遇琛是不是不行。 直到有一天,謝琰看到了顧遇琛的搜索記錄—— #我太大了怎麼辦?# 【小劇場】 (一) 某日,兩人激戰到天亮,謝琰上班不可避免的要遲到了。 顧遇琛從角落里推出一輛頗具年代感的二八大杠,“我送你上班。” 謝琰看了眼鐵架子后座,隱隱抽痛。 意識到問題的顧遇琛沉默地給謝琰叫了輛出租車。 第二天,謝琰看著停在自家門口的嶄新蘭博基尼urus目瞪口呆。 顧遇琛把車鑰匙扔給他,“以后你開它去上班。” (二) 顧遇琛是商界著名的投資之神,投啥啥爆。 他還有一個名頭和投資之神一樣響亮——投資界葛朗臺。 他有一套壓箱底的西裝,用來應付各種正式場合,據說已經穿了五年了。 某次國際會議,顧遇琛終于換下了那套西裝,穿著某奢侈品牌的高定出席會議。 眾同行驚訝,調侃他:鐵公雞終于掉毛了! 顧遇琛攤手,一臉從容,語氣嘚瑟,“這是我愛人給我買的,好看吧?” 排雷: ①不裝窮,攻是真的摳,但只對自己摳,可以為了受花錢如流水。 ②摳逼投資之神首富攻×房地產大亨幼子咸魚受。 ③同性婚姻合法設定。
31萬字8 11700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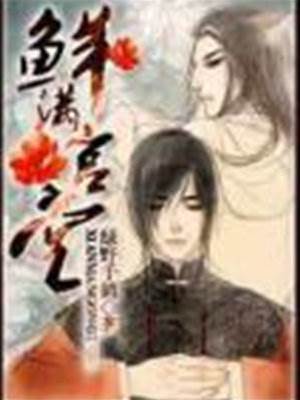
鮮滿宮堂
海鮮大廚莫名其妙穿到了古代, 說是出身貴族家大業大,家里最值錢的也就一頭灰毛驢…… 蘇譽無奈望天,為了養家糊口,只能重操舊業出去賣魚, 可皇家選妃不分男女,作為一個貴族破落戶還必須得參加…… 論題:論表演殺魚技能會不會被選中進宮 皇帝陛下甩甩尾巴:“喵嗚!”
35.5萬字8 7357 -
完結135 章

當軟萌受嫁給暴躁總裁
冷酷不耐煩後真香攻×軟萌笨蛋可憐受 1. 江淮從小就比別人笨一點,是別人口中的小傻子。 他這個小傻子,前世被家族聯姻給了一個人渣,婚後兩年被折磨至死。 重活一次,再次面對聯姻的選項,他選擇了看上去還行的“那個人”。 在同居第一天,他就後悔了。 2. “那個人”位高權重,誰都不敢得罪,要命的是,他脾氣暴躁。 住進那人家中第一天,他打碎了那個人珍藏的花瓶。 那個人冷眼旁觀,“摔得好,瓶子是八二年的,您這邊是現金還是支付寶?” 同居半個月,那個人發燒,他擅自解開了那個人的衣襟散熱。 那個人冷冷瞧他,“怎麼不脫你自己的?” 終於結婚後的半年……他攢夠了錢,想離婚。 那個人漫不經心道:“好啊。” “敢踏出這個家門一步,明天我就把你養的小花小草掐死。” 3. 後來,曾經為求自保,把江淮給獻祭的江家人發現——江淮被養的白白胖胖,而江家日漸衰落。 想接江淮回來,“那個人”居高臨下,目光陰翳。 “誰敢把主意打他身上,我要他的命。” 4. 江淮離婚無門,只能按捺住等待時機。 與此同時,他發現,自己的肚子竟然大了起來。 那人哄反胃的他吃飯:老公餵好不好? #老婆真香# #離婚是不可能離婚的,死都不離# 【閱讀指南】:攻受雙初戀。 【高亮】:每當一條抬槓的評論產生,就會有一隻作者君抑鬱一次,發言前淺淺控制一下吧~
28.5萬字8 1319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