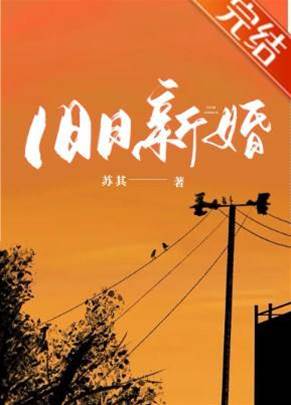《霍爺家的小祖宗甜又野》 第1卷 第3章 扮豬吃老虎
時隔十一年,云清終于又回到了母親住過的別墅。
“把帶上去抓時間打扮!”
一進門,李玉珠便不耐煩地將云清推給了化妝師和幾個傭人。
原本云清灰頭土臉地穿著土氣的棉布還看不出什麼,等洗干凈臉一打扮,再穿上新娘服下樓,完全像換了個人。
居然清麗俗,得令人挪不開眼,皮更是得跟豆腐塊一樣!
李玉珠頓時心生嫉妒。
這個小賤人養在鄉下,怎麼不見曬黑?居然比的兩個兒還要好看!
不過轉念一想,再好看有什麼用,就是個又聾又啞的殘廢,嫁進景園,就等著被霍家那個丑八怪病癆鬼折磨死吧!
云清被李玉珠推搡著塞進了車里,仿佛多留一秒都嫌晦氣。
“趕把人送去景園,別讓那位霍家的爺久等了!”
云清眼底微沉。
車開了不知多久,終于停下了。
紅蓋頭遮面,云清看不見路,下車后,被管家福伯一路牽引進了婚房。
房門在后關上的同時,云清揭開蓋頭,略環顧了一圈,沒看見那個病癆鬼新郎。
而且婚房里也沒有半點喜慶氛圍,只亮著一盞蒼白的壁燈,照映著黑為主調的裝潢,顯得愈發清冷瘆人。
云清索著想打開大燈,昏暗中不小心到了什麼機關,墻上突然從中間分開,出現了一道暗道。
一片死寂里,有慘聲傳出來。
Advertisement
云清微微凝眉,在好奇心地趨勢下,小心翼翼地走進了暗道。
越往里走,空氣里的腥味越濃重。
走得到暗道盡頭,出現在眼前的一幕,讓云清差點吐出來。
衫襤褸的人形躺在地上皮外翻,看著壯的骨骼只時不時幾下搐息著,不停外涌的鮮將下的土地浸得愈發潤……
這分明是人間煉獄!
一只型巨大的雪虎臥在一旁,獠牙和皮上都在滴,雪虎不停咀嚼的看得云清直作嘔。
而唯一一個還活著的男人,眼睛了兩個窟窿,上幾乎沒有一塊好,沖著四周撕心裂肺地慘著。
“——霍景深,你直接殺了我,殺了我!!”
云清活了二十年,自認冷靜,卻是頭一回見到這樣的人間地獄。
手腳冰冷,下意識地后退了兩步,卻撞上一堵墻。
男人低沉冷的嗓音幽幽響起:“對你看到的,還滿意嗎?”
云清頭皮一,猛地轉過,男人似笑非笑地站在后。
“我的小新娘……你還真是會找地方。”
霍景深一步步將到了墻角,他黑浴袍的領口半敞著,出理分明的膛。
云清駭人發現男人口上那幾道疤痕,見過!
就在不久之前……加上相似的聲音,云清幾乎瞬間斷定眼前這個男人就是山里那個輕薄的混蛋……
——他們居然是同一個人!
Advertisement
要是被認出來,這個變態肯定會殺了……
的沉默,讓霍景深戾氣更重。
“不想跟我說話,那以后也就不用說話了!”男人冰涼的大手已經掐住的嚨。
“啊啊啊……”云清趕忙張開著嗓喊了起來,指了指自己嚨和耳朵,隨后連連擺手。
霍景深微微一頓,眸愈發冷,“你是個啞,也聽不見?”
云清趕點頭。
這樣他剛剛做的那些事,就不可能說出去了!
男人黑眸危險地瞇起,“那你怎麼知道我在說什麼?”
云清立馬指向他的。
“……會讀?”
云清用力點頭,可在霍景深眼里只看見冰冷的嘲弄。
“呵,兩個億的聘禮,換一個又聾又啞的廢!你們云家拿我當傻子糊弄?”他角勾起一抹森冷嗜的笑意,“魯斯特,晚上再給你加頓餐。”
白虎發出一聲低嘯,已經撲上去咬死了那個茍延殘的男人。
下一個,就是了。
霍景深揪著云清的領,將往那一片池煉獄里拖。
不……絕對不能死在這里!
還沒有完復仇,也沒有找到母親的下落……
云清一面拼命掙扎,一面暗中出藏在袖口的毒針。
這男人有多狠見識過,沒有十足把握能襲功,眼下只能豁出去賭一把……
就在云清準備手的時候,霍景深口袋里的手機突然響了。
Advertisement
他步子微頓,接起,電話那頭突然傳來管家福伯慌張急切的聲音:“四爺,老太太的頭疼病又犯了!”
聽到事關老太太,霍景深那張冷的臉上總算多了幾人的氣息。
他甩手將云清扔到地毯上,看都沒有多看一眼。
“魯斯特,理掉這個人!”
扔下這一句,他打開暗道,疾步離開。
云清從吸滿的地毯上爬起來,眼前,威風凜凜的白虎正殺氣騰騰地近,渾散發著駭人的暴戾,低吼了一聲,朝著云清撲了過去……
猜你喜歡
-
完結3832 章

霍少的嬌寵前妻
霍氏集團總裁的老婆死了後,有人發現他從良了,不再沾花惹草,誠誠懇懇的帶著兒子過日子。
448萬字8 194243 -
完結440 章

季總別虐了,夫人她要帶娃改嫁!
【追妻火葬場】 季淮夜說,“你父親害死了我的父母,我要讓你全家陪葬。” 宋夢眼眶紅腫,百般解釋。 可季淮夜卻視若無睹,吞並掉她家的家產,奪走她的婚姻,粉碎她的驕傲,一步一步毀掉整個宋家,也毀了她。 後來,宋夢心死了,季淮夜卻慌了,“小夢,再給我一次機會!” 遊輪上,宋夢將手裏的戒指扔進冰冷洶湧的海水裏,冷冷勾唇,“要是撿起來,我就給你機會。” 本想讓他知難而退,卻未曾想季淮夜二話不說跳進了海裏........
52.4萬字8.33 150481 -
完結1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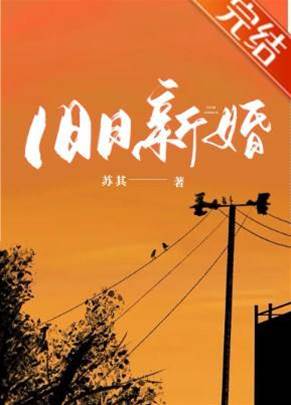
立冬/舊日新婚
秦南山是聞依最不喜歡的男人類型之一,刻板嚴肅,沒有喜好,沒有激情,像密林深處一潭死水,石頭扔進去,波瀾不驚。 一夜混亂,聞依更新認知,不全無可取之處。 一個月後,聞依看着試紙上兩道鮮明的紅槓,陷入沉思。 從懂事起,她從未想過結婚生子。 - 秦南山二十八歲,A大數學系副教授,完美主義,討厭意外,包括數學公式和人生。 聞依找上門時他一夜沒睡,逼着自己接受這個意外。 領證、辦婚禮、同居,他們被迫進入一段婚姻。 某個冬日深夜,聞依忽然想吃點酸的,換好衣服準備出門。 客廳裏穿着整齊加班的秦南山看向玄關被她踢亂的鞋子,眉心緊擰,耐着性子問:“去哪?” “想吃酸的。” “非吃不可?” “嗯。” 男人垂眸看錶,十二點零七分。 他心底輕嘆一聲,站起來,無奈道:“我去給你買。”
31萬字8.18 19464 -
連載635 章

本色
宋津南傲骨嶙嶙,游走于聲色犬馬二十八年,無人能近身旁。奈何喬晚是把刮骨刀。第一次見面,他就被凌遲成碎片,刀刀見血,本色畢露。他早該預料到,有一天自己會斂起鋒芒向這女人俯首稱臣。明知是戲,偏偏入局。她是他永不枯萎的欲望,是他靈魂最深處的墮落與沉迷。
109.6萬字8.18 7726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