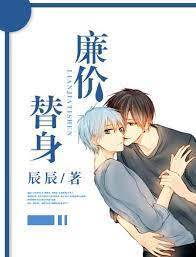《封建糟粕》 97
二人出了花小梁的四合院,巷子長而狹窄,李鳴爭牽著蘭玉的手,雪已經小了,細細碎碎地飄著。蘭玉安安靜靜的,一路沉默不語,直到看著李家停在巷口的車,平就站在車門外。
蘭玉垂下眼睛,看著握著他的手,李鳴爭的手修長而有力,掌心溫涼,虛虛地牽著,像握了一把塵封的冷兵。
李鳴爭說:「上車吧。」
蘭玉一言不發地彎腰進了車,李鳴爭也上了車,二人坐著,不過片刻,平就開車上了空的長街。冬日裡天黑得早,西邊殘籠罩著高低錯落的屋頂,襯著皚皚白雪,有了幾分衰頹的意味。李鳴爭手拂去蘭玉肩上和頭髮上的雪花,聲音徐緩,道:「玩得不開心嗎?」
蘭玉充耳不聞,閉上了眼睛。
二人挨得近,李鳴爭聞到了蘭玉上淡淡的片膏燃燒過後殘留的味道,轉念想起蘭玉出來時的臉,就明白了,想來是蘭玉在外頭犯了煙癮。李鳴爭輕輕叩了叩他的掌心,道:「我爹已經下葬了,明日過完元宵,就將煙戒了吧。」
蘭玉睜開眼看著李鳴爭,臉上沒什麼表,說:「你為什麼會在這裡?」
李鳴爭道:「來接你。」
蘭玉猛地坐直了,漠然道:「我不想回去。」
李鳴爭頓了頓,也不惱,只看著蘭玉,說:「好,你還想去哪兒?」
蘭玉越發煩躁,用力甩開李鳴爭的手,說:「我去哪裡用得著你管?」
他話說得尖銳,毫不留,坐在前座的平心都懸了起來,直直地盯著前路,大氣也不敢出。
李鳴爭看著他眉梢眼角的慍怒,依舊波瀾不驚,說:「蘭玉,離了李公館,你還能去哪兒?」
蘭玉冷冷道:「我想去哪兒就去哪兒,我就算是一頭扎進湖裡也和你們沒有一點兒關係。」
Advertisement
李鳴爭說:「蘭玉,別說氣話。」
蘭玉突然一笑,看著李鳴爭,說:「你覺得我說的是氣話嗎?」
他說著就去拽車門,用力地擰著,可早在他上車時車門就已經鎖死了。蘭玉卻失了控,發起了瘋,竟狠狠去撞紋不的車門。李鳴爭的臉微沉,手攥住蘭玉的手臂想將他拉開,蘭玉全不配合,手腳並用地踢打起李鳴爭,他到底是一個男人,真拚命掙紮起來,饒是李鳴爭一時也制不住。
平被後座的作驚得腳下猛地踩了剎車,二人俱是一晃,李鳴爭直接將蘭玉抵在車座上,攥著雙手,一條頂在他的間,居高臨下,冷冷地俯視著蘭玉。
蘭玉膛起伏,頭髮也微微了,神同樣冰冷,不馴地盯著李鳴爭。
平了聲,「爺?」
李鳴爭說:「繼續開。」他垂著眼睛,下頜線繃,眉擰,罕見的緒外泄,冷峻眉眼迫十足。蘭玉沒有半點畏懼,二人你盯著我,我看著你,李鳴爭說:「想死?」
「蘭玉,到了黃泉之下,你縱是九幽亡靈,也休想擺李家。生是李家的人,死是李家的鬼。」
蘭玉被徹底激怒了,怨恨地瞪著李鳴爭,想用力掙開李鳴爭,可李鳴爭勁兒大,本不容他掙分毫。蘭玉短促地著氣,他想起什麼,突然扯了扯角,氣聲道:「我進不了你們李家的陵園,李鳴爭,你把我埋在你爹邊,你們李家世世代代都得記著這件醜事。」
李鳴爭竟也笑了,他鮮笑,一笑之下竟讓蘭玉怔了怔,李鳴爭輕輕挲著蘭玉的臉頰,有幾分溫地說:「我要將你葬在李家陵園,誰敢說個不字?」
「李聿青和李明安只怕求之不得。」
Advertisement
蘭玉呼吸一窒,李鳴爭說:「到時候,你和沉井的八姨娘也沒什麼區別,骨永遠不見天日,你一樣,無論生死,你都擺不了這副枷鎖,它會一直跟著你。」
李鳴爭道:「和我爹埋在一起,委屈了,我會為你選個好地方,他日等我百年,你我合葬,也未嘗不可。」
蘭玉看著李鳴爭,不可置信地說:「……你瘋了。」
李鳴爭神平淡,道:「蘭玉,你不該招惹我,你既招惹了我,就沒有全而退的道理。」
他輕輕理了理蘭玉因二人手而弄的服,又鬆開手,坐直了,姿筆。蘭玉看著李鳴爭,手指微微發抖,攥了,漠然道:「李鳴爭,我連死都不怕,還怕死後之事?」
蘭玉說:「人死如燈滅,生前誰管後名。」
「可若是你死後,你的陵墓日日和你所憎惡的李家人相對,死後不得安寧,」李鳴爭看著蘭玉,說,「你甘心?」
蘭玉目沉沉地盯著李鳴爭,一言不發。
李鳴爭心想,蘭玉太恨李家了,恨到不惜以死來解,求個乾乾淨淨,清清白白。
可正是因為這子恨,反而了李鳴爭抓住他的手段,李鳴爭恍了恍神,不知怎的,心中竟也生出幾分鈍痛。
李鳴爭說:「蘭玉,你看過你現在的樣子嗎?」
蘭玉眼睫了,抬起眼睛,直直地看著李鳴爭。
李鳴爭掃了眼窗外,對平道:「下一個路口左轉。」
平應道:「是。」
說完,李鳴爭不再說話,蘭玉也沒有開口,車著子死一般的寂靜。
蘭玉不知道李鳴爭要帶他去哪兒,只消一想,他死後被葬李家陵園,日日對著李老爺子的墳墓,就生出激烈的噁心和憤怒不住地腔震,他神經質地摳著冷冰冰的車門,竟有幾分怨恨李鳴爭了。
Advertisement
天已經徹底黑了下來,路邊的屋子裡亮起燭火,平開著車轉過一個街口時,就放緩了車速,果不其然,不過片刻李鳴爭就說了句,停車。
車停了,李鳴爭下了車,蘭玉仍在車,李鳴爭直接扣著蘭玉纖瘦的手腕將他拉下了車。
雪不再下了,朔風未停,鬼哭似的呼嘯著,刮在臉上如鋼刀剮著皮,蘭玉抬手擋了擋臉,細細看去,才發現李鳴爭竟將他帶來了一條從未來過的長街。街道上行人稀疏,兩旁開著許多鋪子,看不清門匾的店門口懸掛著大紅的燈籠,幽幽暗暗,竟有幾分鬼魅的攝人心魄。
蘭玉想出手,可李鳴爭攥得,本掙不,李鳴爭往前走了兩步,蘭玉被迫踉蹌地跟了上去。
走近了,蘭玉約聞著了一縷極悉的味道,那子奇異的味兒頑固地滲冷冽的空氣里,跋扈而霸道。
竟是大煙的氣味。
蘭玉愣了下,一一看過去,竟發覺這一整條街開著的數家店,都散發出同樣的味道,都是大煙館。
蘭玉說:「你帶我來這兒……做什麼?」
他心裡沒來由的生出些恐懼,可不知恐懼什麼,下意識地就退了步,想回手,李鳴爭攥了,冷淡道:「你不是不要戒大煙嗎?來看看你以後的樣子。」
蘭玉說:「我不去。」
蘭玉掙扎的力道不自覺地鬆了,李鳴爭帶他走大煙館。
門口立著迎來送往的小廝,一見二人就殷勤地迎了上來,他一雙招子敏銳,打二人上一過,就落在了蘭玉上。可下一瞬,他就看見了李鳴爭冷冷的目,打了個寒,不敢再看,賠笑道:「爺,您是頭一回來吧……」
話沒說完,平手摟住那小廝的肩膀,將他拉去了一旁。
Advertisement
李鳴爭就這麼拉著蘭玉一路暢通無阻地朝里走了過去。這是大煙館,自清末朝廷就下了煙令,可無論是清朝也好,民國也罷,大煙屢難絕,反而滋生出許多骯髒的見不得人的產業,諸如大煙館之類,其中也不乏戒煙所,可說是戒煙所,骨子裡卻還是大煙館。不知多人進了戒煙所,出來反而癮變得更重,最終掏空家底,傾家產。
這是蘭玉第一次看到這麼多大煙的人。
坐是墊了厚褥子的竹床,煙槍里噴出白煙,煙霧繚繞里,一張張醉生夢死的,癡迷恍惚的臉變得模糊了。蘭玉在花小梁過大煙,煙癮解了,雖被大煙熏得腦子發脹,可看著那些臥在裡頭捧著煙槍吞雲吐霧的人,心底反而冒出幾分森冷的寒意。
他想,他大煙時也是這樣嗎?
那是人嗎?彷彿就是一被大煙腐蝕了魂靈的傀儡,瘋了一般只求那一口黑漆漆的片膏。蘭玉一間一間看去,當中一人得神,竟丟下煙槍,瘋瘋癲癲地手舞足蹈起來,又哭又笑的,中不知在嚷些什麼。他踉踉蹌蹌地拉開半掩的門,正迎面撞上蘭玉和李鳴爭,蘭玉看得手足俱涼,竟忘了避開,所幸李鳴爭將他拉懷中。
蘭玉聞著那人上濃郁的大煙味,嗓子發膩,強烈的嘔吐鋪天蓋地而來,襲擊得他險些站不住,只攥著李鳴爭有力的手臂。
大煙的有男人,人,越往裡越是不人,一張張形容枯槁的臉,眼窩陷,瘦得只剩一把嶙峋的骨,骷髏似的,如癡如醉地抱著煙槍。那瘋癲迷醉的神態,看得蘭玉突然想起今日在花小梁家中,他清醒時,見的花小梁的眼神。
他想,在他們眼中,自己是這番模樣嗎?
這還是他嗎?
蘭玉打了個寒。
突然,有一間屋子裡傳出罵聲,蘭玉抬頭看去,卻見樓梯有個男人一臉不耐煩,旁有個穿著打滿補丁的婦人,瘦瘦小小的,顴骨高突,耷拉著眉,滿臉灰白的苦相。婦人手中還牽著兩個孩子,一個瘦弱的男孩兒,一個孩兒,都哇哇大哭著。
蘭玉一看那男人臉上的焦躁不耐,就知道這人是煙癮要犯了。
婦人苦兮兮地哀求他,「你就把錢給我吧,你明明答應我把鐲子當了就去給兒子買葯,你怎麼又來了煙館……」
眼中落了淚,男人暴地揮開,說:「滾開!」
「哭哭啼啼的,煩死了,」男人額角青筋直蹦,說,「老子說了,等老子了這一口就去買葯。」
婦人臉上印出幾個指痕,捂著臉,哽咽道:「那是娘留下的傳家鐲子,給兒子買葯才不得不當了……」
男人冷笑道:「你也知道是傳家鐲子,老子還沒死呢,先著老子,再管小的。」
他煙癮犯了,指著人道:「趕給老子滾回家,再來煩老子,老子就把你賣了,」他冷冷的,「你不是要給兒子買葯嗎,去賣啊,一樣能給兒子買葯。」
婦人怔怔地看著面前的男人,男人卻已經甩開了,急不可耐地往屋子裡去了。低下頭看著自己的兩個孩子,抹了抹臉上的眼淚,哄著他們,一手牽了一個,黯然地走下樓梯。
直到走出大煙館,蘭玉依舊是恍惚的。
李鳴爭看著蘭玉,半晌,低頭輕輕用了蘭玉的眼睛,低聲說:「蘭玉,聽話。」
「把大煙戒了吧。」
「你即便是不願活,」李鳴爭說,「也不該這麼死。」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