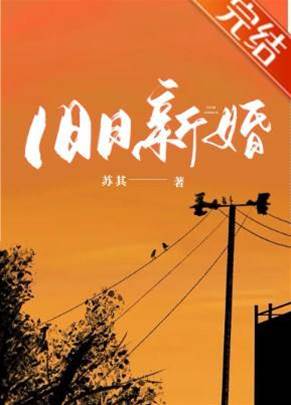《熾焰如火》 第二百八十五章 姊妹情
三人抱頭痛哭,宋沮喪極了。
也不知過去多久,胡艷紅笑了,拭掉了紛紜的眼淚,“前段時間就許諾你們了,不要不就哭鼻子,看這算是怎麼一回事?讓李云看到,該笑掉大門牙了。”
“是,咱不哭。”
宋已經在竭盡全力幫助胡艷紅了,最近心如麻,其實之所以哭,一方面是擔心從今以后胡艷紅果真到農村種田去了,那麼將來幾個人想要團聚一下也難上加難了。
二來是擔心失去了賺錢的門路,三來,不得不承認,宋是有點擔心被拘留的方鈞庭。
未來十五天,在里頭可怎麼度過呢?外面呢?310的生意還需要繼續啊,其實,順利拿到了經營管理權后,生意并沒有和大家想象中的那麼順利。
反之,簡直是舉步維艱。
“去吃飯,找一家最好的餐廳去吃,我請客。”
胡艷紅本就慷慨,拉了兩人就要走,李紅娟將胡艷紅的自行車弄起來,看看站在霓虹燈下的兩個人,“咋能總要你請客呢?出來一次就是你,出來一次還是你。”
李紅娟很是過意不去,其實,這半年來,胡艷紅在想盡一切辦法照顧,收購的東西給的價錢很高,在這高價里頭胡艷紅不但不賺錢,甚至于還可能賠錢呢。
Advertisement
這也是近來李紅娟打聽了市場價以后才知道的。
“皇帝流做,今年到我家,你們誰也不要和我搶啊,今兒個我請客。”
看李紅娟誠心誠意這麼說,宋笑著點點頭,“好好好,你請客就你請客。”
三人到餐廳去,開始點餐。
不管明天怎麼樣,今晚可要吃飽肚子。
這頓飯吃的很愜意,約著一小時后,三人才酒足飯飽從民營飯店走了出來。
抬頭看看,天空的星斗早已經都起來了,繁好像懸掛在藤蘿上的貓兒眼寶石一樣熠熠生輝,宋看著那漫天的星星,一時間倒被這迷住了。
明明是司空見慣的畫面。
不不不,其實是很震撼啊,但正因為司空見慣,所以才沒有留意。
“我們回去吧,太晚了,到那邊公話亭給老師傅打個電話問問孩兒聽話不聽話,晚上回去不安全,先到我家去吧。”
這是胡艷紅的提議。
其實,大家都喝了兩杯,胡艷紅似乎醉醺醺的。
最近這況,無論李紅娟還是宋都不大放心讓胡艷紅一人回去,因此兩人點點頭,到不遠公話亭去,電話很快就接到了。
老師傅急不可待的問:“咋個況,可都理的七七八八了,哎,我一直在等消息呢 。”
宋心里不大用,惆悵的看看遠,又將視線收了回來,風一樣輕的說:“萬字比方字——只差一點啊,我們本來是可以功的。”
Advertisement
“那……”
老師傅也沒問三七二十一,“,你要是想拿下來加工站,我這里還有棺材本,我啊,后半輩子不還是指你和紅娟養老送終?這筆錢你拿去用,我都給你。”
宋極了,心道:“就算這次我不要你這“棺材本”,將來我一定給您養老送終,寬的笑了。
“您啊,就不要心了,我們三個還都年輕呢,你不是也說了嗎?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二來,我們可是八九點鐘太呢,搞得定的。”
宋咧苦笑。
老師傅也知道,一般況只有真正走到山窮水盡,宋這才會求助自己,聞言,他淡淡的笑了,“好好好,總之你有需求你立即聯系我找我就好了。”
“阿爹,”站在宋后頭的李紅娟踮起腳尖靠近柜臺,“娃兒還聽話嗎?”
“喲,這小家伙別提多喜歡我了,下午給弄了米糊糊吃 ,現在剛睡著了,你們做什麼就安安心心去做,家里這一攤子事有我呢。”
看老師傅這麼說,李紅娟更是踏實了。
其實,何嘗不知道老師傅是將自己的孩子看做親孫呢?
宋和老師傅又聊兩句,告知自己和李紅娟今晚準備到胡艷紅家去借宿的事,老師傅點點頭,“你們一起集思廣益,人多力量大,沒過不去的坎兒,你們去好了。”
Advertisement
掛電話之前,老師傅似乎想起來什麼,“,你最近能不回來就不要回來,家里出了點兒意外。”
宋聽到自己的心跳聲,砰砰砰好像敲鼓一樣。
“您說,有什麼事?”宋準備刨問底。
但老師傅卻搖搖頭,似乎不愿因為這意外而影響到宋的心,別開了話題,“總之也沒什麼好大不了的,你最近不要回來就了。”
猜你喜歡
-
完結3832 章

霍少的嬌寵前妻
霍氏集團總裁的老婆死了後,有人發現他從良了,不再沾花惹草,誠誠懇懇的帶著兒子過日子。
448萬字8 195300 -
完結440 章

季總別虐了,夫人她要帶娃改嫁!
【追妻火葬場】 季淮夜說,“你父親害死了我的父母,我要讓你全家陪葬。” 宋夢眼眶紅腫,百般解釋。 可季淮夜卻視若無睹,吞並掉她家的家產,奪走她的婚姻,粉碎她的驕傲,一步一步毀掉整個宋家,也毀了她。 後來,宋夢心死了,季淮夜卻慌了,“小夢,再給我一次機會!” 遊輪上,宋夢將手裏的戒指扔進冰冷洶湧的海水裏,冷冷勾唇,“要是撿起來,我就給你機會。” 本想讓他知難而退,卻未曾想季淮夜二話不說跳進了海裏........
52.4萬字8.33 151372 -
完結1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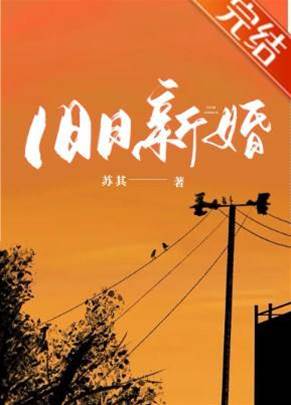
立冬/舊日新婚
秦南山是聞依最不喜歡的男人類型之一,刻板嚴肅,沒有喜好,沒有激情,像密林深處一潭死水,石頭扔進去,波瀾不驚。 一夜混亂,聞依更新認知,不全無可取之處。 一個月後,聞依看着試紙上兩道鮮明的紅槓,陷入沉思。 從懂事起,她從未想過結婚生子。 - 秦南山二十八歲,A大數學系副教授,完美主義,討厭意外,包括數學公式和人生。 聞依找上門時他一夜沒睡,逼着自己接受這個意外。 領證、辦婚禮、同居,他們被迫進入一段婚姻。 某個冬日深夜,聞依忽然想吃點酸的,換好衣服準備出門。 客廳裏穿着整齊加班的秦南山看向玄關被她踢亂的鞋子,眉心緊擰,耐着性子問:“去哪?” “想吃酸的。” “非吃不可?” “嗯。” 男人垂眸看錶,十二點零七分。 他心底輕嘆一聲,站起來,無奈道:“我去給你買。”
31萬字8.18 19478 -
連載635 章

本色
宋津南傲骨嶙嶙,游走于聲色犬馬二十八年,無人能近身旁。奈何喬晚是把刮骨刀。第一次見面,他就被凌遲成碎片,刀刀見血,本色畢露。他早該預料到,有一天自己會斂起鋒芒向這女人俯首稱臣。明知是戲,偏偏入局。她是他永不枯萎的欲望,是他靈魂最深處的墮落與沉迷。
109.6萬字8.18 7769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