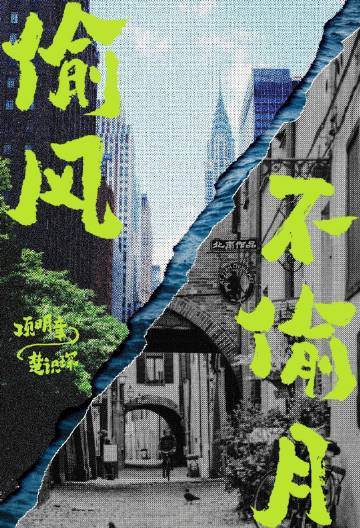《日夜相對》 第283章 春秋1
許迎拎著包,刷了門卡上樓。
從電梯出來時,手機恰好“叮”的響了一聲。
許迎便一邊低著頭看手機,一邊去開家門。
是10010發來的公益短信。
刪除后莫名地笑了一下:還以為是陳敬洲呢。
許迎一只腳踏進玄關。
不知道是不是源于人本天生敏銳的第六,立刻嗅到了一非同尋常的氣息,下意識地先按了下邊上頂燈的開關,已做好了隨時退出房門的準備。
可客廳燈驟亮后,最先闖眼簾的,卻是筆立于臺前那道悉的男人背影。
許迎心跳聲猛然一滯,驚嚇程度不亞于開門的最初一秒,誤以為是小進了家而恐懼。
撞上惡人,可以逃。
撞上了他,卻逃無可逃。
撒謊后不過短短十幾分鐘,就要被當面破。這種極度的恥,令許迎瞬間耳紅,且無比滾燙。
“你,你……”
這扇門進也不是、退也不是。驚愕過后大腦好像陷了一剎的短路,好半晌沒說出一句完整的話。
陳敬洲還拿著手機,聽到聲音后緩緩地回。
他臉上沒有任何緒,被人欺騙的憤怒、不解,亦或是其他,通通都沒有。平靜的實在有些嚇人。
許迎咬了咬,立刻放下包,關好門了鞋子,就這麼著腳跑了過去。
室外璀璨燈火照在玻璃窗上,同樣的也映在他沉靜似水的臉龐上。
許迎仰起頭著他的眼睛,那雙漆黑如墨的眸底,此刻清晰的倒映出屬于的影子。
想:在他眼里,的模樣大概張又不安,心虛的比犯了錯的小孩子更加難以冷靜。
“我不是誠心想騙你的。我只是…我……”
許迎沒勇氣直視他的眼睛,只好垂下了腦袋,急急地想解釋什麼。
Advertisement
心里措辭了無數次,話到邊也歷經了反復的糾結,最后竟拋卻了所有虛假的偽裝,格外誠實道:“……是因為江年明天就復工了,我去了趟醫院跟他聊工作上的事。”
“你也知道,我最近接了好多個項目,今天下班的時間比平常晚一點,我是下班以后過去的,聊著聊著就到這個點兒了……”
“……”
陳敬洲沉默的聽著說,心像困于不見天日的囚籠之中。
他有過許多猜測。掛斷電話后、到上樓以前,那短暫
的時間里,他也安了自己無數次。
可不知道為什麼,他明明吃了藥,但心底里那抑、且無宣泄的緒,好像在一個難以自控的瞬間,猛然沖破枷鎖,從籠中被徹底的釋放。
于是,他聽不進任何解釋了。
只垂著眼睛看,然后視線又落在了那雙白白小小的腳上。
是著腳跑過來的,沒有穿子,有兩只腳趾正悄悄蜷起。
陳敬洲同樣的沒穿拖鞋,雖然隔著層子,可他覺到了地磚冰涼的溫度。
陳敬洲頓時鎖了眉頭。
許迎微仰起臉,想在暗中窺視他的表,恰好瞧見了他皺眉頭的樣子。
連忙又說:“但是、但是也沒有很晚吧!我來回來去的路上,還花了不時間呢。你突然打電話來,我怕你生氣,才沒有說的,你……”
陳敬洲不等的話說完,便從側走過。
許迎不一愣,跟著他回過了,正要張口喊人,卻見他拎著一雙拖鞋又緩步折返。
陳敬洲拎著那雙的稚拖鞋,畫面違和極強。
走回到前時,彎腰把拖鞋放在了腳邊。
“抬腳。”
他的聲音里不帶任何緒,簡短的兩個字令許迎莫名的心中一。
Advertisement
老老實實地抬起腳,讓他為穿上了拖鞋。
他生得很高,直起子冷眼看時,有一種高差異所帶來的強烈迫。
那也是說謊人本能而生的心虛。
陳敬洲看著太淡然了,淡然到似乎有些不合常理。
他只平靜的說:“不需要解釋什麼,我只是你的前夫,在法律意義上,我們沒有任何關系。”
“在道德層面上……”說到這里,他停頓了一下,繼而微笑:“你開心就好。”
許迎聞言怔了怔。
他的語氣再平靜,可話里的諷刺,卻是清晰可見的。
又張了張。
他卻在之前繼續說道:“一直以來你不都是這麼做的,無論什麼事,只要隨你的心意,你覺得開心就好,我無所謂。是我沒有認清自己,也太過高看自己。”
許迎打斷他,很是急切:“我們真的只聊了工作上的事!我沒有說,是因為沒這個必要——”
陳敬洲:“那你覺得什麼才有必要?”
許迎一下子哽住。
只是覺得多一事不如一事,一旦提起江年他
肯定又要生氣。
既然這樣,那還是不提得好。
哪能知道,說這個謊會被他抓個現行。
這麼一來,就連的解釋,都顯得蒼白無力了。
陳敬洲像是看穿了心中所想,他語氣淡淡的說:“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他甚至不及那五年里,你反復提起離婚,反復說出‘你周焰,永遠不可能上我’,那樣的令人憤怒。”
許迎無聲地掐了手指,又聽他說了一句極為莫名的話——
“但我想,人大概只會對自己無法得到、卻永遠心存妄想的東西產生出不安全。”
陳敬洲看著的眼睛。這雙眼睛黑白分明,澄澈如水,一直這麼吸引人,這麼漂亮。
Advertisement
可再多熠熠生輝的彩,也填不滿他心底日積月累的空。
他說:“我不是一只花瓶,沒辦法像花瓶一樣摔碎以后還可以用膠水黏合。”
許迎不理解他的話,眼睛里有幾分困。
陳敬洲沒給再開口解釋的機會,只說:“我沒有不相信你。”
“即便你們今晚不談工作,未來無數個日子,他是你的員工、你的同事,可能也是你的朋友……我沒資格干涉你任何事,就是有些累。”
“我……”許迎眨了眨眼睛,不明白陳敬洲真正的心結是什麼,只想當然的去理解他,又重復解釋道:“我們真的只談了工作……”
弱弱的語氣,令他無法再追究下去。
“我知道了。”陳敬洲說著,又補上一句:“我沒生氣。”
而后又提醒道:“下次別再撒謊了,就像你說的,沒這個必要。”
盡管他心底的緒已然泛濫災,可還是抬起手了的頭發,這作帶有安意味,就像求和的信號。
他說:“我回觀瀾公館了,你早點睡。”
……
陳敬洲從樓上下來,步伐匆匆回到車里。
夜晚車燈打開,稍顯刺眼的線,朦朦朧朧的照出了漂浮在空氣中的塵。
陳敬洲一向穿著得,一不茍,這一刻卻覺得襯衫領口好似扼住了他的呼吸。
他鎖著眉頭扯散了衫紐扣,有些慌地去翻儲格。
他這病不敢讓許迎知道,也不敢讓謝詠君知道,兩種藥裝在了一個瓶子里,時時藏在上,就像藏住了一個不能見的。
不知怎麼的,忽然就想到了趙京山說的話:之所以是,就
是因為它不為人知,且難見天日。
相比起許迎的那個謊言,他更害怕在面前流出任何異樣。
Advertisement
“咚。”
儲格被他翻了,藥瓶從里面掉出來,發出一記極為沉悶的聲響。
陳敬洲心想:姜祎曼突然給他加了一味藥,那一定是因為他的病加重了。
人生病了,吃藥才能痊愈。既然他的病加重了,那麼他適當地多添些劑量,也是理之中。
姜祎曼不是他,每個病人的況也不一樣。
陳敬洲說服了自己。
他不聽醫生的話,明明不久之前已經吃過一次藥了,這會兒又倒出了一次的量,擰開一瓶水,連忙吞了下去。
但他等了許久,期盼藥所帶來的奇異平靜,好像偏偏在他最需要的時刻,徹徹底底的失效了。
他控制不住地回想起許迎眼睛里對他赤的憎惡與怨恨,更控制不住地想起從前與周焰那些甜的點點滴滴。
他不明白,為什麼那個人不是他?
他從心底里嫉妒周焰所擁有過的、對最為炙熱的。
今天,從他患得患失想要主的那一瞬,理智好像就在莫名其妙的緒里走向失控。
陳敬洲忽然覺得心口疼,不過氣,手有些發抖,難極了。
握在掌心中的那瓶藥,好似為了他的救命稻草。
姜祎曼新開的那個“碳酸鋰”,味道實在不怎麼好。
他把兩種藥裝在一起,雖然只有小半瓶,可一口氣全吞下去,味覺本能首先表示了抗議,口腔中炸開的咸腥味,讓他閉著眼睛灌了一整瓶水。
然后,還沒用上十分鐘,胃里便是一陣強烈的灼燒。
他原本的癥狀,果然奇異的消失了。
因為更痛苦的反應,使他無暇再顧及其他。
陳敬洲冒出了冷汗,捂著疼痛灼燒的胃部,空了的藥瓶從他蒼白的手中落。
他彎了彎去撿,口袋里的手機忽然在這時響了。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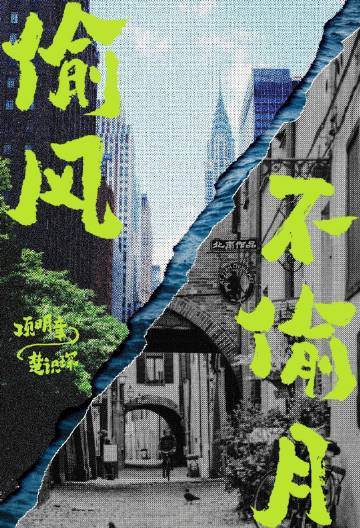
偷風不偷月
穿越(身穿),he,1v11945年春,沈若臻秘密送出最后一批抗幣,關閉復華銀行,卻在進行安全轉移時遭遇海難在徹底失去意識之前,他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后來他聽見有人在身邊說話,貌似念了一對挽聯。沈若臻睜開眼躺在21世紀的高級病房,床邊立著一…
39.3萬字8 6359 -
完結1407 章

嫁給傻王爺后被寵上天
令人聞風喪膽的女軍醫穿越到了段家廢柴二小姐的身上,爹不疼,沒娘愛,被迫嫁給奄奄一息的傻王爺。誰料到傻王爺扮豬吃老虎,到底是誰騙了誰?...
243.7萬字8 16239 -
完結7 章

霸道專寵,葉總裁他又兇又甜
陰差陽錯,她成了總裁的合同替身情人。她給他虛情,他也不介意假意。她以為是義務,卻在偏心專寵下不斷沉淪。她把自己的心捧出來,卻遇上白月光歸國。她經歷了腥風血雨,也明白了如何才能讓愛永恒……合同期滿,葉總裁單膝跪地,對著她送出了求婚戒指,她卻把落魄時受他的恩賜全數歸還。這一次,我想要平等的愛戀!
1.5萬字8 99 -
完結143 章

被我強取豪奪的太子爺回來報仇了
【久別重逢+破鏡重圓+雙初戀+HE+男主一見鐘情】五年前得意洋洋的晃著手中欠條威脅顧修宴和她談戀愛的黎宛星,怎麼也沒想到。 五年后的重逢,兩人的身份會完全顛倒。 家里的公司瀕臨破產,而那個曾因為二十萬欠款被她強取豪奪戀愛一年的窮小子卻搖身一變成了百年豪門顧家的太子爺。他將包養協議甩到了黎宛星面前。 “黎主播,當我的情人,我不是在和你商量。” - 身份顛倒,從債主變成情人的黎宛星內心難過又委屈。 會客室里,外頭是一直黏著顧修宴的女人和傳聞中的聯姻對象。 這人卻將她如小孩一樣抱了起來,躲到了厚厚的窗簾后,按在了墻上。 黎宛星:“你要干嘛!” 顧修宴勾起嘴角,“偷情。” - 顧修宴在金都二代圈子里是出了名的性子冷淡,潔身自好,一心只有工作。可突然有一天像被下了降頭一樣,為了黎宛星公開和顧家兩老作對。 身邊的人好奇的問:“怎麼回事啊?這是舊情復燃了~” 顧修宴淺抿了一口酒,“哪里來的舊情。” - 這麼多年來,一直以為是自己先動心的黎宛星在無意間聽到顧修宴和朋友說。 “我喜歡黎宛星,從她還沒認識我的時候就喜歡她了,是一見鐘情。” 黎宛星一頭霧水。 什麼一見鐘情,當年難道不是她單方面的強取豪奪嗎?
27.3萬字8 14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