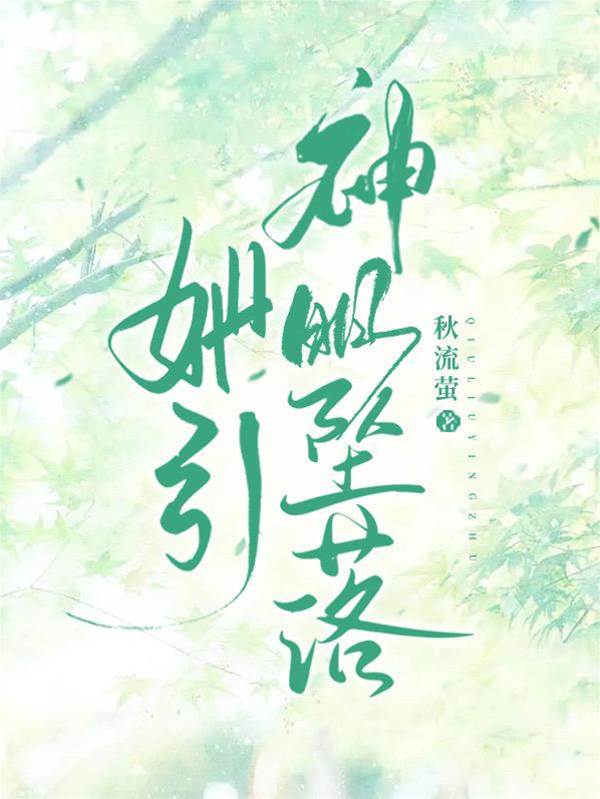《冥王追妻:這個小妞有點甜》 第一千零九十三章 棄車而逃
柴廣漠趙冷都沒聽清,屋裡的聲音就消失了。
「出什麼事了?」
柴廣漠牽著像石頭一樣一聲不響的趙冷,把僵的趕護著到了屋裡,從窗戶裡往外看去,心裡吃了一驚。
————————————————
說起錢斌和小王這邊,他目送老柴跟趙冷鑽進樹叢之後百無聊賴,只能留在車邊著夜的濃郁和夏日獨有的氣氛,雖然山裡不熱,但是在涼的氣氛下還是沐浴出了別樣的滋味兒。不多時,兩人上就結滿了汗水,都是冷汗。
小王雖然取笑趙冷,但說實話,自己如果是一個人呆在這種地方,也得慫。
自己未必就能比趙冷好到哪裡去,不過總歸來說,該取笑的時候,是一個也不會放過的。
一想起電影里的場景,小王也開始發抖。
錢斌卻倒是一直在擔心趙冷的安危。
人走了不久,但每隔幾分鐘,他就得問一次,像是,他們是不是去太久了,會不會出危險?會不會有什麼問題之類的?問的小王都已經快煩了。
「你張口閉口全是你的前輩,煩不煩?」小王撐著手肘,橫了錢斌一眼。
後者不搭理,裡仍舊碎碎念。
「你要真這麼在意的話,你自己跟上他們不就完了嗎?」小王酸不啦嘰的說了這麼一句話。
但是剛出口就後悔了,要是這姓錢的人一走,自己可不就孤家寡人?一個人呆在這深山老林里,到時候真遇上什麼豺狼虎豹不好說,要是來個劫的歹徒自己可怎麼辦?
再說了,小王眼看向錢斌,抿著不吭聲。
實在不想承認,但這男的真要是走了,自己可是真的能哭出來。
就這樣看了錢斌好幾眼,沒見著他準備離開的樣子,小王心裡這才呼了一口氣,可是又邁不過這一層面子,著甚至出言諷刺:
Advertisement
「怎麼,你也不敢一個人走夜路,還是不敢去見他們,也是,畢竟人家好好的二人世界,你去打擾他們幹嘛?」
錢斌一聽這話,臉上的表有些不好看,一時間又是錯愕,又是驚異,最後變了一抹寂寥,他說,「小王,你也覺得,你也覺得他們倆有那麼一啊?」
小王咯吱的一笑,先是白了錢斌一眼,埋怨道,「你憑什麼我小王啊?我跟你關係很好嘛?論輩分論資歷,不到你我小王!」又忍不住八卦起來,說道,「我告訴你,這倆私底下事兒多著呢,他們倆可不是看起來有那麼一那麼簡單,我就跟你這麼說吧,您在局裡問一問,隨便來一個就算是咱們臨時雇來打掃的黃阿姨,你問問都知道,哪有一個看不出來,這個老柴,對咱們小趙,那可不是一點兒半點兒的意思。」
錢斌點了點頭,「哦」了一聲不說話了,他打開車門,說是要出去氣,涼快涼快。
前腳一走出車,後腳就聽到小王的驚呼:「你——你,幹什麼?你別走啊!」
錢斌笑著搖頭,不過笑得像是苦笑,小王眼睛非常尖銳,一看到他的表,心裡就明白了大半,只見錢斌搖開車門,圍著車轉了一圈說道,「我就覺得車裡太悶了,出來走走。」
小王也趕下了車,生怕這錢斌腦子不好使,一個勁的就往外跑,萬一讓一個人留下,這麼個弱子,就這麼代在深山老林里,也太不雅緻了
見到小王像跟屁蟲似的黏在自己屁後面,錢斌來了興緻,他回頭問道,「怎麼,你也覺得車裡憋悶,想出來口氣?」
小王朝他白了一眼說,「我就不能下來走走呀,倒不是說車裡面,只不過一個人呆著太無聊了,我得找個人說說話,不然我會瘋的。」
Advertisement
錢斌笑了笑,他雖然是實習警察,只來了兩個月,可是兩個月里以他對小王的了解來看,可能是警局裡最話嘮的話嘮,也是八卦的不行的八卦。
「行行行,那就隨便你了。」錢斌擺擺手。
他反正倒無所謂,也不在乎是一個人走走還是兩個人逛逛,他先是拍了拍車前蓋,縱跳起,一屁坐到這蓋子上,乘著悠悠的涼風,在夜沐浴的深山老林裡面,頗也覺得愜意,但小王卻不這麼想。
「不是說走走嗎?」小王扭著手骨,眉頭皺得的看著錢斌,有些埋怨似的問道。
錢斌到沒有回答,出手指了指天空說,「你看看。」
小王抬起頭,有些驚訝的捂住,忍不住發出呀的聲音,只見到滿天星河鋪著碎碎的幕,彷彿是從遠紛至沓來,又像是挪著款款步伐的一個倩麗影。看上去和城裡的景緻極為不同。
看著小王這種驚訝的臉,錢斌不出了什麼都懂的表來。
「怎麼?你是不是覺得自己很偉大?」小王的餘瞥到錢斌那討人厭的樣子,忍不住扁了扁,咂咂的說。
雖然不想承認,但真的很。小王吐出一口氣。
後者只是笑,卻不回答。
小王了個懶腰,仍舊盯著天空中那璀璨的星河,笑了笑說,「不過你倒是有這個資本啊,平時我很注意這些,沒想到山裡的景這麼好看,真是真是錯怪了,我是真沒想到這座山居然這麼漂亮,哎,我還想著失禮的事,的確是對不公平。」
「失禮的事?」錢斌好奇的問道。
小王吐了吐舌頭,有些俏皮的說,「就是那個就是,這是我用來嚇唬小趙的,那兩部電影嗎?你不過別說,就咱們這樣在山裡,的確有些像那種節,說不定過一會兒就有一個彪形大漢來找咱們,然後咱們一看那不是人類,發現上滿流的都是,也無法通。」
Advertisement
錢斌雖然當過兵,材也比頗為魁梧,但是聽到小王繪聲繪,惟妙惟肖的形容,也忍不住起了一皮疙瘩,哆嗦起來,他連忙說道,「你快別說了,說的我都起了一的皮,你咋那麼皮呢?非得把自己說的也害怕才行是嗎?」
小王又笑了笑,兩人對視一眼,忍不住都笑起來,你看著我我看著你。
「不過你說的沒錯,在這種地方拋錨確實是不幸中的不幸了,就算真的發生什麼意外的事,我覺得也無可厚非,」錢斌忽然有意沒意來這麼一句,聽得小王雲里霧裡,滿眼冒金星。
「喂,你,你什麼意思?」彷彿是被涵到了,小王捂了自己口的齊肩襯衫和無袖短袖,打著旅遊的噱頭來山裡,也沒穿上什麼像樣的服,更沒想到山裡會這麼涼。
錢斌一瞧這當中帶了點姿的模樣,不由得臉都紅到了脖子,急急忙忙揮手說,「你想哪兒去了?我說的是安全問題,安全問題,」他重複了幾次又說道,「你瞧,這都過去了個把鐘頭了,老柴跟前輩他們那居然也沒有一點回應。」
小王扁扁,嗯了一聲,又說道,「說起來為什麼你要前輩啊?我是說小趙,你對的態度跟我的也差太遠了,我跟可是同期耶,按理說你也應該我一聲前輩啊,來一聲我聽聽,小子。」
似乎對小子這個稱呼頗為不滿,錢斌咬牙關說,「這是有道理的,也是有淵源的,你可別占我便宜。」
「什麼占你便宜?我本來就比你年長,又是你前輩,確實是這樣啊,我可比你早幾年進警隊,你不就當兩年兵嗎?怎麼還不能我前輩了,來來讓我滿足滿足,一聲,放心我不告訴人家,就咱倆獨的時候。」
Advertisement
錢斌越是抵抗小王彷彿就越來興緻,騰的一下起了,從車上翻過來,匍匐前進,來到錢斌眼前。
兩人離的越來越近,用手肘勾住錢斌的脖子,角彷彿吐氣如蘭,吹在錢斌的耳上說道,「趕的啊,你不好好表現,我可不放過你。」
錢斌被小王這大膽的舉給嚇了一跳,他扭頭就要跑。
小王見他跑了,磨拳掌,彷彿更有興趣一樣,呸了一聲說,
「好小子,你以為老娘是吃草嗎?還以為是吃素的,我才不會放過你呢,等著,看姐怎麼治你。」
飛起一腳,從車蓋上跳下,飛快的形極度敏捷地反而下,像一條叢林中的獵豹,三下五除二的就截住了錢斌,攔在他前,嘿嘿低笑著說。
「沒地兒跑了吧?」
錢兵苦笑,「你跟我在這玩什麼呢?咱們現在不是當務之急應該趕修車嘛。」
小王聽了趕辯解,攤開手說,「修車是要修車,但你想,小趙他們不是剛走沒多久嘛,這才一個鐘頭,估計連人家都沒找到,更談什麼修車的,再說了,咱倆玩玩也不耽誤時間嗎?而且我,我只是想告訴你,我沒有那個意思。」
小王一提到這個臉也跟著紅了,埋怨道,「都怪你說些什麼奇怪的話,我只是想知道你為什麼不願意我前輩。」
錢斌無奈,他點了點頭說。
「倒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緣由,但是我剛進警隊的時候,大家對我都不是很待見。」
小王「嗷」了一聲,似乎沒有太大的印象。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連載4114 章
罪妻來襲:總裁很偏執
易瑾離的未婚妻車禍身亡,淩依然被判刑三年,熬過了三年最痛苦的時光,她終於重獲自由,然而,出獄後的生活比在監獄中更加難捱,易瑾離沒想放過她,他用自己的方式折磨著她,在恨意的驅使下,兩個人糾纏不清,漸漸的產生了愛意,在她放下戒備,想要接受這份愛的時候,當年車禍的真相浮出水麵,殘酷的現實摧毀了她所有的愛。
361.9萬字8 23603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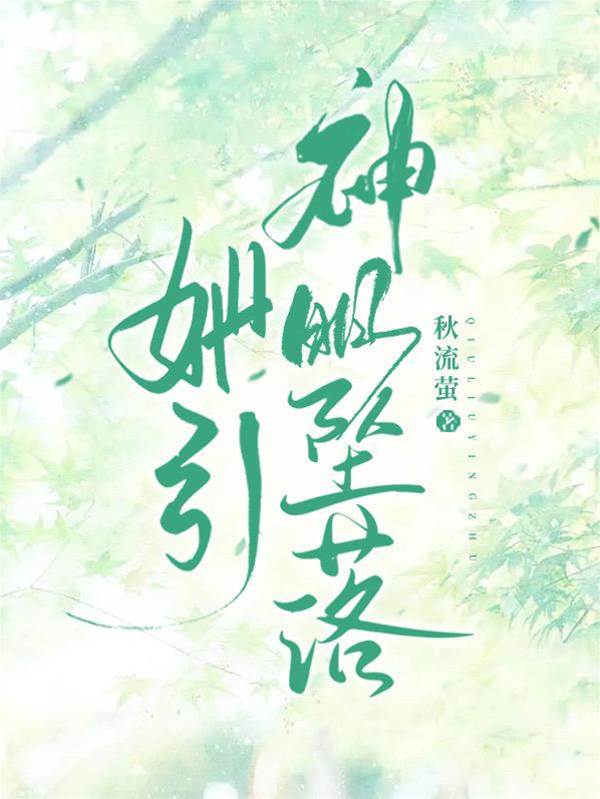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311 章

昨夜燈暖
三年前,蕭叢南被迫娶了傅燼如。人人都道,那一夜是傅燼如的手段。 於是他一氣之下遠走他鄉。傅燼如就那樣當了三年有名無實的蕭太太。 一夕鉅變,家道中落。揹負一身債務的傅燼如卻突然清醒。一廂情願的愛,低賤如野草。 在蕭叢南迴國之後。在人人都等着看她要如何巴結蕭叢南這根救命稻草的時候。 她卻乾脆利索的遞上了離婚協議書。
51.4萬字7.82 115868 -
完結120 章

豪門小可憐?不,是你祖宗
豪門小可憐?不,是你祖宗小說簡介:宋家那個土里土氣又蠢又笨的真千金,忽然轉性了。變得嬌軟明艷惹人憐,回眸一笑百媚生。眾人酸溜溜:空有皮囊有啥用,不過是山里長大,
22.5萬字8.46 589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