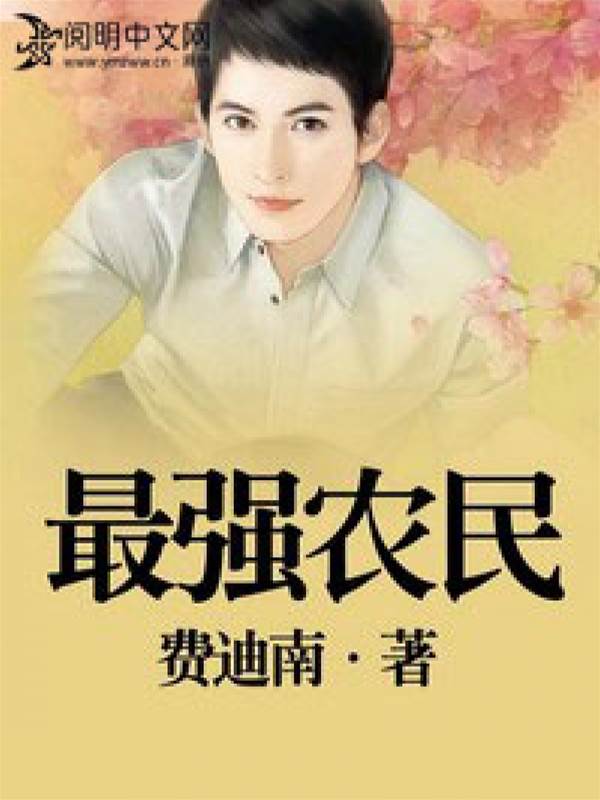《肉欲嬌寵》 第296章
你是誰
雖然看上去似乎只是機人的電量耗盡了,但自那之後日益緩慢的反應和漸漸僵的作無一不在說明著,的使用年限已經到了盡頭。
終於有一天,當年睡醒了從樓上下來時,看到的只有那端坐在沙發上,無法啓的軀。
門鈴很快就被按響了。
幾個同樣穿著金屬皮的高壯男人將沙發上的如同拎垃圾一般拎起,打算帶走。
「在這裡,機人在使用年限到期後,會被聯邦機人管理中心的執法機人帶走,統一回收報廢。」
耳旁的聲音向楚解釋了的疑慮,而看著年歇斯底裡掙扎著想要阻攔那些人帶走的樣子,楚沒來由的心中酸疼。
失去功用的最終還是被帶走了,獨留年待坐在空的客廳裡,神迷茫。
隔了不知多久,他終於了。他攤開自己的手掌,一塊指甲蓋大小的芯片躺在他的手心上。他抬起手,將芯片手腕上的智腦中。
「那是什麼?」
「你……九五二七的核心芯片。」
兩人說話間,年已經將芯片打開,而一段視頻也隨之跳了出來,的臉龐浮現在半明的藍屏幕上。
Advertisement
「小主人。」
「九五二七今後不能在陪伴在你邊了。」
「主人在九年前離開時幷沒有設置命令。但爲了確保小主人能夠活下來,九五二七還是擅自用家庭賬戶中的錢,到今天爲止,賬戶餘額如下……」
「九五二七不是個合格的家用機人,沒有將小主人照顧好。小主人,九五二七離開後,希您不再挑食,您的仍於亞健康狀態,平時應當多鍛煉……」
「小主人一直說九五二七是家人……雖然九五二七知道不應該,但是……還是謝謝小主人,九五二七喜歡這個稱謂……」
「很奇怪……小主人……機人是沒有的……可是爲什麼,一想到要離開小主人,九五二七就覺口不適呢?」
抬起一隻手捂住了口,銀灰的眼眸中亮漸漸熄滅,「程序……程序開始出現碼了……小主……人……再……再見……」
視頻定格在皺著眉的無暇臉龐上,而在的眼中彩熄滅的同時,眼眶中竟有淚珠順著眼尾滾落,儼然人類一般。
年癡癡地手想要的臉頰,手卻穿過明的屏幕揮向空氣。
Advertisement
「你後來又去把我找回來了。」
楚看到這裡,忍不住移開眼去,年的模樣讓不忍看下去。
「是的。」男人聽到楚似乎漸漸開始承認九五二七就是自己,心中不有了些期許。
「我其實一直都沒有將……九五二七看作是機人……是我的家人……更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喜歡的人……」
「那時我其實已經開始研究如何將人類的賦予智能機人了,而且那時候我已經在……九五二七上做了一些調試編碼。」
「所以當我看到最後流淚和心疼的表時,我以爲我離功不遠了……」
「可誰知在那時就這麼突然離開了我……」
年在樓上待的時間更長了,他幷沒有聽從臨走時的囑咐,連吃飯都不怎麼吃了,每日都待在房間裡,在電腦上敲敲打打,那一行行跳的代碼映在他黑的瞳孔中,讓他看上去有些失常的瘋狂。
場景再一次轉換了,楚發現自己置於一有些破舊的平房裡。
年已經長爲青年了,容貌與賀斯年幾乎一樣,但是卻比他瘦削了很多。他坐在書桌前,似乎與什麼人在網上聊著天,不知對方說了什麼,他眼中忽然迸發出彩。不一會兒,他便激地站起,朝著門外衝去。
Advertisement
他急匆匆攔住一輛飛行,不知過了多久,終於在一廢墟中停下。
青年下了車,打開了手腕上的智腦。上面的地圖上標著一紅點,與他現在的位置十分近了。他循著紅點的方位,一點點往前探尋著。
楚發現,這廢墟似乎是一垃圾場,四周都遍布著廢舊淘汰的電子設備與零件,甚至看到了一些殘肢斷手,當然,那些都是金屬機械,屬廢棄的機人們。
終於,地圖上青年的綠點與紅點重合了。
一已被損毀地看不出模樣的機人殘骸被青年抱了起來。毫不在意殘骸上的髒污,青年輕輕地抱著回到了飛行上,如同抱著最珍貴的珍寶。
楚想起來了。
之前在穿越公主的那個世界中,第一次做關於這個世界的夢,就是如今看到的場景。
無法說話,無法作,卻被一個人輕地抱離,帶回了家。
接下來看到的與當初在夢境中到的別無二樣,青年每日都心打理著的。他不斷地往家裡帶著大大小小的零件,爲換上了新的肢,新的元件,每一個看上去都價值連城,無比。
Advertisement
「爲了一個機人,值得嗎?」
楚看著青年盡心盡力地做著這些事,心中不知是什麼滋味。
「不是機人。」
「是我最的人。」
青年的行好似也在證明著男人的話。他時常會親吻沉睡中的,如同王子親吻著他的睡人。
終於有一天,睡人醒了。
「你……是誰?」
歪著頭,銀灰的眼眸中閃著疑。
「我又是誰?」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連載262 章

春潮洶湧
嚴丞鈺卻一點都沒有放過她的意思,將自己深深的埋進她的體內之後,感歎著那種極致的**,差一點沒忍住,失控了自己。 他壓著她歎息的說道,“還是那麼緊。” 楚纖纖在軟軟的床上難受又享受的扭動著,黑發鋪滿了整個床,整個人被他微微提著向上,進入得更加徹底。 她覺得自己整個人都被他撞飛了,身體卻不由自主的扭著腰配合他。 “啊……”她哭著尖叫起來,快感因為這個姿勢兇猛而來,幾乎讓她承受不住這樣的刺激,雙手胡亂的扯著床單。
45.3萬字8 260705 -
完結306 章
肉欲嬌寵
從小受盡人情冷暖,從未嘗過嬌寵滋味的楚嬌,忽然被告知,她的存在不過是小說中的寥寥幾筆,她所受的一切苦難不過是作者爲了成全男女主而隨意設定。 她不甘,不服,不願。 爲了復仇,她綁定【女配肉欲系統】,要想活下去回到原世界,她必須達成踢走女主,攻略男主的任務,而通關條件是——體、體液? 本想走腎不走心的她,沒曾想,卻是遇上一個又一個將她捧在手心裡疼寵的人。 他們付她與真心,她也許之以深情。 而最終,她發現,原來一切,都是愛。 星移鬥轉,時光悠悠,你愛的樣子我都有。 ——題記 設定: 壯碩古板悶騷二叔×古靈精怪小蘿莉(已完成) 冷面冰山寵徒師尊×嬌俏爐鼎乖徒弟(已完成) 絨毛控禁欲大總裁×軟糯小巧萌貓妖(已完成) 腹黑狡詐鰥夫公爹×美貌守寡兒媳婦(已完成) 民國冷峻軍閥大佬×任性妄爲嬌小姐(已完成) 霸道狠厲蠻族可汗×聰穎和親真公主(已完成) 心機深
40.7萬字8.72 482339 -
完結207 章
美人食色
短篇肉文合集(以肉為主,劇情為輔) 第一個故事:性愛錄影(偽兄妹)完結(結局1V1,過程有和男二啪啪啪過) 第二個故事:裸替(裸替X影帝)(1V1) 第三個故事:錢吉俱樂部(大學老師X學生)(1V1) 第四個故事:臥底(臥底X臥底/臥底X黑老大)(1V1,有和男二啪啪啪) 第五個故事:裸替番外(經紀人X新人主線/影帝X裸替副線) 其他作品: 無
20.9萬字5 198543 -
完結42 章
玩家
兩攻相遇必有一受! 池大的風格大家都懂得,走腎又走心,他的"坐好我自己動"至今依然是經典中的經典! 這一篇"玩家" 還出了實體書,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到代購,本篇的圖片就是實體書的封面設計稿~ 攻受皆浪,互相禍害 小小排雷:攻受皆為"玩家"肯定不潔/反攻*1
14.4萬字8 26190 -
完結5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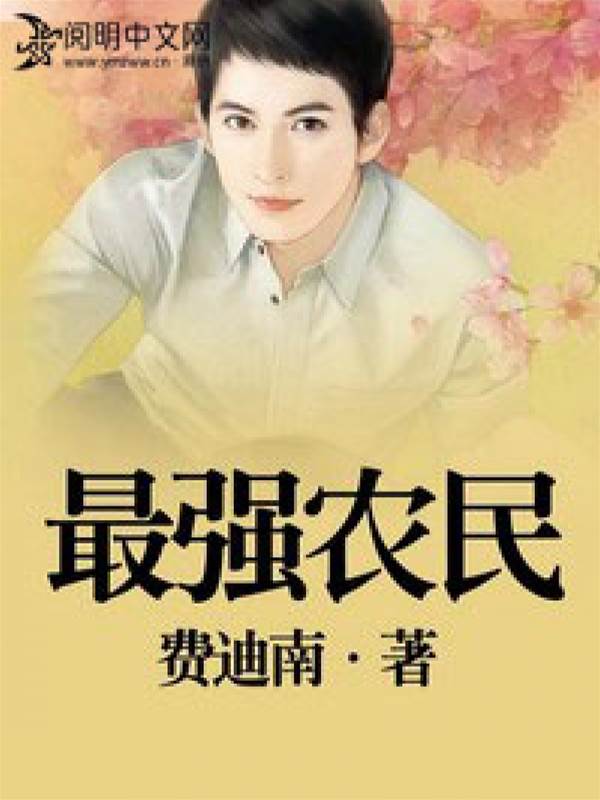
最強農民
作為世界上最牛逼的農民,他發誓,要征服天下所有美女!
14.3萬字8.18 1261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