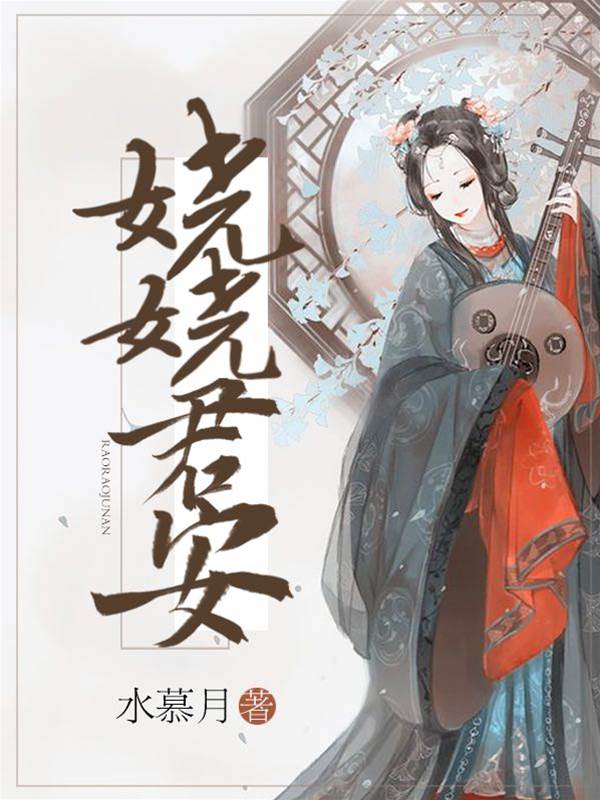《夫人救命,將軍又有麻煩了》 第384章 奇才天才(二)
聽他這樣說,侯飛擎與甲狄都眼怪異看了他一下。
侯飛擎早知他著了鄭曲尺的道,只道他是被自己的化形象迷了眼睛,將鄭曲尺奉上了神壇,實則不過就是一稍微多奇思妙想的子罷了。
他承認,子為匠,確與眾不同,再加上有些膽識與能力,第一次見識到這樣的子,他也覺得有意思極了。
人們總為一些稀罕事而忙碌追逐,如同尋找寶藏一般樂此不疲,但一旦得到了,到頭來一朝清醒后才會發現,它,也不過如此。
甲狄聽公輸大家的口吻,好似兩人關係並非當初在「霽春匠工會」上見過那麼一次,那是一種對相之人才會用的語氣。
但他也沒多想,如今積在他頭頂的事遠比探索別人的私事更重要。
「公輸大家,有些話我也不妨直言,請你來只為解決鄴軍火炮一事,不知你對信中所述火炮之事,可有想到什麼對策?」
公輸即若並非軍隊的人,但他們公輸家與北淵國還有軍部卻有一些暗中協議,只為平衡與牽制彼此。
不過一向這種事還犯不著他來這一趟,他來自有他的打算。
「我帶來一批新的盾甲,重量較以往輕了近一半,但堅程度卻更甚,最主要的是它若連壘,固若城牆。」
甲狄聞言,大喜過。
「你儘管拿它去試一試對方的火炮威力。」公輸即若如是道。
「那便多謝公輸大家的慷慨了!」公輸出品,必然品,甲狄得此好消息,心下激,迫不及待想要一探究竟了。
——
等鋸子帶著甲狄去看公輸家新研製的盾甲時,侯飛擎則與公輸即若私下聊天。
他抱臂道:「你不是還有一件武鐵馬嗎?怎麼不拿出來?」
Advertisement
公輸即若朝前走去,漠然的語氣:「這樣的戰事,還需不著用上鐵馬。」
公輸即若雖然神淺淡,但眸底的傲氣卻是不加掩飾。
「你見識過鄭曲尺所造的火炮了嗎?我聽著都覺得不可尋常。」侯飛擎追上去,與他並肩而行。
「我與墨家這些年以來也早就涉獵火藥,火雷不過就是最初的失敗品罷了,雖未見過對方的火炮如何,但卻北淵未必不能做出一樣的,再者他們的火炮亦未必能有我新研製的武更好。」
提及自己擅長且獨佔鰲頭多年的範疇,公輸即若即便平時沒有什麼競爭與勝負心,但他也不認為真有什麼一朝努力便能超越別人數年的果。
尤其是兩者不於同樣的層面與基礎,是研發需要耗費的金銀、實驗所產生的失敗積累,人力力各方面,便不是一件憑天馬行空的構思就能解決的事。
他敢肯定,鄴國所謂的「火炮」自然弊端不,而這些東西他們需要時間跟能力去解決,至不是現在。
雖然公輸即若對鄭曲尺的能力認可,但不等同他認可鄴國,等甲狄再與鄴軍戰一場,便可以看穿他們紙老虎背後的虛有其表了。
公輸即若的話不是空來風,侯飛擎自然也是信的,於是他掠過這個話題,問起另一件事:「你帶來的是用新找來的那一方稀有鐵礦打造的盾牌?」
這事他略有耳聞,公輸家的弟子廣布九洲,探尋稀有礦源回巢亦是常有的事。
「本來是配給公輸家的軍隊,但既然來了一趟,便暫時借家軍用一用。」
不愧是財大氣的公輸家,隨便一件「隨手禮」便是大手筆。
侯飛擎搖了搖頭:「麻煩的是現在鄴軍佔領了霜飛關,這要奪回來倒不是什麼難事,可這裡子面子這一次都算是丟盡了!」
Advertisement
公輸即若頓步,看向侯飛擎:「鄴軍這個時候來攻打北淵,你覺得鄴軍究竟是在想些什麼?」
關於這個問題,公輸即若很不解,站在他的角度解釋不了,便想諮詢一下侯飛擎這個「專業人士」的想法。
按說鄴國目前正於孤舟獨行,生怕暗會有「風浪」打來翻船,只怕該是哪邊都不敢得罪的謹小慎微才對。
可偏偏他們挑了七國實力中最強的北淵軍,這一次無論是挑釁還是犯傻,這麼做所造就的後果他們承擔得了嗎?
鄴國當真有能力承得住北淵國的怒火嗎?
說實話,侯飛擎這頭一時也沒想得通,但正因為想不通,他才覺得這事不簡單。
而就在他們都奇怪鄴軍這是突然發什麼神經的時候,鄴軍那頭不再悶不吭聲玩襲,而是公然發話了。
「鄴軍此番突襲霜飛關,只為向北淵軍索討逃走的愙朱部落,無意與貴國起衝突,但愙朱部落與我烏堡多次造巨大損害,此事必須清算到底,北淵軍能將逃犯愙朱部落清肅出境,不再包庇。」
此言一公開,像是為其行為解釋了一切,又像是什麼都沒解釋。
有人百思不得其解,這愙朱部落與烏堡結仇,卻關他們霜飛關什麼事?又與他們北淵國有什麼關係?
甲狄這頭也是被鄴軍這一番迷之發言給整蒙了,公輸即若卻在聯繫前後,似猜到了一些什麼,唯侯飛擎臉遽變,一度坐立不安,彷彿在煩惱或沉思著些什麼事。
「放他娘的狗屁,愙朱部落關我們霜飛關什麼事?」甲狄一掌怒拍在桌案上。
侯飛擎眼見事態發展至今,有些事也無法再繼續瞞下去了。
他著實也沒想到鄴軍竟然會自己破這一層窗戶紙,但想起不久之前市井中的流言,說不準就是鄴軍他們自己放出來的,目的顯而易見,便是為了找一個機會將宇文晟沒死的事順理章地披出來。
Advertisement
明明是他們鄴國幹了件齷齪祟、欺瞞天下人之事,別人以牙還牙,卻不曾想最後卻是拿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你是說,你早知宇文晟沒死,便與愙朱族私下合謀,想借他們之手來陷殺宇文晟?」
侯飛擎額:「非也,我並非早知宇文晟未死,只是那愙朱部落族長恰好與我乃舊識,他數月前曾與宇文晟打過一次照面,他擅種蠱,也懂觀面,他懷疑對方上的癥狀疑似中了他們族的凰淚。」(本章完)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2229 章
帝凰之神醫棄妃
大婚當天,她在郊外醒來,在衆人的鄙夷下毅然地踏入皇城…她是無父無母任人欺凌的孤女,他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鐵血王爺.如此天差地別的兩人,卻陰差陽錯地相遇.一件錦衣,遮她一身污穢,換她一世情深.21世紀天才女軍醫將身心託付,爲鐵血王爺傾盡一切,卻不想生死關頭,他卻揮劍斬斷她的生路!
448.5萬字8.38 388648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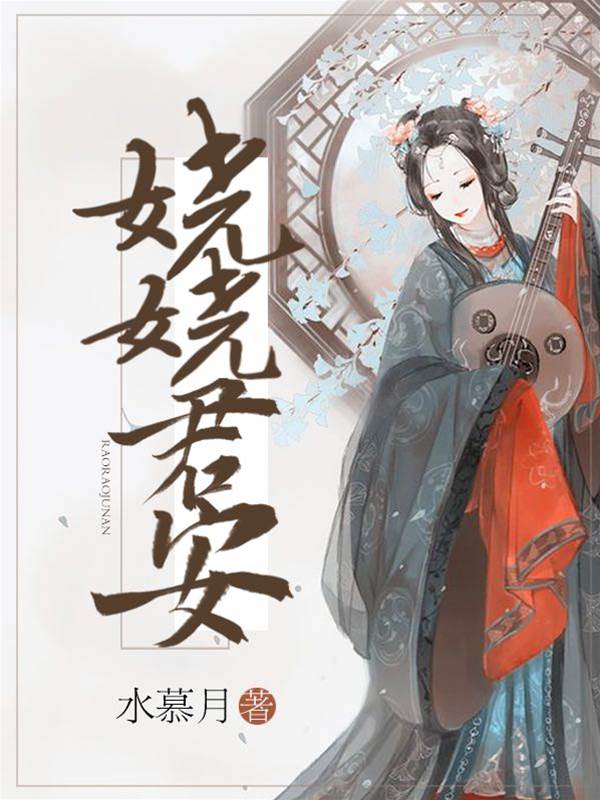
嬈嬈君安
原想著今生再無瓜葛,可那驚馬的剎那芳華間,一切又回到了起點,今生他耍了點小心機,在守護她的道路上,先插了隊,江山要,她也絕不放棄。說好的太子斷袖呢!怎麼動不動就要把自己撲倒?說好的太子殘暴呢!這整天獻溫情的又是誰?誰說東宮的鏡臺不好,那些美男子可賞心悅目了,什麼?東宮還可以在外麵開府,殿下求你了,臣妾可舍不得鏡臺了。
16.6萬字8 14823 -
完結648 章
重生后,我成了渣男他皇嬸
因道士一句“鳳凰棲梧”的預言,韓攸寧成了不該活著的人。外祖闔府被屠,父兄慘死。太子厭棄她卻將她宥于東宮后院,她眼瞎了,心死了,最終被堂妹三尺白綾了結了性命。再睜開眼,重回韶華之時。那麼前世的賬,要好好算一算了。可慢慢的,事情愈發和前世不同。爭搶鳳凰的除了幾位皇子,七皇叔也加入了進來。傳說中七皇叔澹泊寡欲,超然物外,
116.3萬字8.18 58167 -
完結242 章

教不乖,佞臣替人養妹被逼瘋
【傳統古言 廢殺帝王權極一時假太監 寄人籬下小可憐 倆人八百個心眼子】少年將軍是廝殺在外的狼,窩裏藏著隻白白軟軟的小兔妹妹,引人垂涎。將軍一朝戰死沙場,輕躁薄行的權貴們掀了兔子窩,不等嚐一口,半路被內廠總督謝龕劫了人。謝龕其人,陰鬱嗜殺,誰在他跟前都要沐浴一番他看狗一樣的眼神。小兔落入他的口,這輩子算是完……完……嗯?等等,這兔子怎麽越養越圓潤了?反倒是權貴們的小團體漸漸死的死,瘋的瘋,當初圍獵小兔的鬣狗,如今成了被捕獵的對象。祁桑伏枕而臥,摸了摸尚未顯孕的小腹。為了給兄長複仇,她忍辱負重,被謝龕這狗太監占盡了便宜,如今事得圓滿,是時候給他甩掉了。跑路一半,被謝龕騎馬不緊不慢地追上,如鬼如魅如毒蛇,纏著、絞著。“跑。”他說:“本督看著你跑,日落之前跑不過這座山頭,本督打斷你的腿!”
42.7萬字8.18 1579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