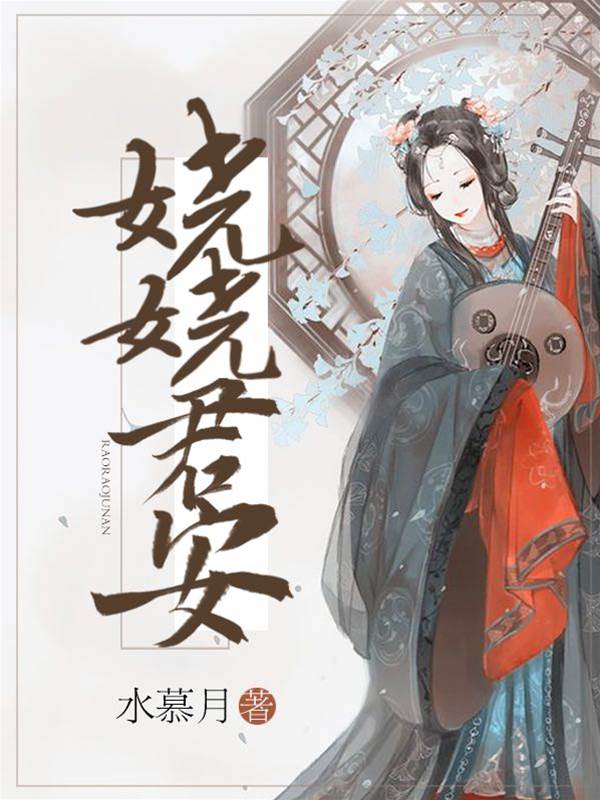《夫人救命,將軍又有麻煩了》 第182章 入圍前十
第182章圍前十
馬車之上,七人分別左右坐下之後,就你看我、我看你,一時之間沒有一人先開口說話。
之前在天寬敞的地方不顯,但一旦一群陌生的人被放在相對狹小的封閉空間當中,就有一種無形的拘束形。
社牛還得數鄭曲尺,率先打破沉默。
「諸位,敢問這坐墊如何?我讓綉娘以牛皮製了填充,坐中帶,中帶,特別適合長途跋涉的路途。」
金月立馬找到了共同話題:「這裡面放的是些什麼啊,你別說,這墊子坐著,確實比其它馬車的坐墊要舒服多了。」
他屁抬起來,又用力坐下,反覆幾次試驗。
裡面是椰棕、棉布層與棉花,耐用又紮實,不但久坐不塌,支撐更是杠杠的強。
鄭曲尺當然不會輕易告訴他們:「材料啊,暫時得先保。」
這時,木熹熹看著座位中間,放置茶幾或果盤的那張小案幾:「這不是茶幾嗎?它怎麼好像可以任意地推拉啊?」
他扯著案幾加高的邊緣,當作拉手,朝外扯著。
「這是一個臨時辦公或吃食的小案幾,但若是累了,夜間只需將它這樣拖拽出來,靠在另一邊座位上固定,再將這些可拆卸的坐墊放置上去,就可以平躺下來睡得很好了。」
摺疊板,加上的設計,在現代很普遍,但他們卻是第一次見,紛紛驚嘆不已。
「有趣,太有趣了,這樣用力一拖,它就整個出來了,還能當床板用,我看看,全部收放進去,案幾隻有一尺(約30cm)公分,但一旦拉開,卻能夠躺下我一個大男人的高。」
「對,夜間寒、荒郊襲、暴雨風雪,人自然留在馬車更安全,底層車廂它不僅能坐下八人位,還能睡下不人。」
Advertisement
「這是什麼,為什麼會有一木頭架在座位上?」
「有時候車上的人難免遇上險況,比如被追擊,馬車損急剎,或者撞上什麼東西人仰車翻,這時候人只要牢牢抓它,就可以穩住形,極大程度減傷害。」
他們就像進寶庫探寶的孩子似的,這裡,哪裡,十萬個為什麼縈繞在心頭。
他們幾人,在車上的每個角落都搜尋了一遍后,忽然打開了車窗,見馬車已經行駛了一段路程,可這過程中,他們深陷好奇探索中,竟沒有察覺到特別大的靜。
馬車以緩速前進,只比人力稍快那麼一些,但真做到了曾說的「立杯不倒」的。
「阿青,能馬車再跑快些嗎?」
他們三個一個比一個子歡,出頭來,著風速。
「可以。」對外面馭車的蔚垚道:「蔚大哥,勞煩提速。」
「沒問題。」
鄭曲尺待完之後,見四姓商賈都各自來了趣,不必再介紹之後,便也安靜了一會兒。
但還沒閑下心來,就到了兩種各不同的視線,一直地盯著。
一道是公輸即若的,他就像的機一樣,想將的剝析分解開來,看得仔仔細細,分毫分差。
一道則是彌苦住持,這一位年輕的住持長著一張普渡眾生的臉,但只是被眼所蒙蔽之過,總覺得他似貪狼,總有一種隨時準備要捕食的兇悍。
但畢竟這只是一種虛無的覺,倒也做不得準,但目前至可以確定,這個彌苦住持並不是表面看起來那樣良善慈悲。
……煩死了,果然還是不能不聊天啊。
清了清嗓子,刻意避開這兩人,對茲商人穆哈道:「這還只是展示品,完得匆忙,還需要多多完善,你瞧,本該設計在車上的吊頂燈,邊櫃與雲朵靠背,全都還沒加上,假如買家付得起足夠的錢,便可盡量提任何要求,我都可滿足。」
Advertisement
「你的馬車,不僅設計有心思,連里的布置都藏有心思,不知這位阿青工匠,你在你們鄴國工匠當中,屬於什麼級別?」穆哈拱了拱手,好奇問道。
坐在這車裡的人,主辦方肯定已經知道是盤龍馬車幕後工匠,而這四位大商,若無意外以後肯定也是的最大合作商,鄭曲尺也就不藏著掖著,趁此機會與他們打好關係。
「我鄭青,是鄴國工匠,目前評級工匠一級,不知四位大商都該如何稱呼?」
「失敬失敬,原來你竟然已是工匠——」穆哈表徒然僵滯住了。
、剛說啥?!
其餘三人倏地將腦袋了回來,同時瞪大眼睛看著鄭曲尺。
「你方才說什麼?!你是工匠一級?是我聽錯了,還是你說錯了?」
這事本就瞞不了任何人,也大大方方承認道:「你們沒聽錯,我也沒說錯,這事,有這麼驚奇嗎?我以往獨居深山進修,不理山下俗事,出師后才知,原來當木匠還得考核評級。」
將上的疑點都合理化,再打造出為苦練技藝,久居山中、不諳世事,來打消別人對於種種世、來歷的探聽。
他們一聽這話,那就是滿臉的「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都覺著是在開玩笑。
直到鄭曲尺將工匠一級的牌子拿出來,擺在他們面前之後,他們才不得不信。
陳敗看著,到了驚嘆:「鄭青,你們鄴國工匠,難道都像你這麼厲害嗎?我好久沒到鄴國去了,以往總聽別人說,鄴國的東西一個比一個劣質難看,所以我們陳家的商隊從不經過鄴國,可你一個工匠一級,就能夠製造出大匠水平的木來,我覺著我可能被騙了。」
這話不能當真聽,只能說陳敗在刻意捧高鄭曲尺。
Advertisement
他也知道,先前他們這些商賈各種貶低、嘲諷鄴國工匠,將人得罪死死的,這會兒不得說上些好話找補啊。
「鄴國工匠中,自有翹楚,亦有低劣,這不可否認,而我,頂多算是一般。」
謙虛過頭,也就是狂傲了哈。
「不一般啊。」
「非常厲害。」
「嚇人的。」
「干!」
三人轉過頭,齊齊看向永遠不跟隊型的茲商人。
「好啊,你在罵人?!」
穆哈了彎須,白了他們一眼:「你們講的話,跟我講的話,意思一樣一樣,憑什麼我就是罵人?」
「你們茲,難道就是這樣稱讚別人?」
「當然不是。」穆哈扶正了一下領,說道:「我這只是在表達我心的震驚,不過,我們茲雖然製造的馬車如今比不上鄴國了,但至在造船方面,那卻是你們塵莫及的。」
「有什麼了不起,我們南陳的六藝五書,還有筆墨紙硯,那是七國聞名的!」
「我們宏勝國的建築群,如七星連月湖的湖下樓閣,春洪長樓的圍欄風景,那都拍案絕的!」
「那我們巨鹿的攀雲梯、九公鹿鼎,不也是全國聞名嗎?」
這幾人在此攀比,聽得鄭曲尺簡直就是心旌搖曳,恨不能鑽進他們腦海之中觀賞一番這些景、、。
不過,好心地提醒了他們一聲:「你們就好意思在公輸大家面前說這些個?」
他們一頓口舌輸出后,這才頓醒在何,旁何人。
頓時,四人表尷尬地瞥了一眼公輸即若。
公輸即若平靜視人,他道:「各國各家,皆有超群出眾之輩,亦有巧擅專技之才,我雖承眾人恭維一句工匠魁首,但不敢自認全能,也無法以一勝百。」
這時,陳敗卻真心實意道:「哪裡哪裡,我聽說公輸大家造的千機弩,萬骨扇,還有凌雲梯,飛燕車,還有好多數不清的藝、兵,全都是頂尖之作。」
Advertisement
「對啊,咱們月家還有幸收藏了一件跗骨沉鳧,聽說北淵國的鳧軍,就是以此裝備大勝了茲船隊。」
茲商人聽了這話,臉不太好了:「公輸大家手上的兵、攻城械,全都是舉國頂尖的不錯,我茲大敗一事,只是敗於這些厲害的武之手,並非北淵國。」
「嘁,你就吧。」
聽完他們口中的各種逸聞、趣事,鄭曲尺道:「北淵,最擅長的,應該是跟巨鹿一般的戰爭械吧。」
的話,就好像一塊冰掉了沸水當中,當即氣氛瞬間降溫。
公輸即若聞言,看向了。
鄭曲尺微笑以對,令人看不清楚這句真正的意圖。
「倒也沒錯。」
他沒有否認。
鄭曲尺曾聽聞,當一個國家大力生產、囤積兵,便是為了戰爭做準備,達到侵略的目的。
囤積軍火往往意味著籌備戰爭。
而戰火蔓延,生生不息,就意味著犧牲、死亡。
想通過公輸即若了解一下,為何霸權,就容不下其它國的存在,難道戰爭是唯一的解決之法嗎?
「為何非得研發這些?難道這些戰爭械,能讓百姓吃飽穿暖、不戰苦?」
公輸即若淡淡道:「你想說什麼?」
「增進民生福祉,利於民,而大量製造戰爭械,就一定能利於國嗎?」問他。
他回答道:「不一定利國,但卻一定護國。」
鄭曲尺聽完之後,足足反應了好幾秒,才失笑道:「是啊,是我太鑽牛角尖了。」
工匠們花費無數時間雕刻出來的緻木,或許一子就能打碎。
那麼子被造出來,一定就是為了毀滅嗎?
不一定。
它也能迎擊別人的子。
他們鄴國,好像也缺「子」的,落後挨打,又何止是鄴國工業方面。
聽聽人公輸即若造的那些駭人聽聞的械,若他們北淵國真拿先進的軍事械來攻打鄴國,以鄴國的軍事防,又能夠抵擋得住嗎?
或許是對鄴國越來越有歸宿,想問題的角度,也從一開始的個人利益,演變一個國家一員,一個關注天下大事變遷、權衡利弊戰事的觀察者。
——
一番測試下來,直到規劃路線的終點,圍觀的商賈全都迫不及待奔跑過去,圍著馬車就是一番查看。
見其安然無恙,除了車沾染上泥塵污穢,竟沒有翻車跟路損?
七人從馬車上下來,公輸即若第一,隨後是彌苦住持,四姓商賈,鄭曲尺墊后。
眾人迫不及待地詢問。
「怎麼樣,方才我們在外邊看,只覺馬車行駛過程中,如行雲流水一般,不知道你們坐在馬車上的如何?」
「對啊對啊,我們等在上面,都快急死了。」
他們此刻的心簡直就是兩極化,投了票的希說好,沒投的希說不好。
公輸即若對他們的提問,表現得很平靜,唯他目掃過盤龍馬車,才生髮異樣彩。
「我的,將付諸於這一柄刻刀之上。」
他走到馬車的窗子旁,呲呲,木榍掉落,一橫一豎,一撇一捺,鐵筆銀鉤,勁健雄渾。
他們靜待片刻,才將刻於馬車上的評語,一字一字讀出。
棲無風雨,無限馳驟,人生適意耳。
這句評,不得不說,囊括了穩、快與愜意,評價極高。
彌苦住持見公輸即若刻完了,便道:「公輸大家,可否借刻刀一用?」
「請。」
他走上前,攏起袖子,凝注片刻,便刻出——驕馬車如水,江勢鯨奔,山形虎踞,春風得意馬蹄遠。
他們看著上面的評語,那簡直是一個比一個誇張,一句比一句更讚。
「好!」
「當真是好啊。」
四姓商賈不給刻字,就只能口頭評價來抒發自己的心頭。
有文話的人,每一句都是含義,沒什麼文化的人,除了一個「好」字,也沒別的字表達了。
「真的、真的就這麼好嗎?」一眾商賈臉發白,似到了重大的打擊。
「的確好,可惜你們晚了一步,現在,此盤龍馬車,與你們失之臂了。」陳敗氣死人不償命道。
他的得意,讓沒投上票的商賈,此刻只想揍人。
「是我們失言了,這位阿青,你也不能不我們投吧。」
「就是啊,再給次機會吧。」
他們圍上阿青,態度跟之前簡直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轉變。
鄭曲尺問他們:「鄴國工匠的東西,你們如今覺得如何?」
「是我們狹隘了,鄴國自然是有好的工匠。」
「就是啊,樹有高低,人有胖瘦,我們一葉遮目,確實不該啊,以後誰要說鄴國製造全是殘次品,我定會上前與他們理論一番!」
鄭曲尺審視著他們此刻的「幡然醒悟」,那恨不得返回過去自己閉的樣子,終於出了一真心的笑意。
眉開眼笑,與後方牧高義他們對視。
看他們一臉呆樣地聽著所有人都在讚鄴國工匠,還傻兮兮地笑了起來,但笑著笑著,眼眶竟然就紅了。
(本章完)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042 章
農家小少奶
穿越成小村姑?好吧,可以重新活一次。 吃不飽穿不暖?沒事,姐兒帶你們發家致富奔小康。 可是,那個比她大七歲的未婚夫怎麼破?本寶寶才八歲,前不凸後不翹的,爲毛就被看上了? 退婚,他不肯;想用銀子砸他,悲催的發現,她的銀子還沒有他的零頭;想揭秘身份以勢壓他,那曾想他隱藏的身份比她牛叉一百倍!婚沒退成,反被他壓… 本文一V一 求收藏求抱養 已有完結文(親孃不
96.7萬字8 235303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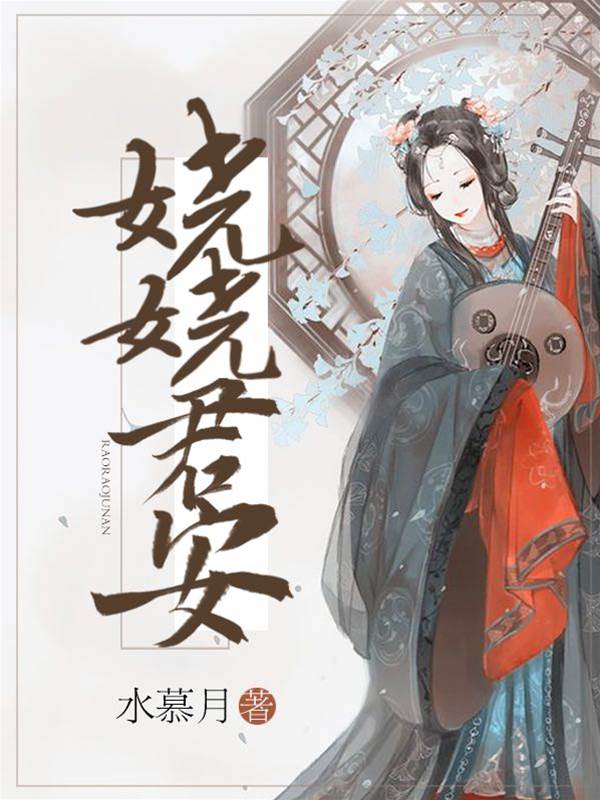
嬈嬈君安
原想著今生再無瓜葛,可那驚馬的剎那芳華間,一切又回到了起點,今生他耍了點小心機,在守護她的道路上,先插了隊,江山要,她也絕不放棄。說好的太子斷袖呢!怎麼動不動就要把自己撲倒?說好的太子殘暴呢!這整天獻溫情的又是誰?誰說東宮的鏡臺不好,那些美男子可賞心悅目了,什麼?東宮還可以在外麵開府,殿下求你了,臣妾可舍不得鏡臺了。
16.6萬字8 14823 -
完結152 章

本王在此/與鳳行
身為魔界銜珠而生的碧蒼王,沈璃的一生是璀璨而奪目的但在她千歲誕辰之際,政治聯姻的魔爪劈頭蓋臉的撓過來九十九重天上的帝君一紙天書頒下著碧蒼王與帝君第三十三孫拂容君定親拂容君早年便因花心而聞名天外她堂堂魔界一霸,一桿銀槍平四海戰八荒,豈能嫁給那種花心草包!這婚必須逃!沈璃不想,這一跑還真碰上了那個不屬于三界五行的男子那男子,當真……奇葩
25.2萬字8 2610 -
完結137 章

乖!嬌嬌別逃!瘋批暴君低啞纏哄
【又名《嬌鳳歸鸞》】【雙重生+雙穿越+病嬌+雙強+團寵+甜寵爽文】 前世慘死穿越去現代后,云梨竟又穿回來了,睜眼便是洞房花燭夜! “阿梨……你為什麼不能試著愛我?” 病嬌攝政王掐著她的腰,眼尾泛紅,發誓這一世也要用命寵他的小嬌嬌! - 世人皆知,暴戾攝政王娶了個草包。 卻沒料到,夜夜在王爺榻上撒嬌耍賴的禍國妖妃,對外卻是明艷驕矜的打臉狂魔! 翻手為醫,覆手為毒…… 不僅前世害她滿門覆滅的人要血債血償,天下英才更是對她甘拜下風! 就連小皇帝也抱緊她的大腿,“嬸嬸如此厲害,不如將那攝政王丟了吧。” 某攝政王:? 他不悅地將小王妃摟入懷,“聽聞我家小阿梨想造反,從此妻為夫綱?” 云梨摟著病嬌夫君的脖頸,“有何不可?畢竟我家夫君的小字比阿梨還要可愛,對吧……容嬌嬌?” - #夫君總把我當小嬌嬌,怎料嬌嬌竟是他自己# - 封面底圖已獲授權:十里長歡-瑞斯、儲秀云心-蟬火。
23.5萬字8.17 113 -
完結107 章

困春鶯
溫幸妤打小就性子呆,脾氣軟。 唯一幸運的,是幼時蒙定國公府的老太君所救,成了貼身婢女。 老太君慈和,經常說:“等幸妤滿十八,就許個好人家。” 溫幸妤乖乖應着,可目光卻不由看向了窗外那道神姿高徹,瑤林玉樹的身影。 那是定國公府的世子爺,京城裏最矜貴多才的郎君,祝無執。 也是她註定靠不近、撈不着的寒潭月影。 —— 溫幸妤出府不久,榮華百年的國公府,一夜傾頹,唯剩祝無執被關押在大牢。 爲報老太君恩情,她千方百計將祝無執救了出來,頂了將死未婚夫的身份。 二人不得不拜堂成親,做了對假夫妻。 她陪他復仇雪恨、位極人臣,成了人人欽羨的攝政王夫人。 可只有溫幸妤自己知道,祝無執一直對她頗爲嫌棄。 她雖委屈,卻也知道假夫妻成不了真,於是放下和離書,遠走高飛。 —— 祝無執自出生起就享受最精細的侍奉,非白玉地不踏,非織金錦不着。 他是目下無塵的世子爺,是孤高自許的貴公子。 直到家族傾頹,被踩入泥塵後,救他的卻是平日裏頗爲嫌棄的呆笨婢女。 爲了掩人耳目,他成了溫幸妤的假夫君。 祝無執看着她掰着指頭算還有幾天口糧,看着她面對欺凌忍氣吞聲,唯唯諾諾。 一副沒出息的模樣。 他嫌棄她粗鄙,嫌棄她呆笨,嫌棄她因爲一捧野花就歡欣雀躍。 後來他做探花,斬奸佞。先帝駕崩後,挾幼帝以令諸侯,成了萬萬人之上的攝政王。 世人都說,他該娶個高門貴女。 可祝無執想,溫幸妤雖呆板無趣,卻勝在乖巧,他願意同她相敬如賓,白頭到老。 可等他收復失地回府,看到的卻是一封和離書。 —— 小劇場: 在外漂泊的第二年,溫幸妤累了,決定在雪城定居。 那夜大雪紛飛,寒風肆虐,她縮在被窩裏怎麼也睡不着。 忽而聽得屋門被人敲響,她恐懼之下提了刀,眼睜睜看着劍尖入縫挑開門閂,門倏地被風吹開。 冷風夾着細雪灌進門內,她用手擋了擋,擡眼看去。 只見那人一身與雪同色的狐裘,提燈立在門外,眉睫結霜,滿目偏執瘋狂。 “敢跑?很好。”
39.7萬字8 9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