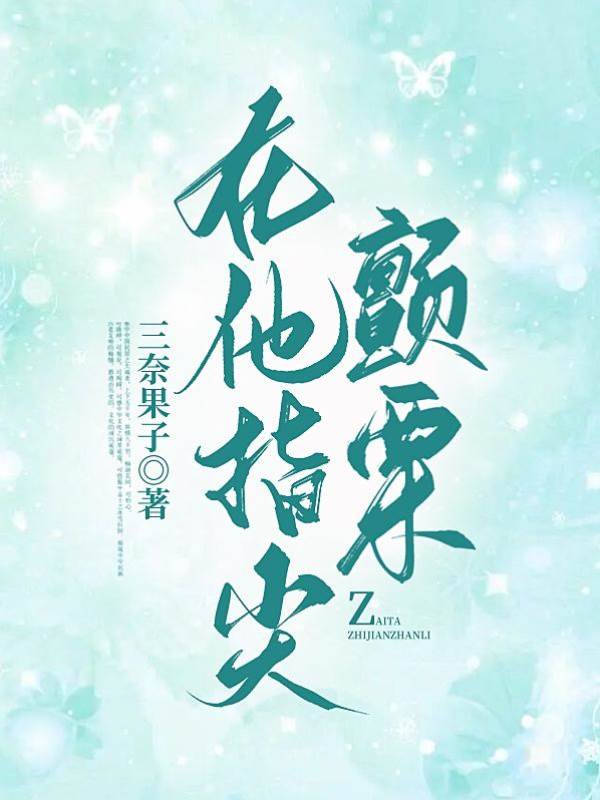《深情眼》 第38頁
葉濛點頭,不過並不打算跟他深度流下去,難得出自嘲的表:「我本來就不是完的人,我自私,貪婪……」
你還好。李靳嶼在心裡默默補了句。
「但我想讓你開心。」葉濛很坦然也很直白地說。
李靳嶼愣住,他說不上來是什麼覺,就好像那凝固冰封的一角,正在被什麼東西化。
葉濛現在倒是紳士起來了,「如果你不對剛才的行為追責的話,我就先走了。」
「什麼追責?」
「我在沒有經過你的同意下,親了你,說實話,這算是擾,」真是相當有自知之明,拿出了電話遞給他,「你需要補償,還是需要報警?」
還真是……讓人哭笑不得。
屋外的音樂已經換了一首,仍然很低靡。李靳嶼側過,耳機依舊掛在脖子上,他拿後背頂著牆,雙手朝在兜里,低頭沉默片刻,下沖門外一點,看也沒看說:「走吧。」
葉濛坐上車,表並沒有很高興,相反,懊惱極了。從來不是這麼衝的人,做事就算大刀闊斧的,但至還是個會給自己留餘地的人,剛剛那下也不知道是什麼上腦,把自己都給整蒙了。
李靳嶼要是真報了警,那現在坐得可能就是一輛警車。想到這,額頭直冒冷汗,這要是被當擾犯給帶上警車的話,只能厚著臉皮回北京繼續給勾愷當狗了。
倒也不是怕什麼,這人從來不束管教,就是怕老太太給氣暈過去。
「你喜歡那小子?」程開然終於忍無可忍地開口。
兩小弟坐在前頭,安安靜靜開著車,眼神是不是瞄了眼後視鏡里的兩人,隨時警惕這詭譎的氣氛,半晌,葉濛回過神,偏頭看窗外,置若罔聞地糾正道:「他比你大,給我支煙。」
Advertisement
現在閉上眼,渾都是李靳嶼的氣息,他的很薄,形清晰明顯,卻出人意料的。
程開然怨氣十足地狠狠砸過去一支,摔在葉濛手上,眼神輕蔑地說:「不是我在背後說三道四,但李靳嶼這人,就不是什麼好男人,渣得很,鎮上這些三姑六婆都被他哄得服服帖帖,就他唱歌的那個酒吧,前幾天我還撞見他跟一的在廁所里打野炮。「
「我知道,「葉濛了口煙,淡吐著菸,眼神微微一瞇,「還有別的嗎?」
程開然覺得這時候的葉濛太迷人,他的無力頓時油然而生,他是最卑微的暗者,他以為自己偽裝的很好,但這會兒他莫名覺得,眼前這個人一定都知道。
「他的料,我三天三夜都不完,」程開然不想讓葉濛覺得自己對李靳嶼徒生歹意,於是緩了緩神,語氣誠懇地說,「他這個人很瘋起來很瘋的,沒人攔得住。你別看他現在對老太太這麼好,他又不是真孝順。他前幾年剛來的時候,跟人打架,把人打了個半殘,現在還在醫院躺著。老太太賠了幾十萬,人家才沒讓他坐牢。不然,現在也就是個勞改犯。」
難道李靳嶼騙?當初說他媽給了老太太一筆錢,其實不是捐給福利院,而是給他賠償去了?
「年輕狂,誰沒犯過錯。」葉濛不甚在意地撣了撣菸灰。
程開然強下的怒火又拱起,像一隻隨時會炸的氣球,說話也惡毒起來:「好,你非要找他是吧?鎮上這麼多正經男人你不找,你要找個沒錢沒勢,除了長得像個花瓶,渾上下一無是活得像條狗一樣的男人是吧?」
Advertisement
葉濛笑了笑,輕描淡寫地說:「是啊,找他也不找你。」
程開然錯愕地看著,大腦突然就空白了,真的什麼都知道,他以為他掩飾的很好,以為會裝傻一輩子,如今,為了李靳嶼,終於挑明了是嗎?
眼前的景象越來越的悉,葉濛將煙撳滅,讓小弟把車停在路口,當然小弟不聽的。葉濛從包里掏出一張銀行卡和一張名片遞給程開然,「開開,去北京把臉上的疤消掉吧,這個醫生可以幫你,他技很好,我有個同事臉上跟你一樣,現在已經跟正常人一樣了。」
程開然遲遲不,他不接,他覺得他接了這張卡,他跟葉濛之間真的就徹底兩清了。良久,他蠕:「什麼意思?」
葉濛往前送了一下,又說:「我媽的事你不要管了,你好好過你自己的生活,咱們之間,以後誰也不欠誰,我媽的死,跟你無關。真要怪到別人頭上,那也只能怪我,怪我不是男孩。」
「你要為了他,跟我斷絕來往?」程開然不敢置信,又猛地拔高音量確認了一遍,「是嗎?」
「因為他不想得罪你,總是拒絕我,」葉濛隨口警告了句,「開開,你要是敢他,你知道我的,我瘋起來,也沒人攔得住。如果有任何人找他麻煩,我都算在你頭上。」
程開然是非常了解葉濛的,葉濛寵男友是真的寵。高中那時候跟一個長得很漂亮的小學弟在一起,其實看不出來葉濛有多喜歡那個小學弟,但就是把人寵得天上有地上無的,誰都不敢得罪。後來分手也是真冷,照樣見吃喝玩樂,也不曾見有什麼難過的。倒是那個小學弟,一開始看著高傲的,誰也不搭理,後來放不下求和的還是他。
Advertisement
所以,跟李靳嶼這種頂多也就算個乾柴烈火。燒完就完事。
=
楊天偉破天荒地被選了青訓營,馬上就要去北京參加集訓。葉濛好心辦壞事,老太太這邊徹底沒人照顧,李靳嶼不想花錢請看護,日夜都是自己照顧。加上轉病房後,費用會比這邊貴上很多,他除了給自己賣,實在想不到有什麼來錢快的辦法。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300 章

穿成大佬的反派小嬌妻
醜到不行的沈從容穿書了。穿成膚白貌美,身嬌體軟,一心隻想給老公戴綠帽子的富家小明星。每天想著要蹭熱度,捆綁上位的娛樂圈毒瘤。全娛樂圈都知道沈從容矯揉造作,最愛艸小白花人設直到某個視訊上了熱搜……眾人眼中的小白花徒手乾翻五個大漢。網友狂呼:妹妹!你崩人設啦!當晚,癱在床上的沈從容扶腰抗議:「人家體弱,你就不能心疼心疼?」薄翊挑眉,摸出手機開啟視訊:「體弱?」沈從容:嚶嚶嚶……她要找拍視訊的人單挑!
186.5萬字8 14320 -
完結1181 章

分手后,她藏起孕肚繼承億萬家產
葉芷萌當了五年替身,她藏起鋒芒,裝得溫柔乖順,極盡所能的滿足厲行淵所有的需求,卻不被珍惜。直到,厲行淵和財閥千金聯姻的消息傳來。乖順替身不演了,光速甩了渣男,藏起孕肚跑路。五年後,她搖身一變,成了千億財…
205.2萬字8.18 79263 -
完結357 章

心聲暴露後,瘋批千金作成小心肝
【穿書 讀心術 吃瓜 沙雕 1v1】溫顏穿書了,穿成為了男主,竊取聯姻老公司墨衍文件機密、惡毒又作死的女配。她還綁定了一個吃瓜且讓她做任務的係統,她需要獲取司墨衍100好感值,才能活命。不近女色、且早就對她厭惡至極的司墨衍,直接提出離婚。“老公,我們不離婚,以後我隻愛你好不好?”【公司被搶,腰子被噶,要不是為了活命,我才不想撩你這個短命鬼呢!】“大哥,你別被這個女人蠱惑,我支持你跟她離婚。”她掃了眼司墨衍當導演的二弟。【戀愛腦,綠帽龜,難怪最後人財兩空,還被送去非洲挖煤,最後慘死在異國他鄉。】“大哥,這個女人就是個禍害!”她掃了眼司墨衍當翻譯官的三弟。【被人陷害,頂罪入獄,最終病毒感染折磨至死,慘。】司家小妹瑟瑟發抖:“大哥,其實我覺得大嫂挺好的。”大嫂的心聲,應該不會詛咒她了吧!【小姑子人還怪好嘞,隻可惜遇到渣男,流產四五次,家暴還出軌,最後買巨額保險將她——】溫顏隻想盡快完成任務走人,哪知司家人都能聽到她心聲,還跟著她一起吃瓜。最終炮灰命運得到改變,她也完成任務。她拍拍屁股走人,冰山老公將她抵至牆角:“誰讓你撩完就跑的?”“你不是要跟我離婚嗎?”
70.6萬字7.82 16658 -
完結10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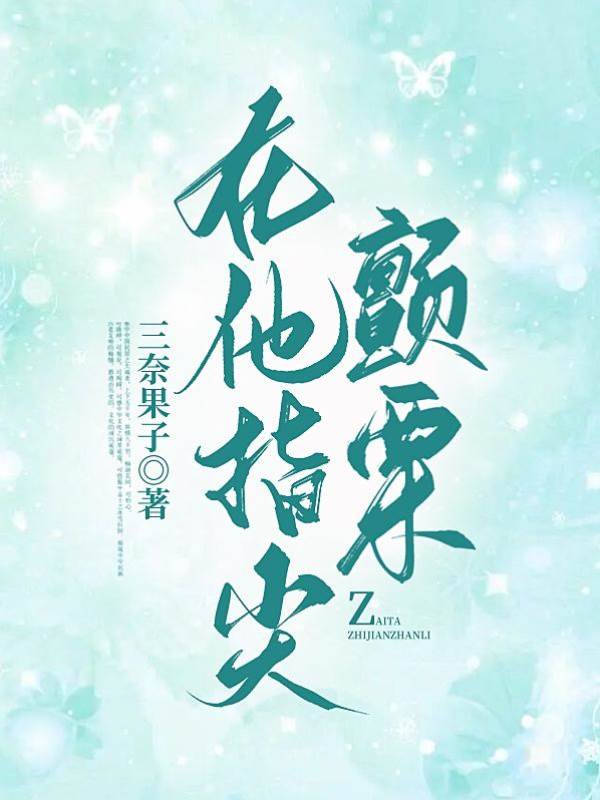
在他指尖顫栗
【美豔釣係旗袍美人VS清冷矜貴貧困大學生】【欲撩?甜寵?破鏡重圓?雙潔?暗戀?豪門世家】他們的開始,源於荷爾蒙與腎上腺素的激烈碰撞她看上他的臉,他需要她的錢他們之間,隻是一場各取所需的交易蘇漾初見沈遇舟,是在京大開學典禮上,他作為學生代表正發表講話他一身白衫長褲、目若朗星、氣質清雅絕塵,似高山白雪,無人撼動驚鴻一瞥,她徹底淪陷人人說他是禁欲的高嶺之花,至今無人能摘下可蘇漾不信邪,費盡心思撩他,用他領帶跟他玩緊纏遊戲“沈會長,能跟你做個朋友嗎?”“蘇漾,”沈遇舟扣住她亂動的手,“你到底想幹什麽?”“想跟你談戀愛,更想跟你……”女人吻他泛紅的耳朵,“睡、覺。”都說京大學生會主席沈遇舟,性子清心冷欲,猶如天上月可這輪天上月,卻甘願淪為蘇漾的裙下之臣然而蘇漾卻突然消失了多年後,他成為醫學界的傳奇。再見到她時,他目光冷然:“蘇漾,你還知道回來?”房門落鎖,男人扯掉領帶,摘下腕表“不是喜歡跟我玩嗎?”他親吻她,偏執且病態,“再跟我玩一次。”“沈遇舟,對不起。”男人所有不甘和怨恨,在這一刻,潰不成軍他拉住她,眼眶發紅,眼裏盡是卑微:“別走……”沈遇舟明白,他是被困在蘇漾掌中囚徒,無法逃離,也甘之如飴
20.8萬字8 2982 -
完結93 章

錯加老板微信后
林淺聊了一個虛擬男友,每天對他口嗨浪到飛起,享受着調戲的快樂。 【在嗎,看看腹肌】 【我們之間有什麼事不能躺你身邊說嗎?】 【你嘴這麼硬,讓我親親就軟了】 但他續費太貴了,一個月期滿後,他答應了做她男朋友,攻略成功的林淺忍痛刪了他。 可下一秒,公司大群裏,那個冷肅嚴苛人人懼怕的總裁幕承亦,在衆目睽睽下@了她。 【@林淺,給我加回來】 林淺:……! — 林淺後知後覺自己當初加錯了微信,這一個月撩的一直都是她恐懼的大老闆慕承亦。 人怎麼可以捅這麼大的簍子? 她好不容易鼓起勇氣跟他說實話,卻被他“約法三章”了。 慕承亦:“雖然我同意做你男朋友,但我沒有時間陪你吃飯,你也不可以要求我陪你逛街,更不準強迫我跟你發生親密關係。” 林淺:…… 慕承亦:“但作爲補償,我給你幾家米其林餐廳的儲值卡和SKP購物卡,每失約一次就分別往裏面打10萬。” 林淺:我願意! 其實這個戀愛您本人沒必要親自到場談的! 每天沉醉於紙醉金迷快樂中的林淺,爲了不露餡,只能硬着頭皮繼續撩。 幾天後卻發現自己被騙了,他根本沒失約過幾次! 下班不管多晚都要跟她一起吃飯; 下暴雨也要陪她逛街; 每天還把她按在辦公室的門上親! 一次酒後,她沒抵住他的美色,佔了他的便宜。 第二天晚上,想死遁逃走的林淺被攔腰抗回了牀上,高大身影欺壓而下,調出她手機裏的虛擬男友購買記錄,聲音沉暮透着寒氣。 “說說看,哪個是你買的虛擬男友?” 林淺:“……你。”
23.3萬字8.18 16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