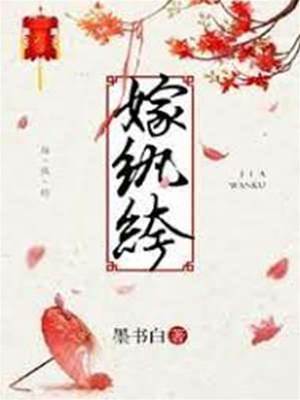《別院私逃後,瘋批權臣怒紅眼》 第123章 “原來夫人連自己的夫君是誰都不記得了”
冰冷的雪花撲簌落在薑映晚眼睫上。
融化的雪水刺骨冰涼,仿佛暗的蛇吐著信子從眼瞼至周,鑽心刺骨的冷仿若將所有湮滅呼吸的驚懼由至外全拖曳出來。
低的烏睫停頓一剎。
隨即得更厲害。
連帶著,全都在明顯地發抖。
抗拒他的靠近,抵他的強迫。
的本能拚命提醒後退,可所有逃離的作像被什麽東西牢牢桎住一般,任憑用盡全力氣也彈不了。
而一步步近的裴硯忱,卻仿佛沒發現的害怕,似是而非地諷刺笑著,語氣戾如冰淵,沉沉睨著慘白的臉。
“這種窮鄉僻壤的落後小鎮,夫人選在此再嫁二夫,還真是——會委屈自己。”
紫煙的驚恐並不比薑映晚的。
在裴硯忱距離僅有兩丈之餘時,從深懼中回神的紫煙,下意識地抓著薑映晚的手臂本能地想拉著往後逃。
然而作還未作出,裴硯忱手起劍落,一串跡在眼前揚起又迅速墜落,骨的劇痛遲鈍傳來,手臂上外翻的淋淋傷口蔓延至全。
Advertisement
紫煙瞳孔劇震,疼到極致的麻木讓抓著薑映晚臂彎的手失力般鬆開。
“紫煙!”薑映晚本能地側去扶,還未到,腰驀地一疼,攥骨箍筋般的疼痛讓不自覺擰了眉。
“裴硯忱!”咬牙回頭,冰冷栗的目對上他沉沉下來的漆眸。
裴硯忱對眼底的抗拒視而不見。
徹骨冰寒的指骨慢條斯理地過側臉,隨即一把慣住盈白的下頜。
就像心來地玩笑般,玩味地對說著:
“夫人既要二嫁,自要風風才是。”
“這小院中的紅綢不夠豔,漫天的大雪也不夠喜慶,為夫替夫人添些紅豔如何?就當——”
“為夫送夫人再嫁的賀禮了。”
“夫人說,可好?”
薑映晚抖如糠噻,院打鬥間,廊下的紅綢不知何時被斬斷一截,像條破布般被踩進雪地中,和雪麵上的鮮混合在一起,在漫天火的映照出,一時竟分不出,哪裏是,哪裏是破絮般的紅綢。
薑映晚從不知道原來可以這麽冷。
Advertisement
比如墜冰窟,還要冷上千倍萬倍。
急促斷續的呼吸間凝出的霜白霧,讓看不清咫尺間裴硯忱的眸。
“怎麽不說話?”他似終於不滿始終的沉默,也厭惡極了這刺眼到極致的嫁,掐著下頜的手指力道收。
箍得生疼。
裴硯忱沉沉笑著,近。
難得好心地問:
“為夫將這些人都殺了,用他們的,賀夫人這場大婚,如何?”
薑映晚眼底發紅,全抖著,咒罵看向他,語氣中恨意明顯。
“裴硯忱!你簡直是個瘋子!”
他冷“嗬”出聲,慣著下頜的指骨倏地用力,疼得眼底瞬間蓄了淚。
“夫人不是早就知道了嗎?”
重傷短暫昏迷掙紮著醒來的容時箐,抑咳著中的,努力想掙後黑甲兵,於大雪中往薑映晚這邊看來。
“晚晚……咳咳!”
薑映晚眼眶中的淚重重砸在地上。
看也未再看裴硯忱一眼,用盡全力氣掙開他,拔就往容時箐那邊跑。
Advertisement
但剛走了沒幾步,手腕被人從後重重箍住。
力道大的,薑映晚甚至懷疑腕骨碎了。
裴硯忱麵上那抹零星的冷笑終於不在,他攥著薑映晚不準再掙紮半步,森寒不斂殺意的眸子冷冷掃向容時箐那邊,沉下令:
“帶下去!連夜遣押京城,押至刑部嚴審!”
黑甲兵齊齊應聲。
容時箐和他後的心腹立即被帶走,冷風蕭瑟的小院瞬間空下來。
“時箐哥哥!”
薑映晚焦急地看著容時箐被押上囚車,瘋了般拚命拍打裴硯忱,想掙他的桎梏追出去。
“放開!”眼尾猩紅得厲害,“你放開我!”
裴硯忱詭譎漆沉的黑眸冷下來。
眼底鷙得駭人。
“一年的時間,看來夫人連自己的夫君是誰都不記得了!”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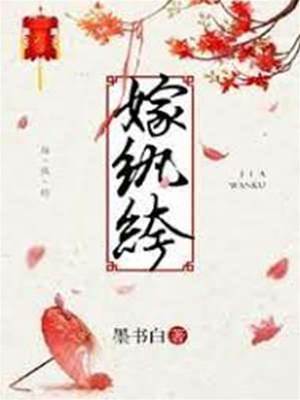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50163 -
完結2933 章

領袖蘭宮
入宮了,她的願望很簡單:安安靜靜當個小宮女,等25歲放出去。 可是!那位萬歲爺又是什麼意思?初見就為她 吮傷口;再見立馬留牌子。接下來藉著看皇后,卻只盯著她看…… 她說不要皇寵,他卻非把她每天都叫到養心殿; 她說不要位分,他卻由嬪、到妃、皇貴妃,一路將她送上后宮之巔,還讓她的兒子繼承了皇位! 她后宮獨寵,只能求饒~
449.3萬字8 89937 -
完結1135 章
逆天神妃
她是華夏的頂尖鬼醫,一朝穿越,成了個被人欺辱至死的癡傻孤女。從此,一路得異寶,收小弟,修煉逆天神訣,契約上古神獸,毒醫身份肆意走天下。軟弱可欺?抱歉,欺負她的人還冇生出來!卻不知開局就遇上一無賴帝尊,被他牽住一輩子。 “尊上!”影衛急急忙忙跑來稟報。躺床上裝柔弱的某人,“夫人呢?”“在外麵打起來了!夫人說您受傷了,讓我們先走!她斷後!”“斷後?她那是斷我的後!”利落翻身衝了出去。
141.4萬字8 4736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