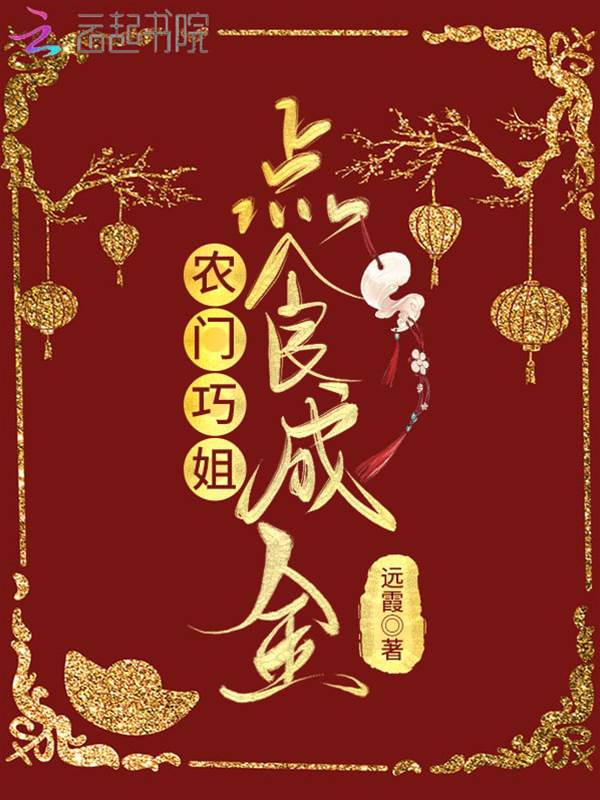《繼妻》 第 51 章 第 51 章
霞帔還好繡,幾個繡娘連夜也能完工,難就難在冠,如今太后主意一拿,皇后心頭寬松,
“那媳婦就不叨攪您,您且歇著,媳婦去尚宮局督工。”
待影消失在簾后,瞿太后幽幽失笑,“慕首輔明日大婚,今夜整個京城皆是忙碌不堪,誰還有功夫睡覺呢。”
瞿太后所料沒錯,西市東市各商鋪燈火煌煌,小廝們忙著往馬車里堆資,掌柜的手執貨單一樣一樣核對,見哪個手腳慢了,或拿錯什,掌柜的便吹鼻子瞪眼一陣喝罵。
明明了夜,竟是比白日還要喧嘩,幾輛馬車急急奔馳,不小心在門口撞了一路,待要爭先出過龍檻,細問皆是往慕府和崔府去的,不由哭笑不得。
漕運碼頭的船只穿梭不歇,燈塔高聳,探照黑夜深,只見幾艘運海貨生鮮的大船徐徐駛來,一穿著短褐的老漢,眺到悉的標識,不由奔至顯眼,沖甲板上的船夫揮旗大喊,
“快些,快些,都給我利索點,慕首輔明日大婚,咱們連夜就得將螃蟹水蝦烏墨魚等送去府上,你們若是耽擱了吉時,小心腦袋!”
通往永興坊慕家的大道,炮竹聲聲,車馬不絕,為此國公府并慕府大小數門齊開,前門后巷皆是被燈籠照得亮,穿著深褐服飾的管事,引頸張,紛紛對接各自所領之事,雖是人頭攢攢,擁不堪,卻也井然有序。
慕家大夫人沈氏并二夫人蘇氏坐鎮風水堂,腳邊擺著一盆銀屑炭,一雕玉琢的蹲在那里,用鉗子撥火,炭火燒的正旺,映得滿面通紅。
二位夫人膝蓋上均擱著暖爐,卻是沒工夫暖手,每置完一樁事便提筆勾掉,堂婆子穿梭不歇。沈氏管務,蘇氏理外務。婚事雖在隔壁國公府舉行,可慕府這邊也有宴席,上下俱是張燈結彩,不許疏。
Advertisement
崔沁“一切從簡”四字,到了慕家這里,便比過年還要熱鬧,蘇氏將最后一疊請帖遞出,不由松了一口氣,
“三弟也真是的,原先不在意,多瞧幾眼的功夫都沒,如今放在心尖上,只恨不得將捧在掌心寵,可人好生羨慕呀。”
沈氏筆耕不輟,抬眸瞥了一眼,失笑道,“今時不同以往,三弟妹這一回過門可不比上一回,可是三弟費勁千辛萬苦求回來的,倘若一不合意,若是要甩臉,我們這些嫂嫂都得著,你且要收斂子,你兩個兒子前程,并我們軒兒瑾兒,悉數得靠三弟提攜,你再不許糊涂了。”
不等說完,蘇氏已然不快,雪帕都被揮薄扇,尖著嗓子道,“哎呀呀,我曉得啦,定是好生捧著哄著,絕無二話。”
沈氏嗔笑不語。
經歷這麼一遭,蘇氏與沈氏也算是徹底歇了心思,只求與三房多親近親近,今后靠著崔沁與慕月笙提攜子嗣。
崔沁如今可是嘉寧縣主呢,被賜冠霞帔,這份榮常人塵莫及。
別以為只有慕府和崔府忙碌,便是城中各宦府邸聞訊,連夜備禮,夫人們將往年給慕府的禮單拿出來參詳,卻被老爺們搖頭拒絕,
“你也不看看國公爺這次是什麼排場?陛下親封的縣主,宮里頭如今連夜在趕制冠霞帔,你還循著舊禮自是不,加一倍,次的不能要....哦,等等,且去隔壁李侍郎家打聽打聽,斷不能落人下乘。”
也不只誰一家聰明,畢竟這回規格不一般,大家心里都沒底兒,于是乎,管家們相繼串門走戶,職差不多的,相互通個氣,誰也不想跌面子。
Advertisement
闔家主母主君皆為此忙碌,姑娘們都急匆匆將箱底的首飾裳給拿出來,一一試穿,好為明日赴宴做準備。
還真就應了瞿太后那話,沒一家閑得住。
比起外頭紛紛擾擾,容山堂次間倒是靜謐如斯。
慕月笙跪在朝華郡主跟前,親自等寫下請婚書。
明日他去迎親,得手捧請婚書遞于崔棣,崔棣寫下一個“允”字,他方能將崔沁迎出門。
燈芒下,他廓深邃而冷雋,帶著幾分鄭重,靜候老夫人下筆。
須臾,老夫人將請婚書一筆一劃寫就,遞給他,聲吩咐,
“笙兒,這家里的事你不要擔心,葛俊和藍青皆是能干,你兄長嫂子也在持,不會出差子,宋婆子派人遞了話來,說是沁兒害喜嚴重,堪堪兩日便瘦了不,你將盡早迎門是對的。”
“嫁如何了?可有備妥。”
慕月笙一襲青袍,姿筆直,“兒子在金陵,便著繡娘繡好了嫁,皆安置在崔府,您且放心。”
老夫人神怔怔他,久久不語,案上的瑩玉宮燈將臉上的細紋照得清晰,到底是上了年紀,經歷過風霜,風采已不及當年,吁著氣,嘆道,
“你到底不一樣了,萬事都不用我費心,葛俊回稟我,說嫁妝也是你備好的,你早這般好,何至于吃這麼多苦,一個人孤零在外,盡冷眼。”
慕月笙閉了閉眼,悔恨織在心頭,朝老夫人磕頭不起,
“皆是兒子的錯,今后斷是不會了。”
老夫人揚了揚眸,將眼底綴著的一抹淚珠吞下,朝他連連擺手,
“迎親的喜服皆是按照你尺寸做好,你不必擔心,且去沁兒那頭陪著,明日天亮前回來便可。”
Advertisement
慕月笙再磕了一個頭,恭敬退了出去。
夜被燈芒退,稀稀薄薄懸在上空。
他站在流溢彩的長廊下,各宮燈蒙上紅紗,被寒風吹得搖晃,斑駁的影在他清雋的面容織,仿若千變萬化的畫,滿眼的喜悅耀人,竟是比那燈火還要明亮。
府忙忙碌碌,外街川流不息。
還未出生,便鬧得京城喧囂不寧,待出世,莫不是一混世魔王?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622 章
特種兵重生:獨寵冷情妃
“轟——”隨著爆炸聲響起,樓陌在這個世界的生命畫上了句點…… 樓陌啊樓陌,你可真是失敗,你所信仰的隊伍拋棄了你,你所深愛的戀人要殺了你,哈哈……這世上果然從來就沒有什麼真心,是自己妄求了…… 再次睜開眼,她成為了這個異世的一縷遊魂,十年後,適逢鎮國將軍府嫡女南宮淺陌遇刺身亡,從此,她樓陌便成為了南宮淺陌! 這一世,她發誓不再信任任何人! 十年的江湖飄蕩,她一手建立烈焰閣; 逍遙穀三年學藝,她的醫術出神入化; 五年的金戈鐵馬,她成就了戰神的傳說! 她敢做這世上常人不敢做的一切事,卻唯獨不敢,也不願再觸碰感情! 她自認不曾虧欠過任何人,唯獨他——那個愛她如斯的男子,甘願逆天而行隻為換得她一個重來的機會! 當淡漠冷清的特種兵遇上腹黑深情的妖孽王爺,會擦出怎樣的火花呢? 莫庭燁:天若不公,便是逆了這天又如何!我不信命,更不懼所謂的天譴!我隻要你活著!這一世,我定不會再將你交給他人,除了我,誰來照顧你我都不放心!你的幸福也隻有我能給! 南宮淺陌:上窮碧落下黃泉,你若不離不棄,我必生死相依!
113.3萬字8.08 137987 -
完結88 章

權貴的五指山
終其一生,霍殷只想將她困於五指山下。 【男主巧取豪奪,霸道強勢,心狠手黑,非絕對好人。】
22.7萬字8 8175 -
完結4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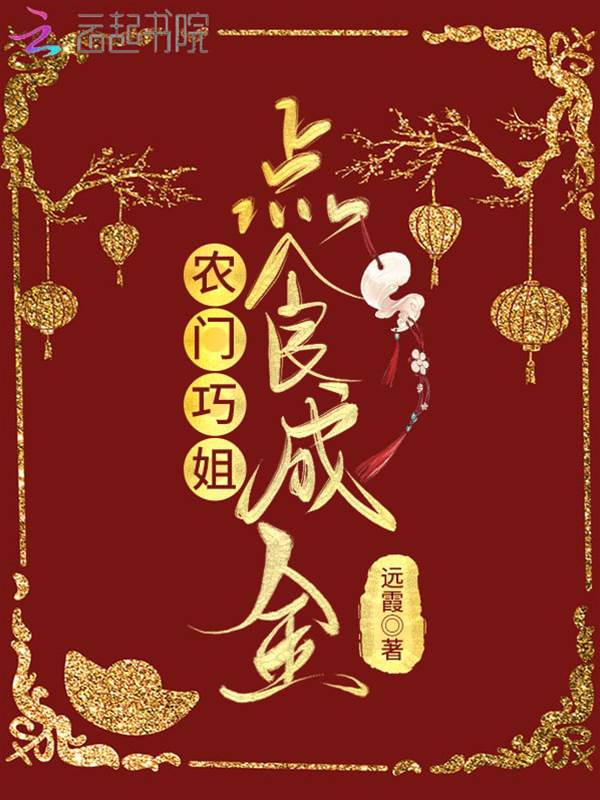
農門巧姐點食成金
高級點心師意外穿成13歲彪悍小農女-包蓉。後奶惡毒,親爺成了後爺。,爹娘軟弱可欺,弟弟幼小,包蓉擼起袖子,極品欺上門,一個字:虐!家裏窮,一個字:幹!爹娘軟弱慢慢調教,終有一天會變肉餡大包,弟弟聰明,那就好好讀書考科舉,以後給姐當靠山,至於經常帶著禮物上門的貴公子,嗯,這條粗大腿當然得抱緊了,她想要把事業做強做大,沒有靠山可不行,沒有銀子,她有做點心的手藝,無論是粗糧、雜糧、還是精糧,隻要經過她的手,那就都是寶。從此,包蓉銀子、鋪子全都有,外加一個自己送上門的親王夫君,氣得後奶一概極品直跳腳,卻拿她無可奈何。
77.6萬字8 37904 -
完結392 章
宅寧春
穿越成小官之女,娘死爹不疼,原身還特別作? 後院一群女人對她虎視眈眈、時不時落井下石,家宅安寧是奢侈! 裝天真,她會,藏拙,她會,畢竟有個疼愛縱容她的大哥。 然而...... 大哥身邊那個損友安的是什麼心? 裝傻耍賴、能玩會撩,不小心惹得她紅鸞心動......
95.3萬字8 9580 -
完結302 章

替身竟是本王自己
雙替身&追妻火葬場 全長安都知道齊王桓煊心里有個白月光,是當朝太子妃 他為了她遲遲不肯娶妻 還從邊關帶了個容貌相似的平民女子回來 誰都以為那只是個無關緊要的替身 連桓煊自己也是這麼以為 直到有一天 那女子忽然失蹤
46.5萬字8 13166 -
完結182 章

芳菲記/重生之盛寵
阿黎出生時就被睿王府討回去當兒媳婦,也就是定了娃娃親。據說是睿王府世子來吃週歲酒席,見她玉雪可愛,央着母親說要討她做媳婦兒。大人們笑過後,果真就定下來了。阿黎覺得沒什麼不好的。容辭哥哥長得好看,本事也厲害。教她讀書認字,送她華美衣裙,有時還會偷偷給她塞零嘴。後來皇帝駕崩膝下無子,睿王榮登大寶,容辭哥哥變成了太子哥哥。人人都說阿黎命好,白白撿了個太子妃當。阿黎不滿,怎麼會是白白撿的,她昨天還在太子哥哥馬車裏被欺負哭了呢。.世人都道太子殿下容辭,風姿卓絕、溫潤如玉。但只有容辭自己清楚,他是從屍骸堆裏爬出來的鬼。容辭跟阿黎做了兩輩子夫妻,可惜前一輩子他醉心權勢,將阿黎冷落在後院。他的阿黎,無怨無恨默默爲他操持家業,後來他招人陷害,阿黎也跟着慘死異鄉。上輩子重活,他步步爲營手刃仇敵,終於大權在握。轉頭想對阿黎好時,但晚了,阿黎病入膏肓香消玉隕。這輩子,他再次重生回來,早早地就將阿黎定下。權勢他要,阿黎他也要!他要寵她一世榮華!
26.4萬字8.57 3762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