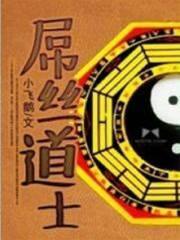《北派盜墓筆記》 第56章 皮框
山裏火映照。
“唉,皮三,哥我問你個事,你說真能死而複生嗎?”
“不知道啊陳哥,不過我看這事有點邪,你就說咱們之前從金棺銀槨裏把這東西弄出來了,當時咱們都看見了吧?那隻是癟了點,牙都在外麵了,跟兔子牙似的,還有,那臉上都還有彈呢,真他媽的滲人。”
我藏在山口,悄悄的打量看,聽他們說話。
陳建生和皮三的男人正在攀談,在他們麵前,橫放著一個巨大的半明塑料筐,塑料筐裏盛滿了,這些看著像淡的牛,是什麽不知道。
我還發現了一件事。
約的,在大塑料筐的中,有個黑影泡在裏麵,從外麵映照的廓看,這黑影像是個人......
“別!你小子不要命了!還敢這些水!”隻聽陳建生突然厲聲嗬斥。
“嘿嘿...”皮三的男人撓撓頭,“咱這不是好奇嘛,對了,還有一件事我得告訴陳哥你,這次出去後,陳支鍋的那點家當我也應該有份吧?畢竟就剩咱們兩人了,我也不貪心,給我三就行!”男人出來三手指頭。
陳建生臉上掛著笑,“自然,這事你也出力了,我答應你,三就三。”
“太好了!仗義!”皮三眼裏的興怎麽都藏不住。
“三兒啊,你不是對這東西好奇嘛,你真想看看也行,站邊上小心點,說好了,隻許看一眼啊。”陳建生笑著指了指塑料箱子。
“真的?我能去看一眼?”
陳建生點了點頭,“去吧,不要水就行了。”
Advertisement
得了準許,男人踮著腳尖,小心翼翼的走了過去。
走到塑料大水箱前,他低頭看了看,頭也不回的說:“陳哥,這水白花花的像牛,看不清啊,在哪呢?”
“在中間位置,你再仔細看看,”陳建生低沉的聲音傳來。
“中間?”
“好像沒有啊?”
接下來發生的一幕,我全在暗中看進了眼底。
隻見陳建生悄無聲息的撿起來地上的一塊圓石頭,他腳步聲很輕。
“三兒!”陳建生忽然大喝一聲。
“啊?什麽?”皮三直接轉過頭來。
“砰!”
霎那間!陳建生高舉著石頭,不偏不倚,一下子砸到了皮三的正額頭上!
一秒鍾後,兩行殷紅的鮮順著石頭流下。
皮三張了張, 噗通一聲倒在了地上,他腦門上變的模糊。
“呸!”陳建生丟掉沾了鮮的石頭,他看著地上躺著腦袋開瓢的皮三道:“三?你敢跟我要三?你算個什麽東西!半都沒有!那都是我陳建生應得的!呸!”
踢了踢皮三,見他沒什麽反應了,陳建生扭頭朝四周觀了起來。
我忙回去藏好。
好險,差點就被發現。
隨後隻見陳建生拖著皮三雙腳,把他拖到了塑料箱子前。
“三兒,安心點走吧,你那份陳哥我先替你留著,你放心吧,等你到底下見到咱們的支鍋和後勤了,你也替我帶句話,就說逢年過節的,我都會給他們燒點洋房的。”話罷,陳建生抬起了他的上半,看那架勢,擺明了是要往大皮筐裏丟!
親眼看見了人殺人,我頓時有些慌神。
Advertisement
皮三兒高一米七五左右,但他子壯實的很,陳建生可能一時手,這一下沒把人整進去,反倒是砰的一聲把皮三兒又放倒了。
這一下讓他後腦勺著了地。
沒曾想,皮三兒被磕醒了,他沒死!
“幹你姥姥!”皮三兒滿臉是,他突然掙紮著想要站起來。
陳建生慌了神,他住皮三兒,直接用雙手死死的掐住了他脖子!
皮三雙蹬,拚命的扭掙紮,把陳建生臉都抓破了。
“死!死!去死!”陳建生額頭上青筋暴起,這副模樣宛如惡魔。
不過一兩分鍾,皮三兒的臉就由紅變了紫,隨著陳建生手上的力氣不斷加大,他臉又了豬肝,他嚨裏不斷發出聲響,像是有口老痰卡住了嗓子眼。
就在這時。皮三兒的脖子一點點轉了過來。
他漲豬肝的臉,不偏不倚,和我四目相對了。
他看著我,我也看著他。
霎那間,皮三兒眼神裏仿佛充滿了驚恐,憤怒,害怕,他高高舉起來左臂,指向了我這邊。
“死吧!死吧!”陳建生仿佛走火魔了一般,毫沒在意皮三的舉。
三分鍾後,皮三兒雙一鬆不再掙紮,他眼球凸出,還在死死的盯著我!
死不瞑目!
陳建生從上翻下來,他了臉上的汗,不斷著氣。
休息了一小會兒,他把翻進了皮筐裏。
“噗通一聲。”
隨後我就看見,不過幾秒鍾的功夫,那些白的就變的像燒開了的開水一樣,不斷的沸騰冒泡。
Advertisement
腥臭味撲麵而來。
隻見,皮三兒的就像是被泡了,正一點點的在分開,在溶解!
皮,發,骨頭......所有的所有,整個過程前後持續的時間不到十分鍾。
一個大活人,最後連渣子都沒剩下!
那些還是像牛一樣白,不知道是不是我眼花了,有一瞬間,我仿佛看見裏麵泡著的黑影,頭好像了一下!
這是最完的毀滅跡!
看著眼前自己的傑作,陳建生角出一笑容,隨後,這抹笑容又被他藏了下去。
用布把塑料大框蓋住,陳建生一拍雙手,裏吹著口哨,一臉輕鬆的向我這邊走來。
他要出山!
我立即後退幾步,藏在了一塊凸出來的石頭後麵,由於我比較瘦,加上我一個勁的往回吸肚子,他剛出來,我剛藏好。
很險,剛好沒被看到。
陳建生一邊走一邊哼著小曲,他唱的歌是鄭智化的水手。
“在人欺負的時候 總是聽見水手說,他說風雨中 這點痛算什麽,幹淚 ,不要怕
至我們還有夢.....”
聲音漸行漸遠,我暗罵了聲死變態,隨後我著石壁,貓著腰跟了過去。
我很好奇山裏那個大皮筐,我知道那裏肯定藏著什麽。但我現在沒時間去看那東西,我必須要跟著陳建生。跟著他才有機會找到紅姐和孫家兄弟,我猜想他們昏迷後肯定是被分開關起來了。
“陳土工。”前方忽然有人說話。
悄悄一看,我發現說話的人是侏儒老頭邊的那兩個中年人之一。
“劍哥,”陳建生連忙彎腰。
“陳土工,你邊那個小兄弟呢,剛才你們不是一塊兒走的嗎?”
陳建生表自然,他拍了拍自己額頭,笑道:“劍哥你說三兒啊,嗨,懶驢上磨屎尿多,他突然肚疼,在上大號呢,看他那樣,估計一時半會兒的好不了,應該是吃壞了肚子,劍哥我們別等他了。”
聽了陳建生的解釋,中年男人點點頭。
“怎麽了劍哥,你看什麽呢?”說著話,陳建生也扭頭看了過來。
我著石牆,都不敢呼氣,腦門上都出了汗!
“沒什麽,可能是我的錯覺吧,最近總變的疑神疑鬼。”中年男人道。
陳建生心裏住著鬼,他便假笑著催促說:“我也覺得沒啥事,趕走吧劍哥,咱們去準備下一步。”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