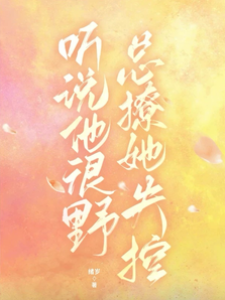《幾渡春》 498 心有餘悸
因著傷了嗓子,的聲音出不來,隻是了。
薛倡銘看不懂,又急又疑的看:“姐,你在說什麽?”
邵靖川在這時候開口,說道:“沒什麽大事,昨天就醒了,正在休養中。”
徐自行看了他一眼,微微皺了下眉,但不悅的神隻是一閃而過。他的視線,一直落在薛慕春脖子上纏著的白紗布上。
薛慕春鬆了一口氣,瞅了眼薛倡銘。哭什麽,還跑到這裏來哭。
薛慕春遭逢大難,醒來第一件事就是問楊秀,不知道的人還以為們母深,但對於薛慕春來說,關心楊秀的生死,是要知道當年車禍案的真相,還有薛才良有沒有跟說過,他當年在吉州做過的那些事。
所以,楊秀還不能死。
薛慕春坐著,一言不發,想著什麽。而薛倡銘還在關心的問有沒有哪裏不舒服,噓寒問暖的令人不適。
他們小時候還不錯,但伴隨著長大,楊秀對的利用,薛倡銘做媽寶男做得理所應當,姐弟倆的就疏遠了。尤其上一次,薛倡銘惹到了宋老板之後,薛慕春就跟他盡了。
薛慕春深吸了口氣,咳了一聲。這一咳,讓幾個人都張的盯著。
薛慕春抿了抿,徐墨突然想起來剛醒,需要醫生再過來做個詳細檢查,就出去找主治醫生了。白緋月跟了出去。
薛慕春瞧著那兩人出去,一掃看到床頭櫃上的手機,就拿過來寫:我想跟尤總談談。
徐自行看著雙手按鍵,不知怎的,臉更沉了。但不是發怒,隻是眸沉靜得很,像是心緒不佳,
Advertisement
薛倡銘靠最近,一眼看到手機上的字,看了一眼,再瞧了瞧尤珍:“尤總,說要跟你談談。”
在他看來,尤珍是亨利的大區總裁,薛慕春出事,作為合作夥伴過來探病也屬正常。隻不過,可能是關心薛慕春還能不能做總代理,可能想把換掉。而薛慕春也惦記著總代理人的份,急著表明自己的意思。
徐自行不了解尤珍跟薛慕春的關係,隻是觀察力跟腦子要比薛倡銘厲害的多。如果尤珍隻是以合作商的份過來,用得著跟著守一天?薛慕春沒欠的錢,沒必要像個債主一樣守著。按照親疏關係,完全可以晚幾天再來。
在場的,隻有邵靖川知道薛慕春與尤珍之間的關係。他沉了口氣,說道:“一會兒,等醫生檢查過之後再說吧。”
薛慕春看了他一眼,點了點頭。
片刻之後,醫生檢查完畢,確認薛慕春並無大礙,損的聲帶過幾天就能恢複。聽到這句話,徐自行才稍稍放心,又看了眼薛慕春的嚨。
去年,也是失去了聲音,被靈堂上的那一把火煙熏的。
徐自行眉沉沉,走了出去。他沒有跟其他人一樣等在走廊上,一直朝外走,像是離開了,隻是過來確認一下薛慕春的狀況。
邵靖川沉默著一言不發,白緋月這時看他的神,也看出來一些什麽了。不安的問道:“慕春……是不是在謀劃著什麽?那曹貴華,他是不是要侵吞薛家的財產被看出來了,才鬧這樣?”
薛倡銘紅著眼睛,因為薛慕春傷昏迷,大家都張的傷勢,就什麽都沒來得及說。而曹貴華那邊,他逃了,警方正在追捕。因為曹貴華已經拿了外籍,牽扯的人又涉及上層,暫時是保狀態。
Advertisement
就連新聞,對外發布也隻是簡單的說,“一名外籍人士在江城某高級住宅區涉嫌殺人,正在拘捕中”等三言兩語的詞匯。
薛倡銘了紅了的眼角,道:“不,是為了查我爸,還有爸當年的死因……我不知道,為了這件事,瞞了這麽久,一個人扛了這麽久,甚至不惜拿自己的命做餌。”
他的這番實誠話,倒是讓邵靖川高看了他一眼。
他還以為,楊秀病了之後,薛倡銘沒了給他拿主意的主心骨,這才對薛慕春表示姐弟誼,原來是被了。
不過,竟然拿自己的命做餌……邵靖川偏頭看了閉的門一眼,手指了下,真是不不怕死麽,方法那麽多,選了個最冒險的!
病房,尤珍盯著薛慕春,氣得先深呼吸了三次,這才開口訓人。
“我要是知道你這麽瘋,當時怎麽也要拉著你上車。你知不知道,再多一分鍾,你就會被他勒死!他如果有刀,或者有把槍的話,你現在就在太平間裏了!”
薛慕春咳了兩聲,用手機寫:別這麽說,咒我呢?
之所以這麽大膽行事,自己也是先做過排查的。暗中讓傭將刀都收了起來,茶幾上的果盤也擺放了隻用剝皮的葡萄,龍眼、荔枝之類的水果。
生日會上,曹貴華肯定要跟人一起跳舞,上不方便攜帶手槍、刀子之類的東西。
尤珍狠狠瞪了一眼,依然是心有餘悸。
“怎麽不按照我們計劃的來?”
薛慕春的行為,完全離了們的預設範圍。們開始設計的,隻是找到曹貴華布局殺人的證據,找到那隻手表,之後再提起申訴,推翻二十年前的舊案。
Advertisement
薛慕春抿了下,這次沉下心來,寫了長長一段字。
“曹家在二十年前,就有了左右案件的權勢。二十年後,他們的權勢隻多不減,那些跟他們在一條利益鏈上的人,肯定不願把舊案翻出來,勢必要保他們。所以,我想,不管我們拿到的證據有多,都未必能撼他們。”
“最好的方式,就是以我自己作餌,曹貴華手,把他的罪名坐死。他沒有曹典那麽沉得住氣,這麽多年,在權勢熏陶下嚐盡了好,早就膨脹。”
去年遇到的車禍,包括讓盧佳怡給盧佳期換藥,哪一件不是他心狠手辣的象征?
所以,這次薛慕春布局,不但用自己的手機拍攝他翻查薛宅的一舉一,在送來的禮盒上也了手腳,錄下了他用繩子企圖勒死的證據。
現在這些證據,都已經到了警方手上。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25 章

難以招架,裴總每天都想強取豪奪
【1V1 雙潔 強取豪奪 強製愛 男主白切黑 天生壞種 追妻火葬場】裴晏之是裴家的繼承人,容貌優越,家世極好,外表溫潤如玉,光風霽月,實則偽善涼薄,是個不折不扣的壞種。他從小就感受不到所謂的感情,不會哭不會笑,就連這條命都是拽斷了一母同胞哥哥的臍帶才留下來。裴家人都說他是沒有感情的瘋子,因此把人送到道觀養了十多年。直到他18歲那年斬獲大獎無數,才被裴家人歡天喜地接回來。都以為他會改邪歸正,殊不知,惡魔最會偽裝。*江予棠自幼性格木訥,沉默寡言,是放在人群裏一眼看不到的存在。一次偶然的機會當了裴晏之的私人醫生。都說裴晏之性格溫柔,教養極好。江予棠對此深信不疑。直到兩人交往過程中,他步步緊逼,讓人退無可退。江予棠含淚提了分手。可招惹了惡魔,哪有全身而退的道理。往日裏溫潤如玉的男人像是被惡魔附體,對她緊追不舍,把人壓在牆上,語氣又壞又惡劣,“你要和我分手?換個男朋友……”後來的後來,男人抓著她的手,小心翼翼貼在臉上,嗓音裏滿是祈求,“棠棠今天能不能親一下?”從此以後,上位者為愛強取豪奪,搖尾乞憐。【沉默寡言醫學天才女主X表麵溫潤如玉實則陰暗瘋批偽善涼薄男主】
22.6萬字8.18 17507 -
完結72 章

遲來童話
城南池家獨女池南霜從小千嬌百寵,衆星捧月,是洛城圈內出了名的矜縱任性。 偏偏在二十四歲生日這天,被池老爺子安排了一樁上世紀定下的娃娃親,未婚夫是洛城地位顯赫的謝氏掌權人謝千硯,據說明朗俊逸,只是鮮少露面。 衆人皆道這門婚事佳偶天成,老爺子更是態度堅決。 氣得她當場把生日皇冠扔在地上,放言: “我要是嫁給謝千硯我就不姓池!” 抗婚的下場是被趕出家門,千金大小姐一朝淪落爲街頭商販,自力更生。 在屢屢受挫之際,是隔壁的窮小子宋宴禮多次出手相助。 對方溫柔紳士,品貌非凡,且人夫感十足,除了窮挑不出別的毛病。 相處中逐漸淪陷,池南霜毅然決然將人領回家。 老爺子聽說後,氣得抄起柺杖就要打斷這“軟飯硬吃”小子的腿。 然而柺杖卻沒能落下來—— 窮小子緩緩轉過身來,露出一張熟悉的臉。 “爺爺,”他溫柔地笑,“不是您說,只要我把南霜追到手,這門親事就還算數嗎?” 池南霜:???
24.8萬字8 160 -
完結12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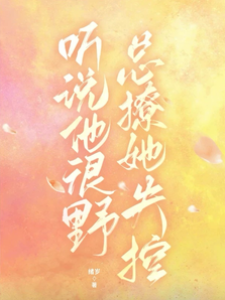
聽說他很野,總撩她失控
【真心機假天真乖軟妹VS假浪子真京圈情種】【雙潔+甜寵蘇撩+暗戀成真+雙向救贖+破鏡重圓+復仇he】 多年前,姜家被迫陷入一場爆炸案中,姜知漾在廢棄的小屋被帶回周家。 這棟別墅里住著一個大少爺,很白很高、帥得沒邊也拽得沒邊。 他叫周遲煜。 第一次見他,他的眼神冷淡薄涼,那時的她十三歲,卻在情竇初開的年紀對他一見鐘情。 第二次見他,她看見他和一個漂亮性感的女生出入酒吧,她自卑地低下頭。 第三次見他,她叫了他一聲哥哥。 少年很冷淡,甚至記不住她名字。 “誰愿養著就帶走,別塞個煩人的妹妹在我身邊。” —— 高考后,姜知漾和周遲煜玩了一場失蹤。 少年卻瘋了一樣滿世界找她,他在這場騙局游戲里動了心,卻發現女孩從未說過一句喜歡。 “姜知漾,你對我動過真心嗎?” 她不語,少年毫無底氣埋在她頸窩里,哭了。 “利用、欺騙、玩弄老子都認了,能不能愛我一點……” —— 他并不知道,十年里從未點開過的郵箱里,曾有一封名為“小羊”的來信。 上邊寫著:周遲煜,我現在就好想嫁給你。 他也不知道,她的喜歡比他早了很多年。 —— 年少時遇見的張揚少年太過驚艷,她才發現,原來光不需要她去追逐,光自會向她奔來。
22.1萬字8 9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