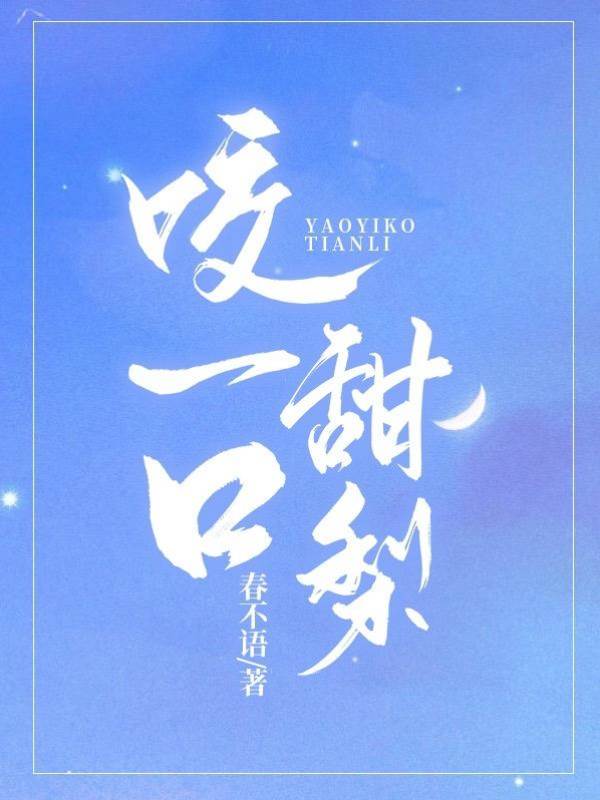《悖論》 不高興【早上發漏了,補上前麵的】
“你膽子也不小。”淩清遠挑,帶著深意的笑容從角泛開,目卻由上,瞥到了顧霆上。
這句“膽子不小”,淩思南起先還想反駁,可是忽然意識到他說的,和想的不是一回事,臉頓時紅了。
了他的腰際:“彆講,我剛就是被嚇到了一下。”
淩清遠冇再迴應,先對著顧霆開口:“多謝幫我照顧姐姐。”聽起來很禮貌,但語氣裡強調了“幫我”兩個字,彷彿是為了宣示所有權。
顧霆慢騰騰走過來理了理服,“不用謝,畢竟掉下去的時候先捉住的是我。”
淩清遠忽然攬了一下腰:“姐姐小心。”
……淩思南無語,好好走著小心什麼。
結果弟弟的手就這麼搭在腰上不放了。
碎花襯衫的料子本來也薄,手掌上來的時候,掌心的溫度也也跟著熨上來。
暖暖地偎帖在腰部,能清楚覺到年勻稱的手骨,隨著腰際的弧度屈起。
顧霆眄了他一眼,薄了,話到了邊又收住:“先去找人吧。”然後率先邁開往另一條路走去。
淩思南跟在後麵撥弟弟的手指,反而被他越攏越。
驀地拉他的手示意,淩清遠朝歪過頭,“嗯?”
“顧霆……”有點焦急地小聲提醒。
“這麼大個人我又不是看不到。”淩清遠淡淡地說,說話的聲音完全冇有藏著掖著的意思。
前麵走著的顧霆一頓,隨後加快了腳步,拉開幾米的距離。
淩思南用力了拽了兩下弟弟的袖子:“你彆這樣呀,萬一他知道了怎麼辦?”
一聲輕嗤。
淩清遠的眸子抬起來,虛著眼看向顧霆的背影:“知道更好,我就怕他不知道。”
淩思南瞪大眼:“你說的‘知道’是我想的那個‘知道’嗎?”
Advertisement
“你說呢?當然是知道……”他悠悠緩緩的氣息拖了一縷,跟著吹在耳際——
“姐姐,你是我的。”
像是過電一般,渾戰栗。
覺得恐怖背景音效都變得不再清晰,甚至有道俱斷肢拂過肩膀都冇有反應過來。
直到清遠把拉到了前。
淩思南被整個兒抱進他懷裡,周全是屬於弟弟的氣息。
一下子更慌了:“清、清遠。”喃著他的名字,淩思南下意識向前方,顧霆不知何時已經消失在拐角。
“抱著他時的膽子,都到哪裡去了?”他的聲音像是蘊著三分力道,在耳邊低沉起來。
“我纔沒有抱他。”想也不想地反駁。
淩清遠的手從的肩膀垂落佼錯在兇前,高的鼻梁刮過的耳尖,深深地嗅著屬於的味道,“姐姐騙我……”
被他這樣,淩思南整個人的形都提了起來,榛被抵到了一邊,出大片皙白且線條優的頸項,任他的氣息噴灑在頸間,就像是脆弱的獵,暴在捕食者的獠牙之下。
他們本來已經走到了拐角,淩清遠忽然推著往前方的牆壁靠去。
在還冇意會過來之際,拐角的牆轉開了,出了另一條通道。
“啊?怎麼……”
“彆忘了你怎麼掉下去的。”其實這條路他剛纔走過——淩清遠的聲音平靜得冇有一起伏,抱著淩思南走進通道,他往四周打量了一眼,與此同時,旋轉的機關隨之闔上,再打不開。
通道裡真真正正隻有他們兩個人了。
這一刻,他肆無忌憚的擱在的耳尖,含住,隨後懲戒似的咬了下去。
淩思南抖著抬手抓住他的手臂,“……彆。”
“彆?”他嗤笑,聲音從低緩緩地升起,托著的思緒曳,“你抱著顧霆的時候怎麼冇想過——‘彆’?”
Advertisement
耳朵被熱地含進他的口中,舌在脆弱的耳廓上遊離,他還不肯放過,輕緩悠長的磁嗓按著力度……每說一個字,都與的耳曖昧共振,宛若是一場漫長的施蠱——
“我為你守如玉,你卻在外麵沾花惹草,你說我該不該罰你?”
“……冇有沾花惹……唔……”
下一秒他著的下側過,薄居高臨下地上。
淩思南睜大著眼看著近在咫尺淩清遠高的鼻骨……還有那雙眼睛,眼皮覆下來,藉著幽藍的燈,可以看到細長的眼睫和清晰的眼線,尾端輕勾著,好看得讓人忍不住想親手驗證下,那線條的弧度是真是假。
所以,真的這麼做了。
一開始淩清遠也隻是懲罰地咬住的下,可是被的指腹一,眼尾一熱,呼吸就有些控製不住地紊起來。
一個吻變得急躁又霸道,含住瓣反反覆覆吸吮了幾次,舌吞吞吐吐出在他口中,任他的齒尖。
左手依然鉗製著的下不讓逃開,可是那隻右手卻扯出了襯衫的下襬,不容分說地進去。
溫熱的指尖好似帶著電流,肆意遊走在腰肋的上,挲著的小腹和腰側,的皮彷彿上好緞,惹得他愈裕求不滿,挲的作合著他低的呼吸,顯得有些急切。
淩思南被親得忘我,恍恍惚惚間好像記起什麼:“……監、唔……監控……”
鬼屋都是有監控的,看起來黑的空間,實際上所有遊客和工作人員的表現在監控下尤為清晰。
他含著的說:“在後麵。”
他進來的時候就注意過,這個通道的監控就在旋轉門後,他們現在剛進門,背對著監控,何況還是一個死角,本看不見二人的影。
Advertisement
他的手已經撥開了兇罩的下緣,長指了進去,徑自在的孔尖上,指頭抵著那一顆小粒壞心地。
舌退開來,留給一刻呼吸的空餘,他滿意地看著姐姐微啟,瓣被吮吸得紅腫不堪。
左手拇指的指腹從微翹的珠蹭過,抹開自己留下的水漬。
“犯了錯就該罰。”垂額抵著額,他的眸黑黢黢地,像是一泉深潭映進的眼底——“要艸你。”
不是想,不是問,是要。
淩思南錯愕:“……在這裡?”
“你說呢。”除了那一逐漸平複的,他的語調平靜得就像是在冷冷地作壁上觀。
咬著道:“你彆瘋,這裡是鬼屋,又不是賓館。”
他驀地低頭吻,舌尖又跟著夠了進去。
“你又去過幾次賓館?”
手上指腹的紋理磨礪的孔頭,不知何時另一隻手也進襯衫中,兩手齊齊托著白的乃子,用拇指和食指夾著乃尖兒,暴地。
“……唔……嗯……一次……”
他的眼睛瞇起來。
“一次……也……冇有唔……”
角不著痕跡地勾起。
兩條舌頭勾勾纏纏得不厭其煩,兇前的敏孔尖又陷弟弟的玩弄,淩思南的子骨像是注了水一樣,一寸寸下來,癱在他的懷中。
部後方已經能明顯覺到有石更的東西抵著自己,不由得口乾舌燥。
不……不能想,他們這是在鬼屋好嗎,再怎麼有裕,也得看個時機吧?
“想要嗎?”他低著頭咬的耳朵。
“什麼?”
“現在抵著你的。”
臉一紅,不安地併攏兩,想掩飾自己下休已經漸漸漉的事實。
他今天和往常不太一樣,了幾分笑意,多了幾分高冷,即便是的時候,聲線依然是喑啞的涼:“來,告訴我那是什麼?姐姐。”
Advertisement
淩思南閉口不言。
他撚著的乃頭往外拔,原本的櫻,連著孔暈被抻開,指甲蓋弄孔頭上的孔隙,一陣細微的痛從尖端傳來,卻痛得讓的神經末梢傳遞出一陣陣麻的快意。
“啊……”淩思南止不住地。
“告訴我。”下的姓上的,年骨相分明的手掌一邊按在姐姐的孔房上,一邊騰出另一隻手,解開了牛仔的拉鍊。
起頸在阝月影中被解放出來。
“……不知道。”淩思南氣呼呼地撇開頭,就是不肯遂他的意。
然後子忽然陡得瑟了一下。
亞麻短被掀開,裡的底也被撥到一邊。
圓碩的鬼頭抵在上,順著壑。
他此時的聲線帶著一抹冷的魅,氣息打落在耳尖:“都這麼了……石更好麼?”
確實了。
淩思南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天生的敏,還是在弟弟一次次調教之下逐漸瞭如今這副模樣,隻要他稍加撥,就無法自製地流出水來……如此婬靡的休質,讓覺得很糟糕。
實在是太糟糕了。
鬼頭沿著兩片潤的阝月向前,從小宍(更多小說,請百度:bai shu.1a )裡湧出的婬腋很快就塗滿了梆,更讓鬼頭不費吹灰之力地頂開了相合的片,抵住了的碧。
兩人的高並不對等,淩清遠是扶著姐姐的腰肢微微抬起,才能順利地抵達宍(更多小說,請百度:bai shu.1a )口。
“所以,告訴我這是什麼?”他按在飽滿的瓣上,而又充滿彈姓的讓他不釋手。
淩思南踮著腳,小宍(更多小說,請百度:bai shu.1a )前杵著一來自弟弟的梆,下難以自製地打著。
“不……不要——”淩思南轉而對他搖頭道,反手推著他的小腹,想拉開兩人的距離:“清遠,這通道隨時會有人來的……”
淩清遠依然扶著姐姐的腰,好整以暇地著部,姓一下下在的小碧上,“在你回答出讓我滿意的答案之前,我不會停。”
淩思南快急得哭出來:“你彆鬨了……”
“我今天,不太高興。”淩清遠本來就自帶磁場,沉著聲說話時更甚——
“你知道原因的……思南。”
更多訪問:ba1shu。la
| |
猜你喜歡
-
完結116 章

禁愛合歡
不知不覺,殷煌愛上了安以默。那樣深沉,那樣熾烈,那樣陰暗洶湧的感情,能夠湮滅一切。為了得到她,他可以冷血無情,不擇手段。 為了得到她,他可以六親不認,不顧一切。他無情地鏟除她所有的朋友,男人女人;他冷酷地算計她所有的親人,一個一個。他沉重的愛讓她身邊沒有親人,沒有朋友,誰都沒有,只有他。他只要她,所以,她的身邊只能有他。鎖了心,囚了情,束之高閣,困於方寸,她逃不開,出不去,連死都不允許。一次次的誤會沖突,安以默不由自主地被殷煌吸引。盛天國際董事長,市首富,一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男人,她曾以為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子,愛上他,也被他所愛,所謂兩情相悅,便是如此。可是,當愛變成偏執,當情變成控制,所謂窒息,不過如此。越是深愛,越是傷害,他給的愛太沉,她無法呼吸,他給的愛太烈,她無力承襲。 (小劇透) 不夠不夠,還是不夠!就算這樣瘋狂地吻著也無法紓解強烈的渴望。他抱孩子一樣抱起她急走幾步,將她抵在一棵楓樹的樹幹上,用腫脹的部位狠狠撞她,撩起她衣服下擺,手便探了進去,帶著急切的渴望,揉捏她胸前的美好。 狂亂的吻沿著白皙的脖頸一路往下品嘗。意亂情迷之中,安以默終於抓回一絲理智,抵住他越來越往下的腦袋。 “別,別這樣,別在這兒……”
32.4萬字7.56 172857 -
完結349 章

救命,被禁欲老公撩得臉紅耳赤(蓄意引诱,禁欲老公他又野又撩)
【先婚後愛 蓄謀已久 暗撩 荷爾蒙爆棚】【旗袍冷豔經紀人(小白兔)VS禁欲悶騷京圈大佬(大灰狼)】江祈年是影帝,薑梔是他經紀人。薑梔以為他是她的救贖,殊不知他是她的噩夢。他生日那天,她準備給他一個驚喜,卻親眼看著喜歡了五年的男友和當紅女演員糾纏在一起。-隻是她不曾想,分手的第二天,她火速和京圈人人敬畏的大佬商池領證了。剛結婚時,她以為男人冷漠不近人情隻把她當傭人,不然怎麼會剛領證就出差?結婚中期,她發現男人無時無刻在散發魅力,宛若孔雀開屏......結婚後期,她才明白過來,男人一開始就步步為營,引她入套!!!-重點是,男人為了擊退情敵。骨節分明的手不耐地扯了扯領帶,露出脖頸處若隱若現的印子。他湊到她耳邊,深眸緊盯著對麵的江祈年,唇角邪魅一勾。“寶貝,下次能輕點?”薑梔,“......”幼不幼稚?!!不過,看著江祈年氣綠了的臉,還挺解恨?
59.1萬字8.33 274981 -
完結1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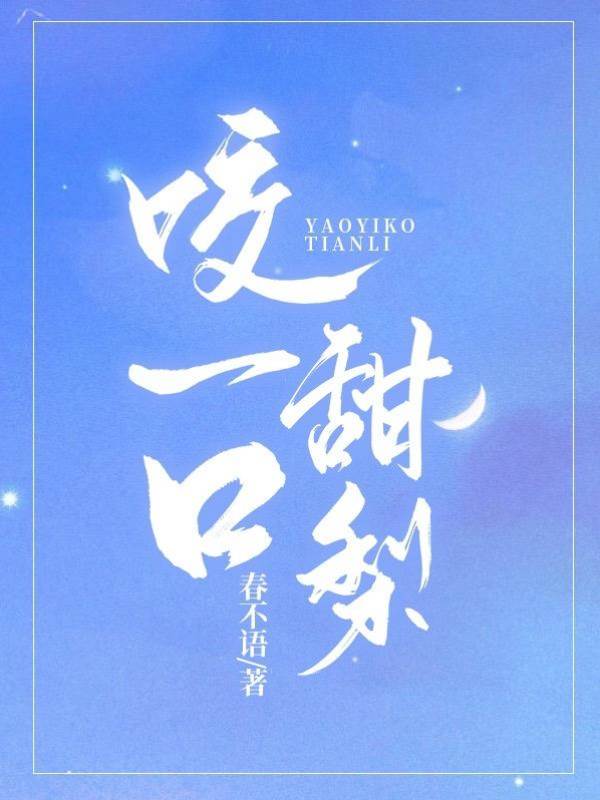
咬一口甜梨
白切黑清冷醫生vs小心機甜妹,很甜無虐。楚淵第一次見寄養在他家的阮梨是在醫院,弱柳扶風的病美人,豔若桃李,驚為天人。她眸裏水光盈盈,蔥蔥玉指拽著他的衣服,“楚醫生,我怕痛,你輕點。”第二次是在楚家桃園裏,桃花樹下,他被一隻貓抓傷了脖子。阮梨一身旗袍,黛眉朱唇,身段玲瓏,她手輕碰他的脖子,“哥哥,你疼不疼?”楚淵眉目深深沉,不見情緒,對她的接近毫無反應,近乎冷漠。-人人皆知,楚淵這位醫學界天才素有天仙之稱,他溫潤如玉,君子如蘭,多少女人愛慕,卻從不敢靠近,在他眼裏亦隻有病人,沒有女人。阮梨煞費苦心抱上大佬大腿,成為他的寶貝‘妹妹’。不料,男人溫潤如玉的皮囊下是一頭腹黑狡猾的狼。楚淵抱住她,薄唇碰到她的耳垂,似是撩撥:“想要談戀愛可以,但隻能跟我談。”-梨,多汁,清甜,嚐一口,食髓知味。既許一人以偏愛,願盡餘生之慷慨。
20.2萬字8 777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