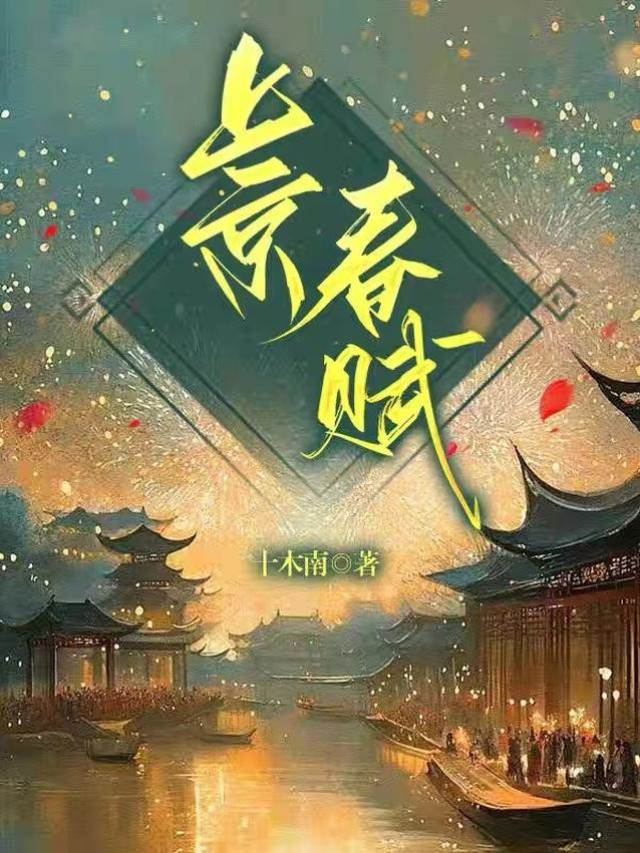《將軍寵妻手冊》 第106章
”索讓李公公退居一旁,趙恒慢悠悠纏起細布,“畢竟人遠在大音寺,公主難以顧及,你此後收到的那些消息,其實不過皆是朕讓人傳的罷了。”
“可若你並未中毒,又是如何瞞得過柳醫?”
趙恒淡淡一笑。
“朕起初是假戲真做,既是真中毒,自然無什麽瞞不瞞的。再後來,便有機會查清他是如何你挾製,再以同樣的法子對待。”趙恒道,“他既能你挾製,自然也會同樣屈服於朕。”
聽他漫不經心說完,趙安歌不由退後,手心的帕子被攥了一團。
還是小看眼前人了,竟不知自己手裏的籌碼已悉數倒戈……
可好在,這場仗還是有勝算,隻要將這宮闈控製,再宮,也不是不行。
冷笑一聲。
值此時,紅櫻從殿外匆忙跑進。待看見已坐起、似還有幾分神的趙恒時,暗暗吃驚。
“公主。”紅櫻到近旁,低聲道,“北安軍在中途了埋伏,損失近半。”
趙安歌一驚。
還未等細問,那邊的人便又開了口,“看來開始了?”
踩下床,著駭然的趙安歌,趙恒笑道:“多年前,聽聞太後曾留下一支良兵戈,朕這人,向來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於是這數年來一直苦苦搜尋,奈何無果。還是多虧公主,朕才知他們躲在哪。”
Advertisement
趙安歌皺了皺眉,“你是如何得知的?”
“以為朕病膏肓,公主放鬆戒備,行事便也愈發大膽。為殺掌握你許多罪證的段明宏,當日分明出了宮,可所有宮門皆一致說未曾有人外出,豈不蹊蹺?軍是直接朕統領,朕從未這樣發號施令過,豈不意味著軍裏有人存了異心?此後隻需派人暗中盯著公主的一舉一,想查出是誰也並不難。
”
“隻是朕沒想到。”說起此,趙恒沉沉一嘆,“北安軍是朕當年一手扶持起來,朕從未對他們起過疑心,沒想到,他們竟就是太後留下的最後一枚棋子。”
說話間,殿外打鬥聲愈漸高漲,刀劍相擊的鏘鏘之聲夾雜哀嚎,清晰落在了屋人的耳畔。
“軍六千,北安與南武原本勢均力敵,可如今你的北安軍了埋伏,損失慘重,如何與朕的南武軍相抗衡?”
趙安歌聞此冷笑。
“皇兄真是好手段,演了這麽長一場戲,騙過了所有人。”
趙恒微垂下眼簾,默了默。
倒也不是所有人……
他坐到床沿,兩手搭在膝上,背脊筆,盡顯天子威嚴。
“你如今的勝算便是城外那一千死士,而朕則要靠著那一千家軍。朕今日便與你打個賭如何?就賭城的,到底是你不畏死傷的死士,還是朕驍勇善戰的家軍。”
趙安歌略一挑眉。
Advertisement
“好。”
二人說罷齊齊看向窗外,不約而同凝起了眉。
而彼時,章楚思早已按約定帶著人到了晟京城門前,正與守城的將士對峙。
突如其來的陣仗,讓方才還熱鬧的街道,轉瞬間便靜得隻聞風聲。行人匆忙趕回家,小攤小販也扔了生計,隻為保住小命。
後是章府及各其他外戚府上的侍衛,前是守城門的將士。章楚思往前一步,將士的兵刃便跟著抬高一分,明晃晃的寒在日下閃得刺人眼。
兩方正僵持時,忽聞後馬蹄響。
眾人回過頭,便見三匹馬橫沖而來,縱使見著前頭的這一圈人,也毫沒有勒馬的舉,眾人不得不慌忙各自避開。
抵至章楚思跟前時,君行才勒馬停下,垂眸著那人。
章楚思淡淡一笑,“兩柱香,我至多能擋住兩柱香。”
點點頭,君行便又一踹獵風的肚子,越過將士沖出了城門。
褚七和紫聞的馬兒亦隨其後。
眾將士尚未回過神,隻見方才還無所作的章楚思突然高舉起一塊符牌。
“眾將士聽令,關城門!嚴防死守!絕不允許任一支兵馬再晟京!”
拿的是當今聖上的符牌,行的便是聖上命令,眾將士豈會不從,登時異口同聲應“是”,關上城門。
章府侍衛亦紛紛轉,調轉了陣營。
Advertisement
此舉讓另幾家大驚失,“章楚思!你要幹什麽!”
腹部的傷仍在作疼,饒是如此,章楚思依舊忍著不適高聲命令:“聖上有令!叛者,殺無赦!”
“是!”
寒刃相擊聲響起時,城外,褚七勒馬停住,與君行二人分道而行,徑直趕向軍營。
另二人則是一路快馬,直至趕到已來過數次的山腳下後,棄馬急步上了山。
趕至小竹屋時,石鬆正愜意躺在屋前,聞得靜,剛轉過臉,便見往日裏一臉倨傲的臭小子倏然朝自己單膝跪下。
石鬆驚得坐起,一時恍然。
“石教頭,晚輩知您留在此山林中,是對軍營不舍,那一定也知此山中哪能看清軍營轅門,還告知。”
說話間,呈上了那張字條。
石鬆接在手裏看了眼,麵冷幾分,又看麵前後生,沒再多說,起便屋子,拿了弓箭走出。
“走。”
君行猜得不錯,他留在這裏的確是因不舍。
石鬆領著二人走上小道,又穿過叢林,便到了一個。
“這裏曾是我與你父親把酒言歡之地,隻不過後來他去世,我便也再未來過。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01 章

農門醫妃:妖孽王爺纏上門
天師世家第八十八代嫡傳弟子阮綿綿因情而死,死後穿越到大秦朝的阮家村。睜開眼恨不得再死一次。親爹趕考杳無音訊,親娘裝包子自私自利,繼奶陰險狠毒害她性命,還有一窩子極品親戚虎視眈眈等著吃她的肉。食不裹腹,衣不蔽體,姐弟三個過得豬狗不如。屋漏偏逢連陰雨,前世手到擒來的法術時靈時不靈,還好法術不靈空間湊。阮綿綿拍案而起,趕走極品,調教親娘,教導姐弟,走向發財致富的康莊大道。可是誰來告訴為什麼她路越走越寬,肚子卻越走越大? !到底是哪個混蛋給她下了種?桃花朵朵開,一二三四五。謊話一個個,越來越離譜。俊美皇商溫柔地說:那一夜月黑風高,你我有了魚水之歡。妖孽皇子驕...
32.6萬字7.73 30934 -
連載1973 章

3歲小萌寶:神醫娘親,又跑啦!
“娘親,你兒子掉啦!”小奶包抱緊她的大腿,妖孽美男將她壁咚在墻上:“娘子,聽說你不滿意我的十八般武藝?想跑?”沈云舒扶著腰,“你來試試!”“那今晚娘子在上。”“滾!”她本是華夏鬼手神醫、傭兵界的活閻王,一朝穿越成不受寵的廢物二小姐。叔嬸不疼,兄妹刁難,對手算計,她手握異寶,醫術絕代,煉丹奇才,怕個毛!美男來..
177.8萬字8 17475 -
連載1305 章

和離后毒妃帶三寶顛覆你江山
虐渣+追妻+雙潔+萌寶新時代女博士穿成了草包丑女王妃。大婚當天即下堂,她一怒之下燒了王府。五年后,她華麗歸來,不僅貌美如花,身邊還多了三只可愛的小豆丁。從此,渣男渣女被王妃虐的體無完膚,渣王爺還被三個小家伙炸了王府。他見到第一個男娃時,怒道“盛念念,這是你和別人生的?”盛念念瞥他“你有意見?”夜無淵心梗,突然一個女娃娃頭探出頭來,奶兇奶兇的道“壞爹爹,不許欺負娘親,否則不跟你好了,哼!”另一個女娃娃也冒出頭來“不跟娘親認錯,就不理你了,哼哼。”夜無淵登時跪下了,“娘子,我錯了……
231.7萬字8.18 9007 -
完結15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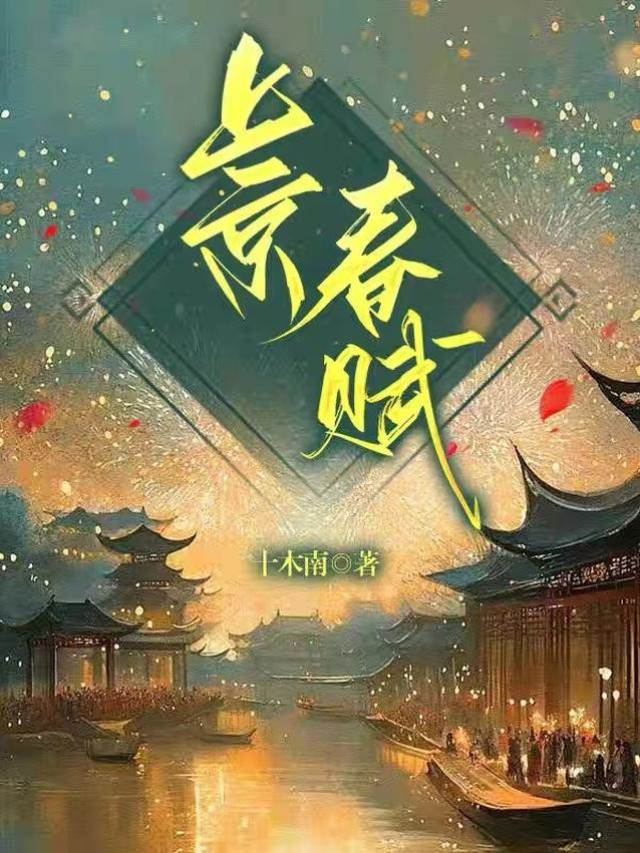
上京春賦
【純古言非重生 真蓄謀已久 半強取豪奪 偏愛撩寵 情感拉扯】(已完結,本書原書名:《上京春賦》)【甜寵雙潔:嬌軟果敢小郡主VS陰鷙瘋批大權臣】一場陰謀,陌鳶父兄鋃鐺入獄,生死落入大鄴第一權相硯憬琛之手。為救父兄,陌鳶入了相府,卻不曾想傳聞陰鷙狠厲的硯相,卻是光風霽月的矜貴模樣。好話說盡,硯憬琛也未抬頭看她一眼。“還請硯相明示,如何才能幫我父兄昭雪?”硯憬琛終於放下手中朱筆,清冷的漆眸沉沉睥著她,悠悠吐出四個字:“臥榻冬寒……”陌鳶來相府之前,想過很多種可能。唯獨沒想過會成為硯憬琛榻上之人。隻因素聞,硯憬琛寡情淡性,不近女色。清軟的嗓音帶著絲壓抑的哭腔: “願為硯相,暖榻溫身。”硯憬琛有些意外地看向陌鳶,忽然低低地笑了。他還以為小郡主會哭呢。有點可惜,不過來日方長,畢竟兩年他都等了。*** 兩年前,他第一次見到陌鳶,便生了占有之心。拆她竹馬,待她及笄,盼她入京,肖想兩年。如今人就在眼前,又豈能輕易放過。硯憬琛揚了揚唇線,深邃的漆眸幾息之間,翻湧無數深意。
25.6萬字8 29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