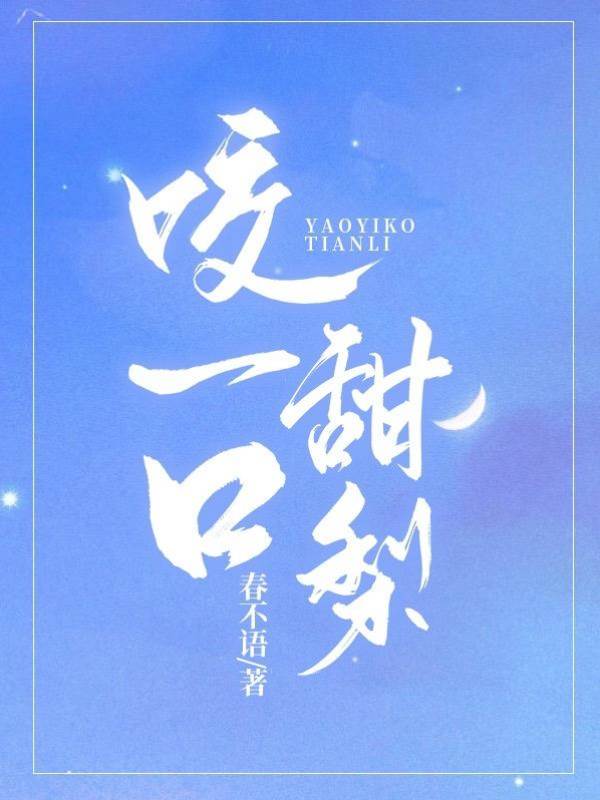《薄總,太太又跟人去約會了》 第847章 你都沒試過
言棘沒有瞞:“以前大學的一個學弟。”
顧忱曄抿了抿:“他喜歡你?”
那人看言棘的眼神明顯不對勁。
“嗯。”
“……”
回答的這麽幹脆,反而讓顧忱曄不知該怎麽接了,一口氣堵在口,半天才從嚨裏出一句話:“你喜歡那種娘裏娘氣的小男人?”
就言棘這子,喜不喜歡也看不出來,但對林栩帆的包容明顯比對其他人多,雖然有點丟臉,但也不得不承認,要是自己在麵前那麽多話還風,估計能當場把他腦袋擰下來當花盆。
人瞧著他,認真道:“他不娘,隻是年紀小,下頜線的廓不如你淩厲。還有,背後說人非君子所謂,顧公子。”
那聲‘顧公子’,尾調上揚,的諷刺意味十足。
顧忱曄冷笑:“他年紀小,下頜線不如我淩厲,你的意思是我老?還有,他都當著我的麵要搶我老婆了,你還讓我當君子?我……”
他咬著牙,生生將那句沒出口的髒話咽了回去。
言棘:“很快就要離了。”
“你想都別想,”顧忱曄恨恨的盯著,仿佛有火苗在管裏攢,讓他本來就煩了的緒愈發焦躁不安,“我不會同意離婚的,言棘,你趁早死了這份心。我和你,隻有喪偶,不會離婚。”
言棘摁下門把,推開門進去:“那趁現在你還活著,去選個喜歡的骨灰盒吧,住在自己喜歡的房子裏,做鬼也能開心點。”
顧忱曄:“言棘,你……”
不等他把話說完,麵前的門就關上了,‘砰’的一聲,震得他耳嗡嗡作響,男人盯著麵前險些怕在他臉上的門板,怒道:”言棘,誰慣的你脾氣這麽大?開門。”
Advertisement
足足過了五分鍾,裏麵也不見一靜,顧忱曄憋了一肚子氣,轉下樓了。
他恨恨的坐在客廳裏,越想越不甘心,結婚兩年,他也不過是對冷淡了些,但質上從來沒苛待過,就非得擺出一副他已經沒救了的堅決態度,吵著鬧著離婚?而且任誰被一個毫無基礎的人婚,都不會樂意,他就不能有點怨氣?
今晚沒風,偌大的別墅裏安靜極了,顧忱曄看了眼樓上,隻覺得心頭像是有什麽在突突的跳,他下外套,起去拿酒,剪裁合的襯衫勾勒出男人拔的肩背,薄而勁瘦的腰線被束在黑的西裏。
他起開瓶蓋,仰頭對瓶悶了一大口,吞咽不及,有酒從角落,順著敞開的領流進去,被浸的布料瞬間變得明,在他的口,薄薄的線條在服下若若現。
酒順著管進四肢百骸,灼熱的氣息從胃裏躥上來,喝得太猛,腦子仿佛都被薰得恍惚了一下。
“砰。”
一瓶酒喝完,顧忱曄將空了的酒瓶重重往吧臺上一放,抬腳就去了樓上,走到一半,又折到一樓來拿客房的鑰匙。一邊走,一邊憤恨的想,他明天就把家裏的鎖換了,全換智能指紋鎖,他是唯一的管理員。
……
言棘剛洗完澡,著頭發正往沙發那邊走,聽到敲門聲,順手就打開了門,看到門外拿著睡的顧忱曄,挑了挑眉:“你幹嘛?”
男人捋了下服,盡力淡淡的道:“睡覺。”
“你喝酒了?”
Advertisement
門一打開,就聞到他上濃烈的酒味。
顧忱曄低頭,在自己上嗅了嗅,“嗯。”
他越過言棘,徑直進了房間,將手裏的睡扔在床上,抬手開始解襯衫的扣子。
言棘:“??”
顧忱曄的行為太過突然,完全出乎意料,一時沒反應過來,一直到他解完最後一顆扣子,抬手準備服時,才出聲製止他:“你不會是打算在這裏睡吧?”
顧忱曄:“我們是夫妻,睡在一起是天經地義的事。”
他說這話時,表十分認真,帶著點兒矜持和傲。
言棘頭發的作一頓,抬頭迎上他的視線,一字一句,鄭重的重複那句已經說了無數遍的話:“我們已經要離婚了,顧忱曄,你是不是覺得我說這話隻在跟你鬧脾氣?”
“……”
男人抿,沒有說話,言棘可能會鬧脾氣,但鬧脾氣的對象一定不是他,所以說離婚,是真的要和他離婚。
他的結了下,沙啞著開口:“為什麽非要離婚?”
言棘像是聽到了什麽好笑的笑話,低頭‘噗嗤’一聲笑了出來,靠著一張牆而放,用來當裝飾的角桌,偏頭著漉漉的長發,大概是今晚的試探結果讓很滿意,難得有耐心跟他閑聊:“你喝的是什麽能讓你沒腦子的假酒嗎?我們沒基礎,格不合適,三觀以及對未來的規劃都不一致,你說,為什麽非要離婚?”
顧忱曄:“……你都沒試過,怎麽知道我們一定不合?”
“好,那試試,”暖黃的燈下,言棘笑得他骨悚然:“你現在就去把慕雲瑤弄死,我就信我們三觀合適,以顧公子的手段和背景,全而退應該不是什麽難事吧?要是退不了,那我們就更不配了。”
Advertisement
“……”
他想起那幾個唯慕雲瑤馬首是瞻的跟班,現在當真是一個比一個慘,破產、被包養、得艾滋,吃了上頓愁下頓,這麽多巧合,他不信沒人懷疑過言棘,而現在還好端端的站在這裏,證明那些人沒找到證據。
他們不怕言棘,但卻不敢得罪言家。
顧忱曄深深的看了一眼,皺眉:“我去弄死慕雲瑤,跟你剛才說的那些有什麽關係?”
言棘的笑容輕飄飄的,似乎隻浮在表麵淺淺的一層:“這樣就證明我們三觀合啊,都想弄死慕雲瑤,你不是不想跟我離婚嗎?三觀合,才能有更多話題聊,未來時間這麽長,要是相對無言,豈不是很無聊。”
“……”顧忱曄今晚無語的次數,比自己前半生加起來都多:“你就不覺得自己這三觀有點扭曲?誰家好人談要殺人祭天的?”
猜你喜歡
-
完結116 章

禁愛合歡
不知不覺,殷煌愛上了安以默。那樣深沉,那樣熾烈,那樣陰暗洶湧的感情,能夠湮滅一切。為了得到她,他可以冷血無情,不擇手段。 為了得到她,他可以六親不認,不顧一切。他無情地鏟除她所有的朋友,男人女人;他冷酷地算計她所有的親人,一個一個。他沉重的愛讓她身邊沒有親人,沒有朋友,誰都沒有,只有他。他只要她,所以,她的身邊只能有他。鎖了心,囚了情,束之高閣,困於方寸,她逃不開,出不去,連死都不允許。一次次的誤會沖突,安以默不由自主地被殷煌吸引。盛天國際董事長,市首富,一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男人,她曾以為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子,愛上他,也被他所愛,所謂兩情相悅,便是如此。可是,當愛變成偏執,當情變成控制,所謂窒息,不過如此。越是深愛,越是傷害,他給的愛太沉,她無法呼吸,他給的愛太烈,她無力承襲。 (小劇透) 不夠不夠,還是不夠!就算這樣瘋狂地吻著也無法紓解強烈的渴望。他抱孩子一樣抱起她急走幾步,將她抵在一棵楓樹的樹幹上,用腫脹的部位狠狠撞她,撩起她衣服下擺,手便探了進去,帶著急切的渴望,揉捏她胸前的美好。 狂亂的吻沿著白皙的脖頸一路往下品嘗。意亂情迷之中,安以默終於抓回一絲理智,抵住他越來越往下的腦袋。 “別,別這樣,別在這兒……”
32.4萬字7.56 173099 -
完結349 章

救命,被禁欲老公撩得臉紅耳赤(蓄意引诱,禁欲老公他又野又撩)
【先婚後愛 蓄謀已久 暗撩 荷爾蒙爆棚】【旗袍冷豔經紀人(小白兔)VS禁欲悶騷京圈大佬(大灰狼)】江祈年是影帝,薑梔是他經紀人。薑梔以為他是她的救贖,殊不知他是她的噩夢。他生日那天,她準備給他一個驚喜,卻親眼看著喜歡了五年的男友和當紅女演員糾纏在一起。-隻是她不曾想,分手的第二天,她火速和京圈人人敬畏的大佬商池領證了。剛結婚時,她以為男人冷漠不近人情隻把她當傭人,不然怎麼會剛領證就出差?結婚中期,她發現男人無時無刻在散發魅力,宛若孔雀開屏......結婚後期,她才明白過來,男人一開始就步步為營,引她入套!!!-重點是,男人為了擊退情敵。骨節分明的手不耐地扯了扯領帶,露出脖頸處若隱若現的印子。他湊到她耳邊,深眸緊盯著對麵的江祈年,唇角邪魅一勾。“寶貝,下次能輕點?”薑梔,“......”幼不幼稚?!!不過,看著江祈年氣綠了的臉,還挺解恨?
59.1萬字8.33 275566 -
完結1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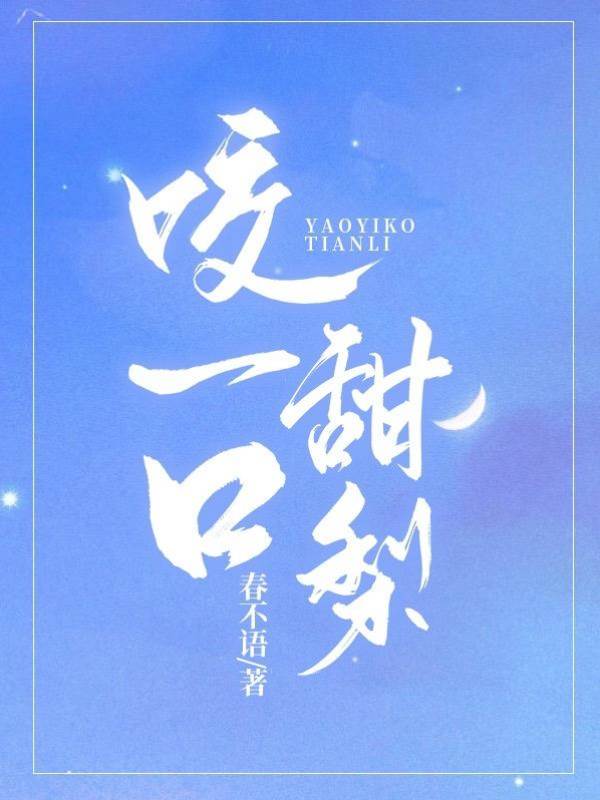
咬一口甜梨
白切黑清冷醫生vs小心機甜妹,很甜無虐。楚淵第一次見寄養在他家的阮梨是在醫院,弱柳扶風的病美人,豔若桃李,驚為天人。她眸裏水光盈盈,蔥蔥玉指拽著他的衣服,“楚醫生,我怕痛,你輕點。”第二次是在楚家桃園裏,桃花樹下,他被一隻貓抓傷了脖子。阮梨一身旗袍,黛眉朱唇,身段玲瓏,她手輕碰他的脖子,“哥哥,你疼不疼?”楚淵眉目深深沉,不見情緒,對她的接近毫無反應,近乎冷漠。-人人皆知,楚淵這位醫學界天才素有天仙之稱,他溫潤如玉,君子如蘭,多少女人愛慕,卻從不敢靠近,在他眼裏亦隻有病人,沒有女人。阮梨煞費苦心抱上大佬大腿,成為他的寶貝‘妹妹’。不料,男人溫潤如玉的皮囊下是一頭腹黑狡猾的狼。楚淵抱住她,薄唇碰到她的耳垂,似是撩撥:“想要談戀愛可以,但隻能跟我談。”-梨,多汁,清甜,嚐一口,食髓知味。既許一人以偏愛,願盡餘生之慷慨。
20.2萬字8 786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