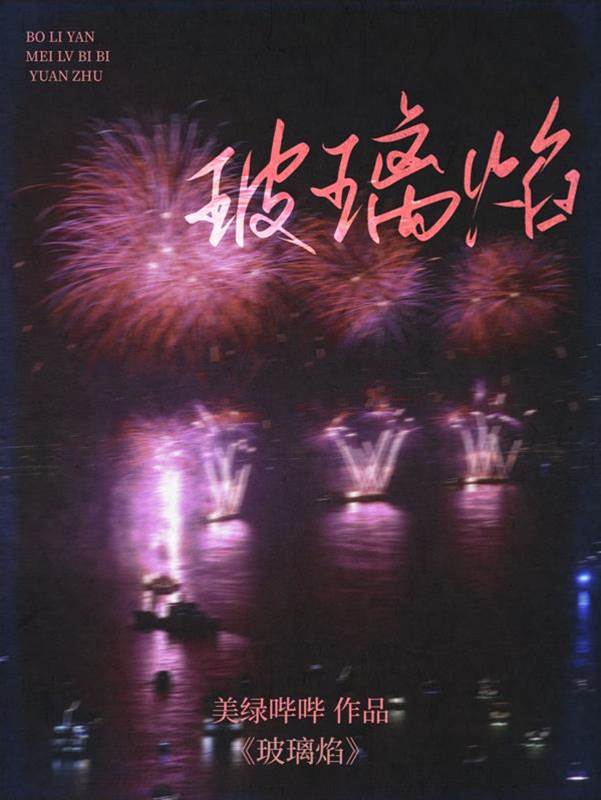《極致心癮》 391.第391章 白月光2
當然,遇到麻煩事,爺肯定提前知道,不到徐家來手。
但現在,小姑娘了徐家的人,徐家規矩雖束縛不能在四九城自由,也要在其他地方補償。
吃完飯,黎影照舊回東市。
一事接一事落頭上,英國名額的事還沒理好,徐家又要給一場婚禮。
不給不合規矩,既然徐家族譜,必須按明正娶來。
一份讓知人明白的重視,只要進徐家門,徐家護著。
徐家給的面,前提也要規矩做事,舉止言行不可出格。
接徐家后,與權力,覺得后者更實在,更有力。
手可得的資源優勢。
當然,沒說去犯法。
黎影啟程去英國前,改去國。
這一次,沒告訴徐敬西,而是落地拉斯維加斯。
然而,遇到的不是徐敬西,是三千萬。
維達拉大廳,穿著黑大的三千萬正坐在沙發與客戶談事。
有過三千萬的易,三千萬認得黎影。
角傷的三千萬指著從紅跑車下車的白月黎影,點點耳麥,告訴自家老板:“他的白月來了,千真萬確。”
三千萬都覺驚訝。
不過,是被Schreyer護送來,進維達拉輕而易舉。
暗區老板對手機挑眉,接過平板看監控。
維達拉大廈門口,白月正把車鑰匙遞給泊車員,拎著裝手機的小包,乖乖跟在Schreyer后。
暗區老板冷冷一笑,沒告訴旁忙正事的徐敬西,起,走到落地窗前。
“把帶來96樓,別打擾任何人。”
三千萬照做。
暗區老板意味不明低嗤,“原來他喜歡清純的。”忽而疑,“他結婚了?”
三千萬低聲:“覺應該結了。”
Advertisement
“你從哪兒覺?”暗區老板冷笑,“他可一點都不像會結婚的人。”
三千萬:“歐洲的時候,他逮住白月,立馬把所有路都封了,白月有他的孩子,他不可能不結婚,您覺得呢,我可是被他送進警局,就因為照顧他人幾天。”
雖然才接一回,十分了解。
——老板,他笑著溫的時候,比你還瘋,這種人,一點不能惹
當然,三千萬沒說這句。
老板突然冷嗤:“結婚不我要賀禮,他媽的,找我就一天到晚談事,做什麼盟友,他可太險了,說不定一不開心就把我吞并。”
以為徐敬西不敢麼,只不過,他更致力于另一條權力路。
-
黎影是被Schreyer帶來拉斯。
在哪間房,問過三千萬。
電梯,三千萬說:“先生在96層,剛剛和我老板有爭執,雙方掀桌子。”
出電梯,黎影疑:“真的掀了嗎,我們進去會不會不合適?”
三千萬遣散守在96樓的安保,推開門:“掀了,你的先生掀的,場有人說話惹到他了。”
總而言之,脾氣不太好。
黎影后退:“一會兒再進,我不去當炮灰。”
三千萬說著,“我老板想見你,不用擔心。”把推進去后,關上門。
黎影放下包給服務員。
抬頭。
目,是一張紅木大圓桌,聚了十幾位知名資本大亨。
許久未見的徐先生坐的位置背對,手里夾著一支沒點燃的香煙。
他對面坐的是暗區老板。
不是沒談好,是他媽的,暗區老板因為他朋友一通電話,兩個人通電話吵架后,著急上火。
徐敬西看得煩,直接桌子掀了,暫時不談。
攪得在場的人心驚跳。
Advertisement
兩位主事人心都不好,明明陀山居計劃很順利,偏偏聊到中場,沒一位心好。
無人注意到悄悄場的黎影。
“來,開槍啊。”
氣氛嚴肅,灰地毯一片狼藉。
鋼筆,打火機,煙盒,牛皮紙袋,還有一只致的懷表。
沒人敢一收拾起來,屏息坐著等候兩位主事人發落。
誰先發火不重要,徐先生脾氣晴不定,容不得任何人在自己面前不務正業,無視大局的態度。
特別是暗區老板因一通電話而擾談判。
邊上的安保已經整裝待發的模樣,隨時可能開槍比較一番。
怎麼覺…是被塞進來阻止災難?
徐敬西和那位暗區老板都不是吃素的,再吵下去,指不定上真格。
維達拉今夜得鋒一夜。
誰死不知道,反正不影響利益,第二天早上熄火,合作繼續。
徐敬西敲了敲手里的香煙,還未點燃,毫不留發難:“怎麼?不接電話會死麼,半個小時能解決的問題,一定要拖到四十分鐘?”
黎影撿起地上的打火機,乖乖上前,自徐敬西后,遞出打火機。
“消消氣。”
晶燈耀亮下。
他目落在那只細白干凈的小手,好一會兒,慢慢回頭。
小姑娘一臉溫的笑意,對著他,看著他。
那雙慣會人的狐貍眼在飛機上熬過夜,通紅且泛淚花,是哭委屈的模樣。
眼尾那抹紅,比朱砂艷。
無聲對視。
暗區老板起,笑著命人把墻上的秦代秦篆《春秋左氏傳,昭公十三年》整理好,送到黎影手中。
“送他的,沒人擋得了他的路,他不適合談,他只適合獨裁一切,老實放過彼此,別讓他上頭發火,維達拉遭殃。”
Advertisement
“生氣起來,我都怕他下一秒把一切毀了。”
絕對真理。
黎影看了眼徐先生的表,沒拒絕,沒波瀾起伏,只好接下字帖。
用不到半分鐘,96層全清空多余人員,厚重的五米高裝甲門及攝像頭,一并被關閉。
小姑娘站在徐敬西面前,手里攥住枚銀打火機。
“Schreyer帶我來。”
“找我,說婚禮的事,不是我自己一個人的婚禮,親口問你比較合適。”
不等徐敬西問,已經老實回答。
男人坐在那兒,目淡淡落在上,將的張與無意冒犯全看在眼里。
“所以才來見我?”他問,“就這麼個原因?”
“看看你…”黎影抬頭,“你還生氣嗎?”
說著,看了眼男人此時的神。
白襯,一件貴的黑西服,領口規整翻迭敞開,出骨前頸,一副高不可攀的姿態。
生氣沒生氣的事,拿不準。
男人只問:“沒其他事了?”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588 章
七零嬌女有空間
花朝大夢一場,帶著空間重生了! 這時候,她才十六歲,還是個嬌嬌俏俏的小姑娘,二哥沒有過失傷人致死,父母也都好好地……最重要的是,她還擁有一個健全又幸福的家! 撥亂反正重活一世,她腳踹渣男,拳打白蓮,護家人,踩極品,還反手捉了一個寬肩窄臀腰力好的小哥哥,利用空間一起玩轉七零,混得風生水起……
105.7萬字8 50643 -
完結552 章

全娛樂圈都在等影后打臉
雲城第一名媛葉傾城重生了! 從此,娛樂圈多了個叫蘇淺的巨星。 從娛樂圈新人到影后,她一路平步青雲,所謂人紅是非多,各種撕逼黑料接踵而至。 蘇淺冷笑! 她最擅長的就是打臉! 越黑越紅,終有一天,她另外一重身份曝光,再次重回名流圈。 看她如何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跪著讓他們唱征服!
97.1萬字8 17046 -
完結13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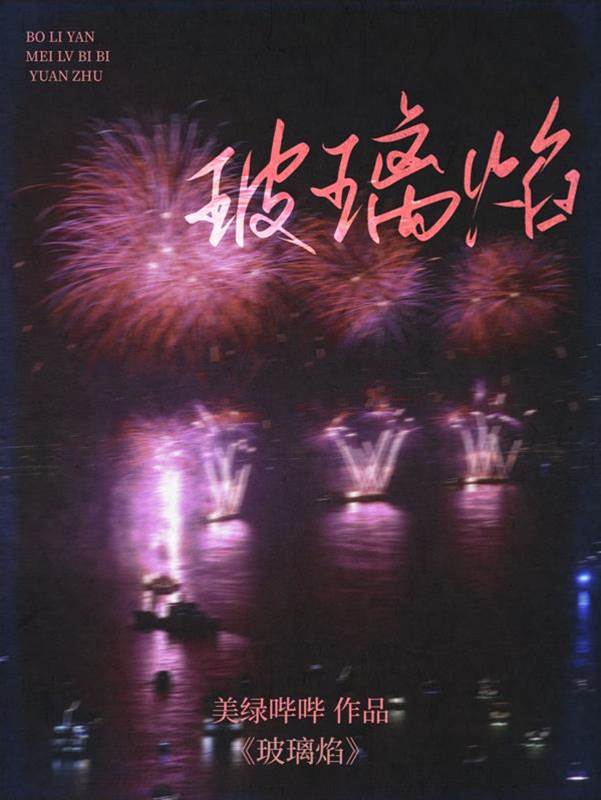
玻璃焰
[已簽約實體待上市]【天生壞種x清冷校花】【大學校園、男追女、協議情侶、強製愛、破鏡重圓】黎幸在整個西京大學都很有名。高考狀元,夠美,夠窮。這樣的人,外貌不是恩賜,是原罪。樓崇,出生即登上金字塔最頂層的存在優越家世,頂級皮囊但卻是個十足十的人渣。——這樣兩個毫無交集的人,某天卻被人撞見樓崇的阿斯頓馬丁車內黎幸被單手抱起跨坐在腿上,後背抵著方向盤車窗光影交錯,男人冷白精致的側臉清晰可見,扣著她的手腕,親自教她怎麼扯開自己的領結。——“協議女友,知道什麼意思嗎?”“意思是牽手,接吻,擁抱,上床。”“以及,愛上我。”“一步不能少。”——“玻璃焰,玻璃高溫產生的火焰,銀藍色,很美。”
25.7萬字8 14204 -
連載274 章

前妻太難追,偏執總裁他步步緊逼
【男主偏執病嬌 女主清冷美人 強取豪奪追妻 1v1雙潔 HE】五年婚姻,陸玥隱藏起自己的本性,乖巧溫順,取悅著他的一切。可圈內誰人不知,傅宸在外有個寵上天的白月光,為她揮金如土,就算是天上的星也給她摘下來。而對於陸玥,他覺得,她性子溫順,可以永遠掌控在手心。直到某天,她一紙離婚協議甩給他,轉身走人,與新歡站在商界巔峰,並肩而立。可在她一回頭,卻看見菩提樹下,傅宸的臉。“想離婚?”他一身純黑西裝,矜貴無比,淡淡道:“做夢。”
30萬字8 708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