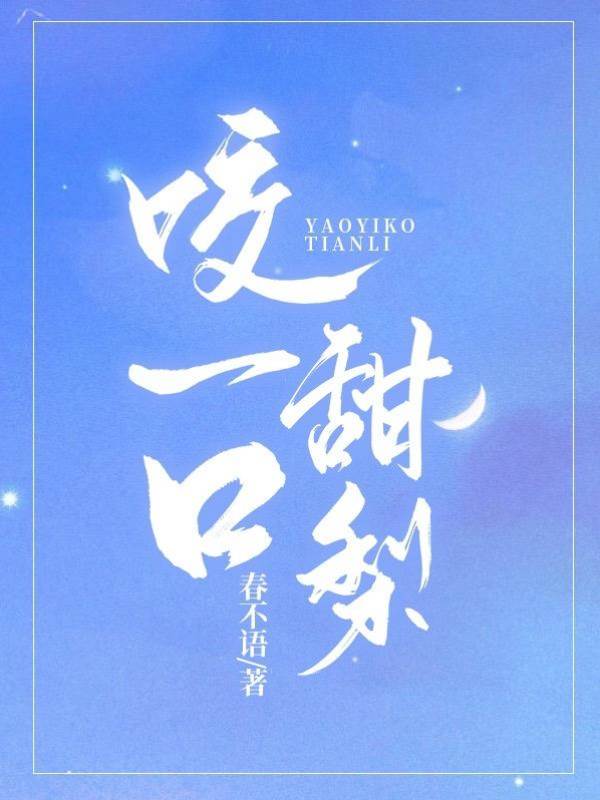《晝夜覬覦》 第331章 局中局
在監獄服刑的周母出事了。
據獄警反應,從月初開始,就出現了淋結腫大的現象,起初沒有在意,以為隻是普通的癥狀,過幾天就會好轉,沒想到近期開始,竟然出現了尿的現象。
天剛亮的時候,周母在獄中暈倒了,找來醫生檢查才發現,況有些不容樂觀。
所以趕通知了周衍。
在薑且麵前,周衍不敢提起周母,唯恐想起之前那些不好的過往。
於是在詢問的時候,周衍隻得找了個理由搪塞過去了。
他走的行匆匆,薑且盡管察覺有些不對,但是他不想,也懶得勉強去問。
倒是下午的時候,書過來匯報,說派出去留意的人,看出陶勝不對勁。
陶禧人在警局,他不僅沒有撈人或者找律師的意思,竟然還頻繁出銀行。
利盡而散,薑廣濤躲在上崖村,這事恐怕跟陶勝也不了幹係。
陶禧畢竟是一介流,要是隻憑一個人,能夠幫助薑廣濤的眾目睽睽之下逃出警察的手掌心,簡直荒誕。
現在二人紛紛獄,薑廣濤不想連累陶禧的心,和陶禧不想出賣陶勝一樣。
可惜陶禧那張和薑廣濤保持聯絡的小號,就注定了他們不能撇的幹幹淨淨。
陶勝行為舉止異常,恐怕多半是想卷錢逃之夭夭。
既然他們都不願意當這個惡人出賣自己的"盟友",不如就讓來幫他們一把。
於是這天中午的時候,薑且在薑萊一再的磨泡之下,答應了跟他見麵。
兩人約在薑且家中,小開心也在。
自從薑且一聲不吭從婚房搬走,小家夥了好大的打擊。
Advertisement
起先以為爸爸和媽媽和好了,沒想到一夜之間又回到了從前。
早上被周衍司機送到薑且麵前的時候,就一直哭個不停。
怎麽哄都哄不好。
薑且隻好一邊抱著,一邊接待薑萊。
上次來時,還是一家三口,結果現在隻剩他一人,不得不薑萊蒙生出一種是人非的落寞之意。
他看著啼哭不已的小家夥,原本想手抱抱,結果小家夥本不領,像是不認識小舅舅了似的,直接把他的手拍開,哭的更兇了。
薑萊尷尬的站在一邊,薑且則扭頭對油鹽不進的兒沉下了臉。
“你再哭,就回去找保姆,以後周末也不要到媽媽這兒來了。”
小家夥被嚇唬住了,流淚不敢出聲,憋著搖頭,“我不要……”
“那就不準再哭哭了。”
薑且換了隻手抱,瞧著滿臉淚痕的模樣,心裏比誰都心疼,但該懂的道理必須要懂,不是這樣一味的哭,就能想怎樣就怎樣。
薑且給洗了把臉,出來見薑萊還在原地杵著,“不是有話說嗎?怎麽,又不想說了?”
“周衍沒在嗎?”
他朝臥室張的作薑且忍不住勾起角,“找他的話,那你可以回去了。”
薑萊見一副要趕人的架勢,趕說,“姐,我媽的事,能不能請你高抬貴手?”
薑且安著緒低落的兒,聞言不由得愣住。
怎麽形容這種預判真的覺呢?
薑且隻覺得可笑。
“薑萊,你是不是沒搞清狀況?帶走陶禧的人是警方!”
“但追究底報案的人是你啊。”
Advertisement
薑萊的焦急已經寫在臉上了,“我不求別的,隻是我媽經不起折騰,和爸一直有聯係不假,但他們是夫妻,怎麽可能眼睜睜看著他被抓進而無於衷呢?”
“所以呢?”薑且依舊在笑,隻是臉上的笑容不免多了幾分心寒,“你是覺得我狠心,把薑廣濤送進監獄喪盡天良是嗎?”
“我沒有這麽想,但這件事明明可以私了,你為什麽一定要驚警方?”薑萊表示不理解,“爸進監獄,對你到底有什麽好?”
薑且氣極反笑,他終於把真心話說出來了。
“那麽請你告訴我,他串通張驍在新項目開始之前,造工地三人重傷,還特意找了提前蹲守準備大肆宣揚,如此惡劣的行徑怎麽私了?”
薑且反相譏,“拿錢了事嗎?那薑氏的名譽置於何地?我若因此攤上任命司,落下罪名鋃鐺獄,誰又會管我的死活?是他薑廣濤會去幫我求?還是他指使的三名工人會替我求?薑廣濤有今天,是他自作自,罪有應得。”
薑萊接不了辱薑廣濤。
“你是他兒,也未免把他想的太不堪了,你奪走公司他當然心有不甘,這事追究起來,張驍已死,自然所有的髒水都潑到了他頭上,你怎知主意不是張驍出的?他不過隻是一時昏頭,濃於水,他不會害你,但你卻實打實把他的後半輩子都葬送了。”
“薑萊,你給我聽好了,薑氏無論從前現在還是將來,都跟他薑廣濤沒有一錢關係。”
什麽事都能含糊,唯獨這件事不行。
薑且毫不留,“警察之所以會抓他,是因為他的的確確做錯了,而不是我的誣陷,我一直以為你是一個拎得清的人,卻不想也是這麽糊塗,我夠給他留臉的了,你別我跟你翻舊賬。”
Advertisement
薑萊蹙眉,深吸兩口氣,下脾氣。
“我知道是爸這麽多年虧待了你,但你也應該了解爸的脾氣,家裏向來是他說了算,我和我媽哪有反抗的餘地,在他逃去上崖村這件事上,我媽的確不知,他曾和陶家的親屬暗中來往過,這件事十有**是巧合。你找黃隊求求,把放了吧?”
薑且放下不知何時睡著的小家夥,冷笑一聲,“你也說了,是"你媽",跟我有什麽關係?”
“都這個時候了,你就非要計較這些嗎?”薑萊曉之以之以理,“就算是你的後媽,到底我們是一家人,如今爸媽鋃鐺獄,外人可都在看我們笑話呢。”
“你是不是忘了你媽說過的話?”薑且勾,“算起來,你跟薑家、跟薑廣濤,沒有半錢關係。”
薑萊一愣,“你為什麽這麽坦然就接了?”他很快就看出了不對,“難道你知道什麽?”
薑且就在等著他問這句話,也不想再大馬虎眼。
“你就沒覺得不對勁嗎?你舅舅陶勝千裏迢迢從a市過來,怎麽每一次聚餐,都隻是你們三個人而從來不見薑廣濤?到底是他工作繁忙?還是你媽就沒通知過他?”
猝不及防提起陶勝這號人,薑萊頓時愣住了。
是了,最近幾個月以來,陶禧他去酒店見陶勝的機會越來越多,每次總是他們三個人。
之前他一直沒有覺得有什麽蹊蹺,舅舅疼外甥,天經地義。
可現在回想起來,每次陶勝看他的眼神,都是那麽的異常。
明明他們之前也沒有多集,但他居然承諾,待自己年老,要把自己名下所有的財產都過戶給他。
難不,他們不是舅舅和外甥的關係,而是——
“不可能!”
薑萊被自己想到的這種可能嚇到了,堅決不認同薑且說的話。
又緣關係的兩個人,怎麽可能會生孩子?
“我知道你覺得匪夷所思,但事的真相就是這樣,你的確是陶禧和陶勝所生的兒子。”
把小開心安頓好,薑且從茶幾
直覺告訴薑萊這裏麵一定不是什麽好東西,但卻也忍不住好奇。
薑且看見薑萊捶在線的手,都在跟著發。
像是很難接這個事實。
打開的一瞬間,更是大氣都不一下。
當看見他和陶勝的鑒定結果高達百分之九九的時候,直接一個踉蹌,一屁癱到了沙發上。()
猜你喜歡
-
完結116 章

禁愛合歡
不知不覺,殷煌愛上了安以默。那樣深沉,那樣熾烈,那樣陰暗洶湧的感情,能夠湮滅一切。為了得到她,他可以冷血無情,不擇手段。 為了得到她,他可以六親不認,不顧一切。他無情地鏟除她所有的朋友,男人女人;他冷酷地算計她所有的親人,一個一個。他沉重的愛讓她身邊沒有親人,沒有朋友,誰都沒有,只有他。他只要她,所以,她的身邊只能有他。鎖了心,囚了情,束之高閣,困於方寸,她逃不開,出不去,連死都不允許。一次次的誤會沖突,安以默不由自主地被殷煌吸引。盛天國際董事長,市首富,一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男人,她曾以為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子,愛上他,也被他所愛,所謂兩情相悅,便是如此。可是,當愛變成偏執,當情變成控制,所謂窒息,不過如此。越是深愛,越是傷害,他給的愛太沉,她無法呼吸,他給的愛太烈,她無力承襲。 (小劇透) 不夠不夠,還是不夠!就算這樣瘋狂地吻著也無法紓解強烈的渴望。他抱孩子一樣抱起她急走幾步,將她抵在一棵楓樹的樹幹上,用腫脹的部位狠狠撞她,撩起她衣服下擺,手便探了進去,帶著急切的渴望,揉捏她胸前的美好。 狂亂的吻沿著白皙的脖頸一路往下品嘗。意亂情迷之中,安以默終於抓回一絲理智,抵住他越來越往下的腦袋。 “別,別這樣,別在這兒……”
32.4萬字7.56 172857 -
完結349 章

救命,被禁欲老公撩得臉紅耳赤(蓄意引诱,禁欲老公他又野又撩)
【先婚後愛 蓄謀已久 暗撩 荷爾蒙爆棚】【旗袍冷豔經紀人(小白兔)VS禁欲悶騷京圈大佬(大灰狼)】江祈年是影帝,薑梔是他經紀人。薑梔以為他是她的救贖,殊不知他是她的噩夢。他生日那天,她準備給他一個驚喜,卻親眼看著喜歡了五年的男友和當紅女演員糾纏在一起。-隻是她不曾想,分手的第二天,她火速和京圈人人敬畏的大佬商池領證了。剛結婚時,她以為男人冷漠不近人情隻把她當傭人,不然怎麼會剛領證就出差?結婚中期,她發現男人無時無刻在散發魅力,宛若孔雀開屏......結婚後期,她才明白過來,男人一開始就步步為營,引她入套!!!-重點是,男人為了擊退情敵。骨節分明的手不耐地扯了扯領帶,露出脖頸處若隱若現的印子。他湊到她耳邊,深眸緊盯著對麵的江祈年,唇角邪魅一勾。“寶貝,下次能輕點?”薑梔,“......”幼不幼稚?!!不過,看著江祈年氣綠了的臉,還挺解恨?
59.1萬字8.33 274981 -
完結1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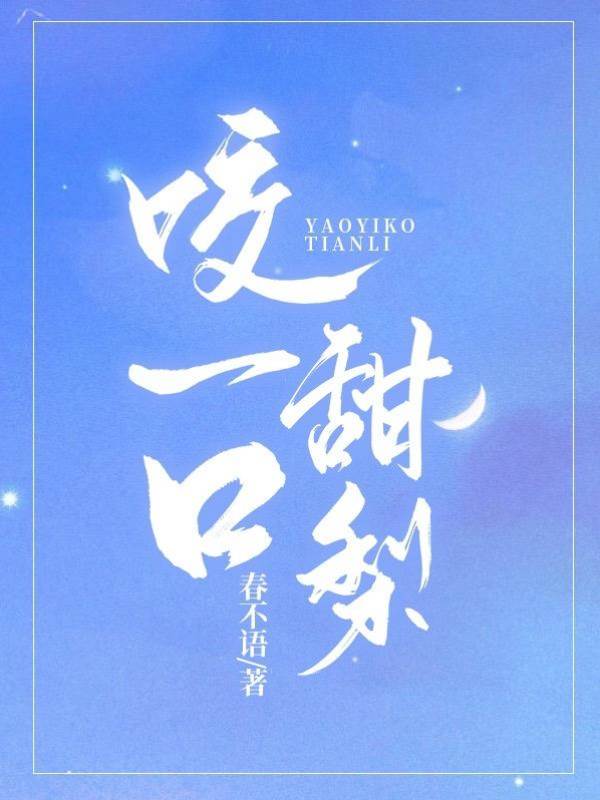
咬一口甜梨
白切黑清冷醫生vs小心機甜妹,很甜無虐。楚淵第一次見寄養在他家的阮梨是在醫院,弱柳扶風的病美人,豔若桃李,驚為天人。她眸裏水光盈盈,蔥蔥玉指拽著他的衣服,“楚醫生,我怕痛,你輕點。”第二次是在楚家桃園裏,桃花樹下,他被一隻貓抓傷了脖子。阮梨一身旗袍,黛眉朱唇,身段玲瓏,她手輕碰他的脖子,“哥哥,你疼不疼?”楚淵眉目深深沉,不見情緒,對她的接近毫無反應,近乎冷漠。-人人皆知,楚淵這位醫學界天才素有天仙之稱,他溫潤如玉,君子如蘭,多少女人愛慕,卻從不敢靠近,在他眼裏亦隻有病人,沒有女人。阮梨煞費苦心抱上大佬大腿,成為他的寶貝‘妹妹’。不料,男人溫潤如玉的皮囊下是一頭腹黑狡猾的狼。楚淵抱住她,薄唇碰到她的耳垂,似是撩撥:“想要談戀愛可以,但隻能跟我談。”-梨,多汁,清甜,嚐一口,食髓知味。既許一人以偏愛,願盡餘生之慷慨。
20.2萬字8 777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