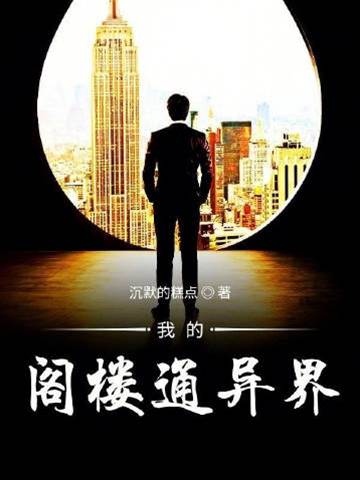《權貴嬌女》 第二百八十九章 提羅寨
第二百八十九章提羅寨巫族勢力龐大,並不拘於冥嶺,雖說塔安和提羅寨裡頭住的大多是粟朝百姓,可也有巫族人氏。
沈白焰替宋稚烘乾了發,這滿目的翠便著兩人出了人,在客棧門口打了一個照麵的,便是個黑黝黝的巫族年。
這整間客棧都沈白焰一乾人等給包圓了,能進門來的定是經過了查問。
巫族年年歲不大,量倒是趕上沈白焰了,隻是兩頰還有些乎,些許孩子氣。
年大大咧咧的看著沈白焰和宋稚,眼神倒是純凈無惡意,他出思索的神來,不大確定的道:「王爺?」
沈白焰略一頷首,見他習慣的扭了扭自己的脖子,發出嘎嘣嘎嘣的脆響,這作他想起一個老人來,便揣測道:「你是阿蚺的兒子?」
「是,王爺我阿炙就行了。我阿大讓我來找你,說是有事兒商量。」阿灸的嗓子有點啞,這個年紀的年大多如此。
阿灸正說著話,忽然覺得上一重,低頭一看竟是一個胖乎乎的娃娃掛在了自己上,還淌著口水對自己笑。
他平生最怕這糯唧唧的小孩子,阿媽去年剛生了一個小妹妹,總是鬧著要阿灸抱,阿灸每回都跑的飛快。
「王,王爺,您快,快給他抱走啊!」阿灸哭喪著臉,道。
宋稚定睛一瞧,原是初兕不知道什麼時候跑到那去了!流星連忙把初兕給抱了過來。
初兕鼓著臉,不知道這位大哥哥為什麼這麼害怕自己。
沈白焰有點想笑,但還是忍住了,偏首對宋稚道:「我去去就回,你先回房間,或讓藍躍陪著你,倒也可以出去逛逛。」
阿灸見他對宋稚說話時語氣溫和,神溫,半點不似阿大口中的那個『慣會做生意的大冰塊』!不免撇撇,隻覺得大人都是拿話恫嚇小孩!
Advertisement
宋稚的用指腹蹭了蹭沈白焰背在後的手,笑道:「好,你去吧。」
沈白焰一走,藍躍便上前一步,對宋稚笑道:「王妃,我讓措陸領著咱們去新的餘心樓瞧瞧吧!我還沒看過呢!」
「建在此?」宋稚驚訝道。
藍躍點點頭,一副十分期待的模樣,「是呀。但建在何,我也不大清楚。」
措陸一直坐在邊上聽著,中氣十足的喝了一聲,「別冒冒失失的,夫人的可熏製過了?」
藍躍哎呀了一聲,道:「我糊塗了,夫人先回房去吧。我問問逐月姐姐去。」
他們話裡話外的,也沒說清楚,不過宋稚將這些話連起來兩頭一聯想,倒是模模糊糊的琢磨出個影子來。
塔安離冥嶺太近,餘心樓建在那裡恐會激起巫族不安,提羅寨有深穀高山,若是建在此,倒是一個折中的法子。
在房裡候著,也不乏味。
這房間的窗外的景緻極,分明是深秋了,這樹木卻還是鬱鬱蔥蔥的,宋稚瞧出客棧外頭的樹,大多是樟樹,難怪在裡頭住著,沒發覺有半隻蚊子。
提羅寨秋日的涼意就跟那大姑娘一樣,從簾後的瞧你一眼,又退了回去。
真不知到了冬日,會如何呢?宋稚漸漸有些期待起來。
流星送了一份點心來,喚做煎堆,宋稚以為是什麼特的民食,一瞧卻是悉的油煎錘,隻是積比油煎錘大了一倍,足比嬰孩的腦袋大小。
兩個孩子瞧著這個碩大的油煎錘,自是新鮮無比,洗凈了手興沖沖的用手掰了一塊,滋滋的吃著。
宋稚當心這吃食易上火,便流星泡了羅漢果茶來。
孩子們在宋稚邊好好的,旁人還以為他們在林府呢!這事兒終有一日要餡,隻是不知那一日是哪一日?
Advertisement
寧聽院裡的小廚房每日兩碗酪蒸倒是不落,有時候也會換抄手什麼的,易克化的吃食。十公主子方便的時候,也常常帶著兒去寧聽院裡玩鬧。
雖是沒外人見過這倆孩子,可也沒人疑心吶。這金尊玉貴的孩子總歸是在林府待著,難不還跑到田埂上玩泥嗎?
林天晴領著康兒來了幾回,總是往這寧聽院裡鑽,總也不見初兕和蠻兒,一問起來,說是到十公主院裡玩去了,或是被小陳氏領著去量裁了。
頭幾次,倒是沒半分懷疑,可這次數一多,林天晴雖麵上不顯,心裡實打實的犯著嘀咕呢!不敢問老夫人,隻臨出門前纏著團圓問了幾句,被團圓給糊弄了過去,團圓一進門,便報給了老夫人。
老夫人握著自己的玳瑁手杖重重的拄了拄地,道:「這丫頭怎麼就與稚兒過不去呢!」
團圓知道林天晴是老夫人從小看護到大的心尖,便是對失了數次,卻也還是割捨不開的,連忙打圓場道:「老夫人,這總也不見,晴小姐有些好奇也是人之常。」
「罷了罷了,在等上些時日,總歸會知曉的。」老夫人長嘆了一口氣,由團圓扶著進去休憩了。
沈白焰到了提羅寨,休養了數日也不見靜,朝上去了信一問,說是與巫族新任的首領達了協議,不打了!
弄的先前戰戰兢兢的那些個大臣好一個沒臉。人家一去,竟是兵不刃的停了這場爭議。
又有人跳出來說,『哎呦,王爺該不會是怕了人家,給人許了不好這才停了吧?那不能行啊!國之大恥!』
朝上又去信一問,說是沒啥!就是幫著人家種種地,修修學堂,不了你國庫的一分銀子,就是得在那待個三五載年的!
Advertisement
不用花國庫的銀子!這下大家可樂嗬了。
幾個在後頭的文跳上前,忙不迭的稱讚歌頌了沈白焰一番,這好話沈白焰可聽不著,但那一位可是明明白白的聽見了,這不,尋了個由頭,將這幾人給打發出京了。
馬屁拍的最響亮的那一位,更是了『使者』,去代表朝廷幫著給沈白焰『出出主意』。
「我呸!什麼出出主意,又來一眼珠子!監視咱們的!」胡琮狠狠啐了一口,氣得不行。
「你這麼惱做什麼?到了咱們的地界,還想著能呼風喚雨吶?」素水渾不在意的笑道。
胡琮掏掏耳朵,道:「這倒是。」
「得了,王爺和王妃今日就住進咱們樓裡來了。王妃倒是個隨和無拘的,隻是兩個孩子還小,你這罵罵咧咧的脾氣可得稍微收斂些。」素水斜瞧了胡琮一眼,道。
胡琮點了點頭,道:「我知道,哪能在孩子跟前這樣鬧騰呢!」
說話間的功夫,沈白焰和宋稚便帶著孩子們和心腹往這餘心樓的來了,他們都穿著心熏製過的裳,散發的淡淡的草藥香氣,所到之蚊蟲退散。
這本是林深,卻人辟出了一條小徑,隻是岔口頗多,若無人帶路,便是走上十次,宋稚也記不住。
有些地方分明是絕路,非得對岸放下橋來,才能過得去。這樣一來,倒也不怕百姓誤闖了。
「今日先帶你走一回,來日進出,倒也不用這般麻煩。」沈白焰道。
宋稚沒大明白,可也沒追問,來日方長,不著急。
待過了最後一座橋,餘心樓便在眼前了。
說是餘心樓,卻是一間極寬敞的院子,說是院子,倒也不那麼妥帖,若宋稚來說,倒像是座小城。
四周皆是草木風聲,靈雀清啼。
Advertisement
素水和飛嵐已在門口迎他們,蠻兒素水抱了起來,一路朝裡邊走去。
餘心樓的模樣,像個城中城,外頭一圈是竹樓,皆住著人,隻是現下出去辦事的辦事,在後山練功的練功,空著罷了。
宋稚和沈白焰自然是住在裡邊,一間獨門獨戶的清雅小院。邊上有兩座獨棟的小竹樓,像是左右護法似的。
「素水姐姐,你住在這兒,陪著蠻兒嗎?」蠻兒摟著素水的脖子,道。
「是呀,我住西邊,飛嵐住東邊。」素水臉上難得有這般溫的笑意,飛嵐窺了幾眼,心跳的飛快。
「再過幾日,便辦了喜事搬一塊住去,也好給旁人挪挪窩。」沈白焰推開院門,忽然扭頭說了一句。
蠻兒沒太聽懂,隻是看了看素水,又看了看飛嵐。宋稚撲哧笑了一聲,素水這輩子沒臉紅過,此時也惱道:「王爺!」
飛嵐得了便宜自然不敢聲張,也是紅著臉跟在後頭。
一進門,便是滿院的花草,一如在王府的樣子,隻是有些花草的模樣宋稚並不認得。
「呀!」茶香像掉進了錢窩裡那般高興,端著一盆蘭花就不撒手。
「你倒是有些眼力。」一個蓬頭垢麵的男子從一叢月季後邊鑽了出來,嚇了茶香一跳。
「牧蘆,你別嚇著人家姑娘。」素水說了一句。
「這是我從山裡尋來的野蘭花。你可別給我糟踐了。」牧蘆扯了一樹枝捆了頭髮,若是忽略他那糟糟的鬍子,模樣倒還周正。
「你別瞧不起人!我指不定養的比你還好呢!」茶香這輩子沒這麼大聲說過話,說完倒把自己給嚇住了,捂著臉半天不敢抬頭。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635 章

夫人虐渣要趁早
重生虐渣,暴爽來襲復仇千金撩翻神秘高冷未婚夫重生前,宋知之是名門上流千金,教養學識顏值身材樣樣線上,卻被渣男蒙騙,落得個家破人亡、死不瞑目的下場。老天有眼,她重生歸來,猛得一p偽善繼母白蓮花繼妹深情渣男嗬嗬前世欠我的統統都給我還回來,變本加厲的那種而世人皆知,她有一個財閥未婚夫,長得禍國殃民,卻因車禍不為人道,高冷暴戾,她一再悔婚等等,世人是不是有所誤解她家未婚夫狠能耐情話很動聽身份說出來都要抖一抖她抱緊未婚夫的大腿死都不會鬆手隻是,分明她在虐渣風生水起,怎麼她家未婚夫比她還心急,“夫人,虐渣要趁早”簡而言之,本文講述的是重生後的宋小姐報仇雪恨又收獲愛情,夫婦齊心一邊虐渣一邊虐狗的故事
195.1萬字8 47683 -
完結361 章

退婚后我嫁給了前任他叔
裴家道珠,高貴美貌,熱愛權財。面對登門求娶的蕭衡,裴道珠挑剔地打量他廉價的衣袍,微笑:“我家名門望族世代簪纓,郎君恐怕高攀不上。”一年後裴家敗落,裴道珠慘遭貴族子弟退婚,卻意外發現曾經求娶她的蕭衡,竟是名動江左的蕭家九郎,名門之後,才冠今古,風神秀徹,富可敵國,還是前未婚夫敬仰的親叔叔!春日宴上,裴道珠厚著臉皮深情款款:“早知阿叔不是池中物,我與別人只是逢場作戲,我只想嫁阿叔。”蕭衡嘲諷她虛偽,卻終究忘不了前世送她北上和親時,那一路跋山涉水肝腸寸斷的滋味兒。 -世人等著看裴道珠被退婚的笑話,她卻轉身嫁給了未婚夫的親叔叔——那個為了她兩世癡狂的男人,還被他從落魄士族少女,寵成頂級門閥貴婦。
59.6萬字8 15905 -
完結1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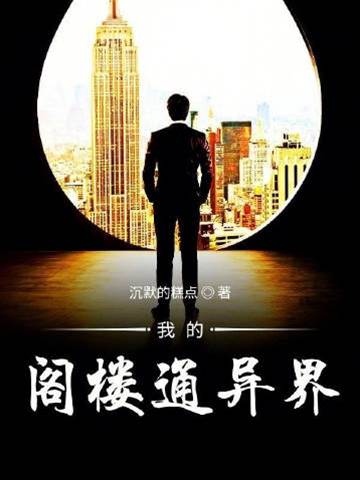
我的閣樓通異界
王歡受傷退役,堂堂全運會亞軍落魄給人按摩。 租住閣樓竟有傳送門通往異界空間,寶藏無數。 命運改寫!他包攬奧運會所有短跑金牌,征服諾貝爾文學獎,奧斯卡金像獎,格萊美音樂家獎。 他製作遊戲滅掉了暴雪,手機滅掉了蘋果,芯片滅掉了英特爾,飛機滅掉了波音。 他成為運動之神,文學之神,音樂之神,影視之神。 稱霸世界所有領域,從奧運冠軍開始。
71.3萬字8 24792 -
完結404 章

夫人盼守寡
嫁給方謹言,關靜萱完全是沖著守寡去的, 一塊兒長大的竹馬都能寵妾滅妻,男人還是死了最可靠。 萬萬沒想到的是,這輩子的方謹言居然是個長命百歲的。 【小劇場】 方謹言控訴娘子,你對兒子比對我好! 關靜萱挑眉兒子是我親生的,你是嗎? 方謹言壞笑我不是你親生的,但是我可以親你,讓你生!
86.5萬字8 46075 -
完結301 章

與權臣前夫重生日常
蘇蘊本是不起眼的庶女,因忠毅侯府嫡子被人算計,才得以高嫁侯府。 侯府世子顧時行樣貌俊美,為人端方自持,注重規矩,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 他一直誤以為,蘇蘊為嫁給進侯府,不惜毀壞自己的清譽,故在成婚后,夫妻二人無愛無情,形同陌路。
46.4萬字8 30425 -
完結423 章

欲扶腰
南漁當上太后那年剛滿二十。面對稚子尚小,國事衰微,她急需抱一只霸道粗壯的大腿撐腰。朝野弄臣蕭弈權向她勾了手指,“小太后,你瞧我如何?”南漁仰著艷絕無雙的小臉,跪在男人靴下:“只要我乖,你什麼都可給我嗎?”后來,她真的很乖,乖到將上一世受的屈辱全部還清,乖到一腳將蕭弈權踹下城樓!彼時,早已被磨礪成舔狗的男人,滿身血污,卻仍討好的親吻她腳尖:“漁兒,別鬧。”-----我欲扶搖直上青云里,他卻只貪欲中腰。 ...
70.1萬字8 949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