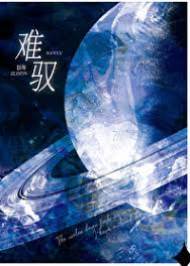《冷先生的甜婚指南》 第90章 他就要要了她
季,全名季運恒,季氏集團董事長的長子,花錢如流水,換朋友比換服還快。
這種男人,開口說“喜歡”,可信度幾乎為負值。
“小謝,當我朋友,我會給你,你想要的一切。今晚,好好伺候我!”季運恒咧著,連哄帶騙地再次靠近以沫。
“對不起,季,我已婚,不適合給您當朋友。”以沫淡定地撂下話,轉既走。
“行了,小謝,你就不要再找什麼破藉口拒絕我了!咱們都是年人,說話就直接點。本今晚就是要你給我當朋友!”季運恒不再跟以沫墨跡,語氣終於不耐煩了起來。
他剛剛還是一副溫的麵孔,此刻驟然一變,出了原本就好的暴躁本。
季運恒步上前,手便捉住了以沫的手腕,將往墻壁上去,並抬起另一隻手,拉下的領,按住的脖頸就狂吻了下來。
“小謝,我要你!本今晚就要你!你必須為我的人!”季運恒一邊迫不及待地吻,一邊胡言語起來。
“小謝,你真是個磨人的小妖!”
以沫連吃的勁都使出來了,但的力度在這男人麵,就像蚍蜉撼樹,自不量力。
此刻……
誰來救救?
“夜”的公共衛生間裡,黑係列風格的洗手臺前,一個俊逸俗,氣質與周遭環境顯得格格不的男人,正站在洗手盆前,慢條斯理地洗著自己那雙修長而好看大手。
其實,他的雙手因為常年槍而生了老繭,隻是最近退役從商後,每天坐辦公室,倒是把他給養白了。
Advertisement
冷夜沉將上那件高定版銀灰西裝了下來掛在了手臂上,現在他一襲白天蠶手工襯,完地將他健碩的給襯了出來。
他今晚是怎麼呢?
冷夜沉劍眉微蹙,緩緩地抬起頭,看著鏡子裡的自己。
腦海裡,又一次浮現出臺上那個駐唱的“小謝”的倩影。
冷夜沉微微瞇了瞇眸子,恍若在鏡子上看到了“漫雪”的微笑。
剛剛有很多次,讓他產生一種臺上的“小謝”,就是他心的人“漫雪”的錯覺。
或許,他已經病膏肓了吧!
他是不是應該去找一個心理醫生給自己看看?
冷夜沉收回思緒,了張紙巾,一邊拭著雙手,一邊走出去洗手間。
救命……
“漫雪”的聲音,不知從何傳了他的腦海。
冷夜沉心一怔。
當季運恒的大手到以沫底的邊緣時,以沫冷不丁地打了個寒,忽然間害怕地抖了起來。
救命……
誰來救救我?
不要……
以沫神經繃,繼續抗拒著季運恒,雙手不停地推搡,心一刻都不敢鬆懈。
突然,一陣不急不緩的腳步聲,從那邊樓道口傳來。
以沫眼前一亮,滿懷希冀地循聲去。
這裡是安全通道樓梯口,所以很有人會路過這裡。
以至於季運恒敢在這裡對肆意妄為。
而這樣的腳步聲,對以沫來說,無疑是一救命稻草。
隻見,一道修長筆直的影出現在了樓梯上。
樓道裡的燈,從上打了下來。
那道影就站在逆裡,隨著他從容不迫的腳步,一張棱角分明的俊臉,在一片影中緩緩地挪了出來。
Advertisement
居然是……他!
以沫也沒想到,會在這種地方,再次邂逅那個被救過的男人。
明明在這之前,一點都不想再遇到他。
可此時此刻,卻多麼希,他能朝走過來。
那男人居高臨上地看著他們,英俊的臉還有一大片都淹沒在暗影裡,完全看不清他是何種表。
季運恒看到這男人時,先是一愣,停下了手中所有的作,憂心忡忡地揣測著這個男人的心思。
他似乎是巧路過此地,好像並不打算手他們的事。
季運恒心裡篤定這個男人不會多管閑事後,地抓住以沫的手,一把拽著,就想帶離開這裡,然後去開間房,接著做這沒做完的事。
“季,你放開我!”以沫掙紮著,手腕都被這男人給抓紅了,依舊不放棄任何求生的機會,趁機對剛剛那個男人大喊了一聲,“先生,求你,救我!”
“你給本閉!”季運恒一邊拽著以沫往那邊的電梯口走去,一邊惡狠狠地謾罵著以沫,“本花了錢,打賞了你,你就得陪本過夜!都來這裡賣了,當了婊子還要立牌坊?賤人,真作踐!要,待會到了本的床上再!”
季運恒說這話時,故意拉高了嗓音,像是說給那個男人聽的。
他隻不過是想警告那個男人,他手裡拽走的這個人就是個出來賣的,不值得“英雄救”。
冷夜沉淡定地從樓梯上下來後,也就默默地站在走道上駐足,靜靜地看著他倆漸行漸遠的影,似乎確實沒有要手管這事的意思。
Advertisement
以沫見那男人對的呼救無於衷,頓時想死的心都有。
趁著季運恒注意力分散之際,以沫低下頭去,在季運恒的手背上咬了一口。
季運恒“啊”地一聲,吃痛地鬆了手,以沫見狀拔就跑。
因為跑得太急,以沫一個踉蹌,跌倒在冷夜沉的麵前。
季運恒趁機追上,再次將從地上拽了起來,一邊破口大罵“你這個賤人,敢咬我!找死,是不是?”一邊揚起另一隻手,要給以沫一掌。
()
冷先生的甜婚指梁以沫冷
猜你喜歡
-
完結91 章

樑少的寶貝萌妻
【暖寵】他,宸凱集團總裁,內斂、高冷、身份尊貴,俊美無儔,年近三十二卻連個女人的手都沒牽過。代曼,上高中那年,她寄住在爸爸好友的兒子家中,因爲輩分關係,她稱呼樑駿馳一聲,“樑叔”。四年前和他的一次意外,讓她倉皇逃出國。四年後,他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而她歸國後成了正值花樣年華。樑駿馳是她想拒絕卻拒絕不
14萬字5 38723 -
完結517 章

婚不設防:帝少心尖寵
日久生情,她懷了他的孩子,原以為他會給她一個家,卻冇想到那個女人出現後,一切都變了。靳墨琛,如果你愛的人隻是她,就最好彆再碰我!
92.1萬字8 67362 -
完結2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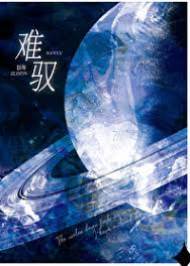
難馭
檀灼家破產了,一夜之間,明豔張揚、衆星捧月的大小姐從神壇跌落。 曾經被她拒絕過的公子哥們貪圖她的美貌,各種手段層出不窮。 檀灼不勝其煩,決定給自己找個靠山。 她想起了朝徊渡。 這位是名門世家都公認的尊貴顯赫,傳聞他至今未婚,拒人千里之外,是因爲眼光高到離譜。 遊輪舞會昏暗的甲板上,檀灼攔住了他,不小心望進男人那雙冰冷勾人的琥珀色眼瞳。 帥成這樣,難怪眼光高—— 素來對自己容貌格外自信的大小姐難得磕絆了一下:“你缺老婆嘛?膚白貌美…嗯,還溫柔貼心那種?” 大家發現,檀灼完全沒有他們想象中那樣破產後爲生活所困的窘迫,依舊光彩照人,美得璀璨奪目,還開了家古董店。 圈內議論紛紛。 直到有人看到朝徊渡的專屬座駕頻頻出現在古董店外。 某知名人物期刊訪談。 記者:“聽聞您最近常去古董店,是有淘到什麼新寶貝?” 年輕男人身上浸着生人勿近的氣場,淡漠的面容含笑:“接寶貝下班回家。” 起初,朝徊渡娶檀灼回來,當是養了株名貴又脆弱的嬌花,精心養着,偶爾賞玩—— 後來養着養着,卻養成了一株霸道的食人花。 檀灼想起自薦‘簡歷’,略感心虛地往男人腿上一坐,“叮咚,您的貼心‘小嬌妻’上線。”
34.9萬字8.18 1069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