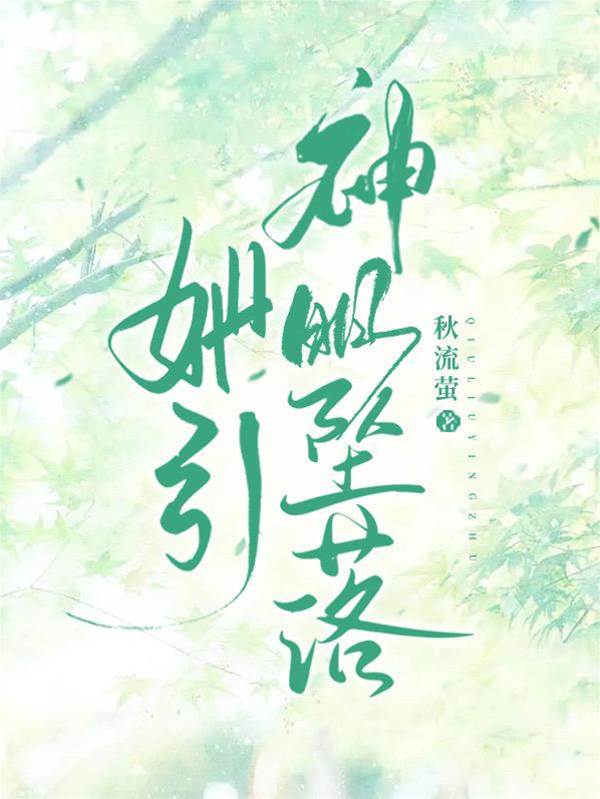《許一一傅霆琛》 第442章 帶回來
此時,不知名海島上。
烏雲沉沉的在天際,偶爾悶雷聲滾,風已經將浪催得不定,眼看一場風暴即將來襲。
在明暗錯的海岸線斷崖邊界,聳立著一幢別墅,黑玉石的外表,布克雕花落地窗,黑天鵝絨的窗簾合攏,一也沒有。在此時看起來,整座別墅格外像是末日的一座墓碑。
黑暗,森。
忽然,黑沉沉的窗簾被猛地扯開一角,一隻蒼白的手啪的一聲落在了雕花玻璃窗上,伴隨著一聲淒厲的哀。
但不到一秒鍾,那隻手就倏然消失,隻留下重新垂落的窗簾不停擺,像被外力作用著,不由自主的抖。
那聲音也低了下去,在呼嘯的風中,隻聽得到低沉的嗚咽。
一道閃電撕裂天空,隨著驚雷炸響,狂風卷著浪衝擊著斷崖,發出巨般的低吼,而暴雨,終於傾盆而下。
就在這時,閉著的別墅大門豁然大開,一個穿白黑赤著腳的男人狂笑著衝出來,在暴風雨中跳著吼著,手裏一長長的皮鞭迎著風雨擊著,癲狂得讓人瞠目。
Advertisement
原本宛若墳墓一般死寂的別墅裏,此時也忽然冒出一群訓練有素的仆從,拿著各自分配好的工,十分練利索的開始整理屋子。
黑天鵝絨窗簾撤下,換上輕蕾白紗,所有家迅速拭上蠟,一塵不染,染了漬的地毯迅速卷起收走,出原木清爽幹淨的,而地板上蜷著的人……
負責地板清理的傭看著那白裹上跡斑斑的影,瑟了一下,終究還是沒忍住,問自己旁邊的同伴道:“怎麽辦?一起扔了嗎?”
同伴立刻噓了一聲,低了聲音道,你忘了早叮囑你的規矩了?要是在我們打掃完之前沒爬起來,那就跟著垃圾直接扔了,還問什麽問?
那傭嚇得子一抖,沒敢再多說一句,但不自覺的,手下的作就放慢了一拍。
仿佛是這一善念起了作用,那本來趴服著一不的人影,先是了幾下,然後極其緩慢的,從地上慢慢撐著跪了起來。
Advertisement
“還活著,還活著!”
小傭又興又張,著嗓子忍不住又開始喊同伴,卻見同伴隻瞪了一眼,比了比門口。
手中沒停,一邊往同伴比劃的方向看過去,幾個戴口罩穿白大褂的人已經匆匆靠近,為首的是個頭發花白的老頭兒,揮了揮手,他後的幾個白大褂就將地上剛撐起來的人輕手輕腳的直接抬上擔架,而後一行人又匆匆而去了。
隻在經過小傭邊時,聽到擔架上那個人吐出模糊不清的呢喃。
“許一一……許一一……我要活著……許一一……你等著……”
那聲音裏帶著刻骨的怨毒,讓原本有些興的心乍然冰凍。
許一一,那是誰?
得有多大的仇恨,才讓這個人在了主人這麽嚴酷的折磨之後,還強撐著清醒過來?
外麵的風雨已經漸漸弱了下去,外麵癲狂肆意的男人漸漸的萎頓,淩的步子一個趔趄,坐倒在斷崖邊的長椅上。
Advertisement
門口等著的人迅速小跑上去,幾乎是就地搭起了一個更間,井然有序的伺候著男人更梳洗,很快,原本瘋得不人形的男人煥然一新,麵目清俊斯文,一高定,矜貴的氣質無形有韻。
隻是麵目間的疲憊無法掩飾,那好看得過分的眸子裏滿是鬱,張開口,用一種像金屬般刺耳難忍的嗓音道:“訓不好的狼崽子,還是帶回來養狗吧。”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連載4114 章
罪妻來襲:總裁很偏執
易瑾離的未婚妻車禍身亡,淩依然被判刑三年,熬過了三年最痛苦的時光,她終於重獲自由,然而,出獄後的生活比在監獄中更加難捱,易瑾離沒想放過她,他用自己的方式折磨著她,在恨意的驅使下,兩個人糾纏不清,漸漸的產生了愛意,在她放下戒備,想要接受這份愛的時候,當年車禍的真相浮出水麵,殘酷的現實摧毀了她所有的愛。
361.9萬字8 23603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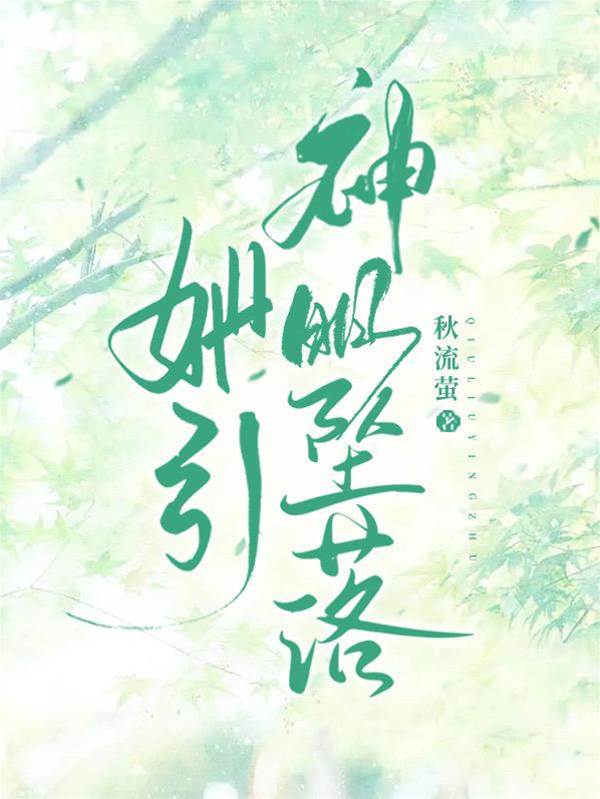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311 章

昨夜燈暖
三年前,蕭叢南被迫娶了傅燼如。人人都道,那一夜是傅燼如的手段。 於是他一氣之下遠走他鄉。傅燼如就那樣當了三年有名無實的蕭太太。 一夕鉅變,家道中落。揹負一身債務的傅燼如卻突然清醒。一廂情願的愛,低賤如野草。 在蕭叢南迴國之後。在人人都等着看她要如何巴結蕭叢南這根救命稻草的時候。 她卻乾脆利索的遞上了離婚協議書。
51.4萬字7.82 115868 -
完結120 章

豪門小可憐?不,是你祖宗
豪門小可憐?不,是你祖宗小說簡介:宋家那個土里土氣又蠢又笨的真千金,忽然轉性了。變得嬌軟明艷惹人憐,回眸一笑百媚生。眾人酸溜溜:空有皮囊有啥用,不過是山里長大,
22.5萬字8.46 589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