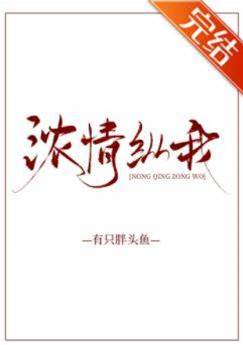《情逢對手》 第207章 我們至此沒有退路
忽然便覺得心搐似的疼,男人摟著,心口的地方得那麼近,能覺到他心跳的有力和急促。
“恩恩,你我嗎?有一點點嗎?”
南夜爵覺得自己真的是找,明明知道是怎樣的答案,卻非要問,非要將傷疤捅開后赤曝曬在人前,再讓容恩狠狠在上面撒一把鹽。
容恩沒有回答,真覺整個人無力,垂在側的雙手不由自主地穿過南夜爵的背部,落在他肩膀上。
的已經失去控制,也分不清是背叛了心,還是心背叛了自己下意識的作。
覺到的回應,南夜爵神間閃過瞬時的欣喜,他眼眸亮了下,更用力地擁著容恩。
他不則已,一旦深,竟是以如此卑微的姿態。
他的令人窒息,甚至是殘忍而極端的,為了容恩,他真的會殺人,真的。
“恩恩,你但凡能給我一點,我也不會這樣對你。”
兩人明明相擁著,卻能覺到彼此將對方刺得很痛很痛,難道他們真的是兩只刺猬嗎?
傷害扎進了皮,見了,留下千瘡百孔的傷疤。
容恩捫心自問,嗎,有一點嗎?
說過,的心是被捂熱過的,真的有。
閻越的事,不敢說,一個字都不敢,南夜爵的瘋狂不是沒有見過,盡管知道,用不了多久他自己就能查出來,可容恩還是不敢說。
“你想讓我你,就是以這種方式嗎?”容恩輕推開他,走一步,那條白金鏈子就會發出在地上拖的聲音,屈辱而悲戚。
“我沒有別的辦法,我不會再讓你去他邊,一步都不可以……”
Advertisement
“所以,你就打算一輩子這麼鎖著我嗎?”
“鎖到你忘記他,留在我邊為止……”
容恩走到落地窗前,窗簾已經拉上半邊,站在它的后面,就真的像是置在無邊無際的黑暗中一樣,“你分明就知道我忘不了閻越的。”
“恩恩,你非要激怒我嗎?”南夜爵來到容恩后,雙手穿過的腰側落在小腹上,“我們像之前那樣安安靜靜的,多好?”
南夜爵清楚,他們回不到那時候,當初容恩是對閻越死了心的,和現在不同。
他想不出還有其它的方法能令容恩搖,唯一的手段,就是閻越死。
#每次出現驗證,請不要使用無痕模式!
一個死人,遲早會被忘,容恩痛的這段時間,他可以陪著。
景苑向來很安靜,這會樓下卻傳來說話的聲音,好像是王玲和什麼人。
南夜爵走出臺,雙手撐在欄桿上,容恩先一步認出那是劉媽的聲音,急忙跟出去,就見王玲擋在門外,正和劉媽說著什麼。
“我找容恩,你讓我和見一面吧?”
王玲面難,這個人認識,當初在閻家見過,“不好意思,容小姐真的不在。”
容恩剛要說話,卻被邊上的南夜爵捂著。
他將拖進臥室,并將落地窗和窗簾全部拉上,乍來的黑暗令人手足無措。
南夜爵坐在床沿,讓容恩坐在自己的上。
樓下,王玲正找著理由搪塞劉媽,容恩知道來這,肯定是因為今天沒有去醫院,閻越看不到著急了。
“南夜爵,你放開我,放開——”
Advertisement
他捂著的,容恩的怒吼過男人的指傳出去,模糊不清。
他握著容恩的腰,將反在床上,的臉埋被子,那條鏈子材質特殊,并沒有帶給容恩什麼不適,只是綁在腰際,始終覺得冰涼。
“南夜爵,你瘋了,你真的瘋了——”
這樣的男人,讓害怕、戰栗。
“是,我是瘋了,那也是被你瘋的。”南夜爵全部重量在容恩背上,大口著氣,心臟的地方覺到窒息,呼不出氣來。
“你別想再見到他,別想——”
容恩知道這個男人有時候會瘋狂得令人發指,眉頭皺,沒來由地覺到害怕,“你要是敢閻越的話,我不會恨你,他要是死了,我也會去死,你不要我!”
“你就這麼護著他?你也想跟著去死嗎?我不會讓你如愿的,容恩,你想都別想——”
“南夜爵,你約束得了我的自由,你管不了我的生死,我若想死的話,誰也攔不了我……”
男人一句話沒有說,只是俯在容恩的背上,他灼
熱滾燙的氣息噴灼在耳邊,他有多麼憤怒,知道。
容恩真是想不通,他們之間怎麼會到了這一步?
過了許久后,男人才從上起來,黑暗中,看不見南夜爵臉上的神,只知道他是帶著怒火離開的,摔門的時候,幾乎整個房子都在抖。
“先生——”
樓下,王玲剛要說什麼,便被南夜爵揮手打斷,“我知道,我要出去趟,你盯著,還有……嗓子有些啞,午飯不要做辛辣的東西。”
“好。”
南夜爵將車開出景苑,沒想到劉媽并沒有走,在大門外撲了過來。
Advertisement
男人一個急剎車,順手摘下墨鏡,一雙深邃的眸子迸出寒。
這個男人,劉媽或多或從閻家二老里了解不,還有電視上也經常會報道,繞過車頭來到南夜爵車門前,“先生,我想請問下,容恩在嗎?”
“不在。”
劉媽被他兩個字堵得說不下去。
南夜爵想了下,將手肘支撐在車窗外,“你找有事嗎?”
“對,我有急事。”
“說。”
劉媽不知該怎麼說,閻越的事,閻家對外依舊保,沒有一個字,“麻煩你,讓我見一面可以嗎?”
“不可以,”南夜爵斷然回絕,將墨鏡重新戴回臉上,“還有,不要再找到這兒來,景苑不是你們隨便能來的地方,順便帶句話給閻越。他想將容恩搶回去,想都別想,別不自量力,他還沒有那個本事。”
劉媽臉煞白,抬頭了里面那座花園別墅,知道自己進不去。
閻越從早上開始就焦急等到現在,閻家人只能哄著,暗地里讓劉媽過來看看容恩今天為何沒有過去。
轉過,南夜爵手指在方向盤上輕輕敲打,“還有,再帶句話給閻守毅,他弄掉了我的孩子,我會親手毀了他的閻家。”
劉媽驚愕,面上毫無,不住抖,南夜爵一腳油門踩出去,后視鏡中,劉媽像是木偶般站在那也不。
南夜爵翻出手機,“喂,阿元,看見外面那個人了麼?給我盯著,挖出閻越的藏之來。”
容恩的手機被南夜爵
#每次出現驗證,請不要使用無痕模式!
拿走了,臥室有電話,試著撥打,卻發現打不出去。
Advertisement
他是鐵了心的,不止囚住的,還斷了同外界的聯系。
劉媽只是個普通的傭人,本沒有想過會被人跟蹤,回到醫院,找不到別的理由,只能騙閻越,說是容媽媽病了,容恩今天趕不過來。
只是,騙得了今天,明天呢,以后呢?
阿元順利跟蹤到醫院,并通過手段查到閻越的病房。
南夜爵趕去的時候,只帶了兩個人,阿元和李航,都是他的心腹。
這會時間很晚了,接近凌晨。
男人穿著純白的手工西裝,里面,黑的襯越發襯出其冷的貴族氣質,他雙手在兜,后兩人一左一右跟著。
黑短發在走廊的白熾燈照耀下,呈現出一種妖魅,左耳上,那顆鉆石耳釘灼灼閃耀,令人不敢接近。
來到病房前,南夜爵頓住腳步,氣勢迫人。
守在外面的保鏢剛要出聲喝止,便被阿元和李航迅速出擊打暈,南夜爵推開門,“你們守在這。”
“是。”
南夜爵進去了很久,由于隔著休息室,外頭的人并不知道里面發生了什麼。
閻家人出去了,也許很快就會回來。
南夜爵出來的時候,神有些異樣,鷙的俊臉上著種復雜,他抿著,將那扇門關上的時候,閉上了狹長的目。
阿元離他最近,聽到他輕嘆了聲。
南夜爵抬起眼簾,他能看到男人眼里流溢出來的哀傷,是的,是哀傷。
帶著悲戚,刺痛人的心。
那樣的神,阿元從沒在南夜爵上看見過。
“走。”
三人剛走出病房,就見了前來查房的醫生,對方見到他們時怔了下,而過時,他迅速推開門,就見兩名保鏢倒在地上,他想也不想地沖里間。
南夜爵不急不緩地走著,幾秒后,就聽到了病房傳來的尖。
他抬了抬頭,只覺頭頂的燈晃得他眼睛睜不開,刺眼極了。
恩恩,自此之后,我們真的沒有什麼退路了吧,要麼一起生,要麼下地獄的時候,一起吧。
猜你喜歡
-
完結572 章

傲嬌總裁狂寵妻
「總裁,夫人找到了!」在哪?「在您的死對頭那……他們……他們什麼?」「他們還有一個孩子。」陸承蕭氣絕,這該死的女人,頂著我陸夫人的頭銜還敢勾搭別的男人,被我抓到你就死定了。葉挽寧,「喂,陸大少,誰說我的孩子是其他男人的。」
82.2萬字8 96028 -
完結563 章

豪門大小姐她撕了白月光劇本
顏汐是北橋市四大家族之首顏家的大小姐。 驚才絕艷,卻體弱多病、注定早夭,是很多人心中不可觸碰的白月光。 有一天她做了一個夢,夢見她所在的世界是一本小說。 小說中,為了撫平喪妻又即將喪女的傷痛,父親領養了一個長得跟她很像的女孩陳香香。 女孩柔軟如同小鹿,卻又格外治愈,比之於她更加讓人憐惜。 在讓女孩當了她一陣子的替身、經歷了各種虐心橋段之後,大家紛紛醒悟,父親、哥哥、未婚夫和朋友,紛紛把女孩寵上了天。 而顏汐這個該死的白月光卻一直要死不死,各種跟女孩作對,生生活成了惡毒女配。 最後被所有人厭惡唾棄,被設計潑硫酸毀容後跳樓身亡,死後還留下了大筆遺產,被女孩繼承。 因未能救活母親而心懷愧疚、對生死看淡的顏汐:…… 她忽然不想死了! 她撕了白月光劇本,決定遠離這群神經病,好好做科研玩音樂搞投資,掉馬虐渣兩不誤,力求活得比誰都久,讓任何人都不能打她財產的主意! 虐渣的過程中,順便出手保護了一下某清貴冷肅的美少年,結果美少年居然也是馬甲很多的大佬?
102.8萬字8 70276 -
完結7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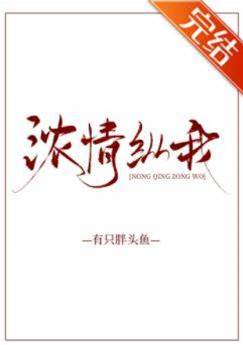
濃情縱我
宋傅兩家聯姻告吹,所有人都以為,深情如傅北瑧,分手后必定傷心欲絕,只能天天在家以淚洗面療愈情傷。 就連宋彥承本人,起初也是這麼認為的。 直到有天,圈內好友幸災樂禍發給他一個視頻,宋彥承皺著眉點開,視頻里的女人烏發紅唇,眉眼燦若朝瑰,她神采飛揚地坐在吧臺邊,根本沒半點受過情傷的樣子,對著身邊的好友侃侃而談: “男人有什麼好稀罕的,有那傷春悲秋的功夫,別說換上一個兩個,就是換他八十個也行啊!” “不過那棵姓宋的歪脖子樹就算了,他身上有股味道,受不了受不了。” “什麼味道?渣男特有,垃圾桶的味道唄!” 宋·歪脖子樹·彥承:“……?” 所以愛會消失,對嗎?? - 后來某個雨夜,宋彥承借著酒意一路飆車來到傅家,赤紅著雙眼敲響了傅北瑧的房門。 吱呀一聲后,房門被打開,出現在他面前的男人矜貴從容,抬起眼皮淡淡睨他一眼:“小宋總,半夜跑來找我太太,有事?” 這個人,赫然是商場上處處壓他一頭的段家家主,段時衍。 打電話送前未婚夫因酒駕被交警帶走后,傅北瑧倚在門邊,語氣微妙:“……你太太?” 段時衍眉梢一挑,側頭勾著唇問她:“明天先跟我去民政局領個證?” 傅北瑧:“……” * 和塑料未婚夫聯姻失敗后,傅北瑧發現了一個秘密: ——她前任的死對頭,好像悄悄暗戀了她許多年。 又名#古早霸總男二全自動火葬場后發現女主早就被死對頭扛著鋤頭挖跑了# 食用指南: 1.女主又美又颯人間富貴花,前任追妻火葬場,追不到 2.男主暗戳戳喜歡女主很多年,抓緊時機揮舞小鋤頭挖墻角成功,套路非常多 3.是篇沙雕甜文 一句話簡介:火葬場后發現女主早跟死對頭跑了 立意:轉身發現新大陸
23.5萬字8 26712 -
完結96 章

分手後我懷了大佬的崽
褚雲降和路闊最終以分手收場,所有人都嘲笑她是麻雀想飛上枝頭。幾年後,她帶著兒子歸來。見到路闊,隻是淡漠地喚他一聲:“路先生。”那一刻,風流數載的路闊沒忍住紅了眼圈,啞聲道:“誰要隻做路先生。”
24.9萬字8 2305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