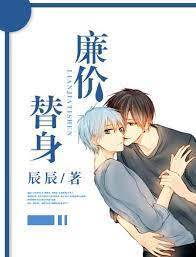《傅律師別虐了,溫醫生不要你了》 第33章 他的家事
傅知越被溫楚淮趕了出來,沈憶秋跟在他後,也被趕到了走廊上。
沈憶秋著那扇在他們麵前轟然合上的防盜門,咕噥了一句,“這個脾氣,還真是大……”
咕噥完了似乎才想起來傅知越還在邊,於是又換上了一副笑臉,“知越,我們……”
傅知越乜了他一眼,一言不發地走向電梯。
沈憶秋趕跟上,到了樓下,沈憶秋四張著,“知越,你的車呢?”
“……”傅知越回眸瞟了一眼溫楚淮家的那盞燈,“你先打車回去。”
“……”
“車費我給你報銷。”
“可是……”
“沒什麽可是,辛苦你這麽晚跑一趟。”
“我不辛苦的,知越,”沈憶秋又來拉傅知越的手臂,“隻要你需要,知越,我什麽時候都在……”
小區的花園裏,婷婷開著幾樹臘梅,火紅的花朵淩霜傲雪,連帶著襯得沈憶秋的臉頰也帶著淡淡的。
傅知越避開了沈憶秋的手,“你有點越界了。”
“為什麽?”沈憶秋眉心蹙起來,眼底在燈下有了幾分晶瑩的閃爍,“你還喜歡他?他都這樣對你了,你還喜歡他?”
“這不是你該過問的。”
“是,我知道,可是知越,我替沈老師不值。”沈憶秋笑了笑,“曾經對溫楚淮那麽好,可是溫楚淮害死了。而你,作為沈老師的兒子,還對這個殺人兇手念念不忘……”
“別說了。”傅知越抬手按住了額角跳的青筋,瞇了瞇眼睛,“我沒有。”
“你有,”沈憶秋輕語,“如果你沒有,你不會在半夜讓我過來陪你演這麽一出戲。”
“你不過就是想看看溫楚淮是不是真的跟別的男人在一起,是不是真的不要你了,想看看溫楚淮如果真的看到你和我在一起,會不會為了你心神不寧。”
Advertisement
“可是你現在看到了,溫楚淮的心裏本就沒有你,他的臥室裏,現在說不定就睡著他真正在意的人,他甚至舍不得讓你打擾他。”
傅知越緩緩抬起眸子,“閉!”
“你為什麽還是認不清現實呢?”沈憶秋輕輕掰過了傅知越的臉,“你和我一樣,都是失去了父母的可憐人,隻有我才能真正理解你,才會諒你。”
“溫楚淮不會,他是造你一切悲劇的源頭。”沈憶秋的聲音像是風的囈語,他進傅知越琥珀一樣的眸子,“忘了他吧,傅知越,我們兩個才是同類人。”
傅知越垂下眼簾,濃的睫了。
那是人猶豫不決時的表現。
沈憶秋勾起角,“知越……”
“我和他的事,用不著旁人來心。”傅知越驀地抬眼,眼底的冰冷和溫楚淮如出一轍,“就算是我想要他為我母親贖罪,那也是我們自己家的家事。”
“沈憶秋,你不過就是我母親資助的孩子。我念在我母親的善心,破格將你錄用在我邊,是為了讓你多學點本事,以後能夠在這個社會立足,不是為了讓你對我的家事指指點點的。”
“我不是這個意思,知越……”
“自己打車回去,”傅知越本不聽他的辯解,“分給你的那些案件,跟上進度,其他的事不是你該管的,別再看不清自己的位置。”
傅知越甩手上了樓,留下一個冷冰冰的背影。
沈憶秋咬了咬,著傅知越消失在對麵的樓道裏,又回眸看向了溫楚淮家的窗戶。
笑容有幾分說不清道不明的詭異。
沈憶秋走了,樓前空曠的一片雪地,留下兩雙分道揚鑣的腳印,很快又被新雪覆蓋了。
Advertisement
把傅知越和沈憶秋趕走後,溫楚淮發了一場高熱。
他自己知道自己的況,他自己就是醫生,知道這樣不聽話的病人在醫生眼裏都是難纏頭,所以幹脆也不去醫院裏給自己的同事添麻煩,自己在家吃點藥算了。
隻是這班是上不了了,於是給科室裏的其他醫生打電話調班。
院長要求提到十五萬一年的申請應該是還沒批下來,這幾天也沒再來找溫楚淮。
客廳裏的電視開著,音量剛剛好能充盈整個屋子,溫楚淮伴著窗外的雨聲,昏昏沉沉聽著午間新聞——
“近日,龔德院士團隊對外發布消息,稱其針對腦絡紊癥的研究已經取得重大進展。龔德院士是近半個世紀以來腦外科領域的佼佼者,長期致力於腦外科醫學領域的研究和創新。”
“他強調,醫學研究的道路是漫長而艱辛的,但為了人類的健康,吾輩當自強不息,勇往直前……”
屏幕上,一灰西裝的主持人慷慨激昂,臉上洋溢著喜悅。
畫麵一轉,是在國家級的會議廳裏,一麵牆大的屏幕角落站著文質彬彬的年輕人,給在場的各位展示著PPT,臺上一排座位,正中央坐著一個須發皆白卻神矍鑠的老人,誌得意滿。
是今天絕對的主角,龔德。
高機位的攝像頭掃視全場,第一排坐著兩鬢霜白的各國行業領頭人,後麵是各個行業被邀請來做這場見證的大佬。
就連會議廳的過道也滿了黑的記者,閃燈亮個不停,快門聲響一片。
畫麵再一轉,是網上的實時評論,滾詞條。
“國士無雙。”
“這才是現在年輕人真正應該崇拜的偶像!”
Advertisement
“院士啊!人家可是院士啊!”
讚之聲不絕於耳,將龔德誇得天上有地下無。
不知是誰發了一句,“我怎麽記得原來吃過這個人的瓜,說他榨手下學生來著,當時還鬧得沸沸揚揚的,後來一夜之間那些人就沒消息了。”
溫楚淮勉強集中了幾分神,點進去看,下麵零零星星幾條回複——
“我是醫學生我記得,但互聯網似乎是沒有記憶的。”
“也不知道幾年前的那些人現在怎麽樣了,不過看這人現在名氣這麽大,當年跟他對著幹的那些人,估計是沒有什麽好下場。”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