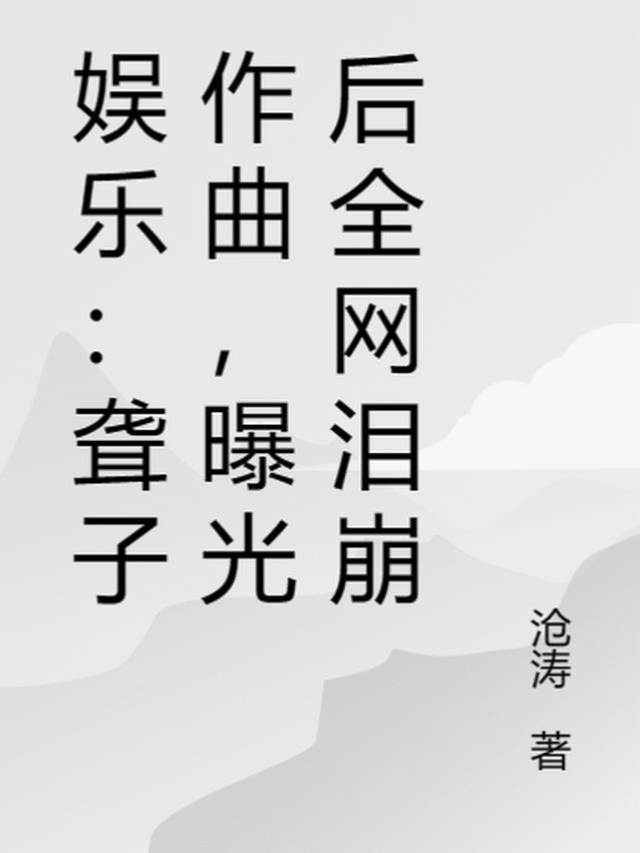《馥欲》 40.白漿
“你這個大騙子,我不相信你了……”
小人好像就只會這麼一句話,翻來覆去地說,聲音卻愈發甜,沉溺,也愈發沒有殺傷力,到最後仿佛演變小貓玩笑的抓撓,人間的呢噥撒。
一側雪在男人手中已呈現出漂亮的紅,被得近乎已經看不出手指痕跡,那種著靡的從宋持風指間如乍泄的春般現。
“不相信我了?”宋持風將的角度稍稍調整,隔著西裝將滾燙的隆起嵌的間,模仿著的頻率,頂撞著的。
寧馥耳畔全都是蓮蓬頭的水聲,沒聽清宋持風問了什麼,隻囫圇地嗯了兩聲。
浴室裡已經全是熱的水汽,細不可見的水珠布在空氣中,黏著著那種熱氣,如同細細的蛛網,鋪天蓋地的將兩人籠在裡面,極難消散。
寧馥的腰已經完全了,整個人幾乎都要塌陷下去,全靠宋持風那一隻手撐著。
低著頭不住發出難耐的息,長發早就被打大半,垂墜前。
“宋持風……嗯……”
男人松了的,帶著寧馥的手自己握住蓮蓬頭的柄,然後一手摟著的腰,另一手將蓮蓬頭的水流開大——
懷裡的小人頓時一個激靈攀上高,宋持風摟住不讓人摔倒的同時把水關掉,從手裡把蓮蓬頭出,掛了回去。
寧馥的臉上已經布上一層淺淺的紅,紅之上是一層如水霧般的汗氣。
在宋持風的攙扶下坐回馬桶蓋上,才發現宋持風上也是了個徹底。
他的白襯完全,地在上,白與織混合,勾勒出壯的線條。
宋持風的皮不算白,是那種相當健康的,每一次穿白襯的時候,領口與袖口呈現出來的差都相當。
Advertisement
現在服一,被半出來,腹部塊壘分明的廓人看著眼熱極了。
寧馥別開眼,就看宋持風轉在旁邊洗手臺上洗了把冷水臉,又走回邊拿起蓮蓬頭:“頭髮打了,一起洗了吧?”
本來以為以宋持風的格今天一定會做到最後,愣了一下,抬頭看他。
對上寧馥眼底那意外神,宋持風是真氣笑了:“寧馥,我在你眼裡就這麼管不住下半?”
聞言,寧馥大概知道不能說對,便沉默下來,一雙眼睛依舊目不轉睛地盯著他看。
好像在說:難道不是?
宋持風有一瞬間的失語,調好水溫之後一點點打的發,才如同自言自語般說:“我什麼時候騙過你,小沒良心的。”
耳畔都是水聲,不是蓮蓬頭出水的聲音,還有下水道下水的聲音,嘩啦作響。
但在這一刻,男人的低語卻很準確地傳了寧馥的耳道,讓小小地生出了一點別的緒。
“剛才不就騙了,你說隻洗澡的。”地說。
但其實也想不起來宋持風有沒有騙過,只是這句話就讓寧馥想起那晚在川城,不由分說先給他一頓質問。
“嗯,我剛就應該閉著眼睛讓你當扶手用。”宋持風把洗發水倒進掌心,語氣好似有些無奈:“反正到最後也是自找苦吃。”
聽見男人的話,寧馥稍稍回頭看了一眼。
他西裝是純黑,現在又打了水更是連一點反也不見,黑一團糊。
但只要宋持風側去拿東西,間那鼓脹的山包便在浴室白的瓷磚牆映襯下更顯膨脹。
頭上已經全都是洗發水,估計宋持風生平第一次給人洗頭,控制不好量,得有點多,白泡把的黑發全都蓋住,讓寧馥看起來好像戴了一頂茸茸的羊帽子,不知是不是出於愧疚,看著他的眼神也跟一隻小羊似的,格外乖巧安靜。
Advertisement
宋持風與對視兩秒,間更是一陣湧灼燒,他只能掌心扣住的腦袋,把人那張小臉兒轉到另一側。
“要衝了,閉上眼。”
好不容易給寧馥洗完澡和頭,宋持風把換上新睡和的寧馥抱出去之後,直接回頭把的襯給了。
男人上壯,了服之後腰背極為清晰凌厲,伴隨著他把襯甩進髒簍的作,線條一陣拉扯抻張,再回到原狀時卻又更多了幾分繃。
直到此刻,他上隻穿著一條象征著文明的西裝,腰間皮帶依舊克制扣,整個人卻如同一頭已經完全進戰鬥狀態的野,每一寸下都躁著一蓄勢待發的味道。
寧馥幾乎不敢在現在對上宋持風的目,垂著眸,就聽宋持風啞著嗓子跟說了一聲:“等我一會。”便轉離開了房間。
男人腳步聲遠去,這個城市頂端的高層頓時陷一片死寂。
頭髮還沒吹,隻裹著一條厚實的巾,坐在床上盯著腳踝的傷出神。
藥膏剛才已經完全被進皮裡,再加上熱水一衝,現在整個扭傷的位置裡好像湧著一包火。
寧馥猜測宋持風可能是去換服,畢竟他剛才服子全都。
屏住心中雜的想法,拿起手機看了一會兒,回了幾條林詩筠們的消息,還有余曉楓等舞團同事的消息,回過神來的時候,已經十分鍾過去了。
十分鍾說長不長,但對於換服來說,也不短了。
寧馥又在床上坐了一會兒,偌大的房子裡卻聽不見任何一點靜,在這樣一個夜裡,靜到令人忍不住心慌。
坐在的床上,愈發覺如坐針氈,忍不住了一聲:“宋持風?”
Advertisement
沒有反應。
客廳的燈關著,從明亮臥室朝外看,只能看見一片空的黑暗。
寧馥心裡開始有些不安,又連著了兩聲均無得到回應之後,便忍著疼下了床,小心翼翼地把傷的腳送進拖鞋裡。
以前慶城大學就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歷史系有一個老師,有先天心臟病,有一天晚上回家路上忽然被一隻從上躍下的野貓嚇得直接當場休克過去,送醫院之後沒搶救回來。
雖然宋持風沒提過他有什麼傳病史,雖然不是那麼喜歡他,但是要他真的倒在自己面前,寧馥也不可能袖手旁觀。
扭傷的腳幾乎不能落地,寧馥只能慢慢地挪到牆邊,一路扶著牆艱難往外走。
在此之前寧馥從沒覺得房間太大也是一種困擾,等好不容易到門邊,額頭又有點輕微的汗意了。
一片漆黑的客廳果然沒有任何人聲,但旁邊房間的房門卻是沒有完全關住,而是留了一道細細的。
燈從隙中了出來,落在地上,筆直一道,就像是穿行於海面的燈塔柱,吸引著的目,指引的方向。
寧馥朝燈的方向一瘸一拐走去,在走到房間門口的時候卻依舊沒能聽見任何聲音。
心的不安在擴大,左手著手機,右手推開了房門。
“宋持……”
風字尚未出口便地噎在嚨口,從剛才起一直默不作聲的男人此刻背對著門口,背後的繃一片勁峭山巒。
他手落在間,下半的西裝並沒有第一時間去,浸飽了水的黑布料在他的作下地包裹著那雙有力下肢。
頂燈暖黃,自上而下,男人雙子面料與匯織一片極力量的明暗錯——
Advertisement
聽見聲音,宋持風回過頭,眉眼間濃重在對上雙眼的瞬間沒有毫輕減,反倒是因為被發現,他索不再抑那種本能的息。
“一個人待著,害怕了?”
他的聲音比剛才還要嘶啞,好像聲帶被滾燙灼燒損壞,如同一張格外糲的砂紙,著聽者的鼓。
剛才宋持風就聽見寧馥在他,卻沒想到會這樣找過來。
寧馥已經完全愣在了門口,看著男人手裡依舊握著自己的,上下來回地。
在視角看不見那,可只是看見男人的手臂青筋隆起,伴隨著作,一張一弛,便已經足夠人浮想聯翩。
“我是以為……”
有點尷尬,但比起尷尬更多的還是不知所措。
沒說完的話斷在了邊,就在怔愣地進退兩難間,宋持風卻開口:“來,你過來。”
寧馥一僵,本能地生出些猶豫,但想到宋持風憋到現在也沒真的,讓的懷疑格外站不住腳,還是一瘸一拐地挪了進去。
“坐下來,把手給我。”
宋持風用眼神示意他面前的床,寧馥有些不自在地坐過去,空氣中屬於宋持風的男氣息頓時撲面而來,趕側過頭去,不想看他間的猩紅,手腕就已經被男人拉起。
他握住的纖細皓腕,直接帶著握住了自己的刃——
寧馥下意識地了一下,只是這一點點輕微的力道在男人面前確實微不足道。
宋持風的大掌強地從外包裹住的手背,帶著用自己的掌心,從到頂端,來來回回細致地弄過去。
雖然都是手,但寧馥的手與自己的手顯然是天差地別。
無論是覺還是其他,都因為寧馥的出現而得到了極大的刺激與滿足。
寧馥被那氣息烘得臉上和耳朵上都在發燙,不想多看,便別過頭去,隻留一隻手給他用。
所有的都在倒退,只有掌心的覺與鼻息的嗅覺在不斷變得敏銳。
空氣中所有似有若無的氣息,荷爾蒙的味道,都像是在激化空氣中湧的流,讓寧馥恨不得就隻留下一隻手在這裡,剩下整個人都直接消失掉。
“寧馥,抬頭,看著我。”
不知過去多久,久到寧馥覺自己的手掌心都開始燙得發麻的時候,男人的沉聲再次降臨。
本能地聽從,卻在抬起頭的瞬間被奪去了呼吸——
男人附,將舌稔地送的牙關,舐勾吻。
那熱滾的柱狀也終於狠狠一抖,在掌心出一濃濁白漿。
猜你喜歡
-
完結850 章

閃婚當晚,禁欲老公露出了真面目
【重生打臉+馬甲+懷孕+神秘老公+忠犬男主粘人寵妻+1v1雙潔+萌寶】懷孕被害死,重生后她誓要把寶寶平安生下來,沒想到卻意外救了個“神秘男人”。“救我,我給你一
87.7萬字8.18 32804 -
完結355 章

予你萬般偏愛
隱婚兩年,終于等到他提出離婚,寧憧以為解脫了到酒吧買醉,誰知轉頭就碰上前夫他咬牙切齒冷笑:“背著我找男人?” 寧憧暗道大事不妙,轉頭就想逃 奈何前夫大長腿,直接將她抓了回去。 “我們已經離婚了!” “那就復婚。” “是你提的!” “有人說過我不能反悔嗎?” “你可是總裁,不能出爾反爾!” “我是個慘遭妻子欺騙的老公。” 寧憧欲哭無淚,前夫哥你能不能別死纏爛打。
61.6萬字8 14306 -
連載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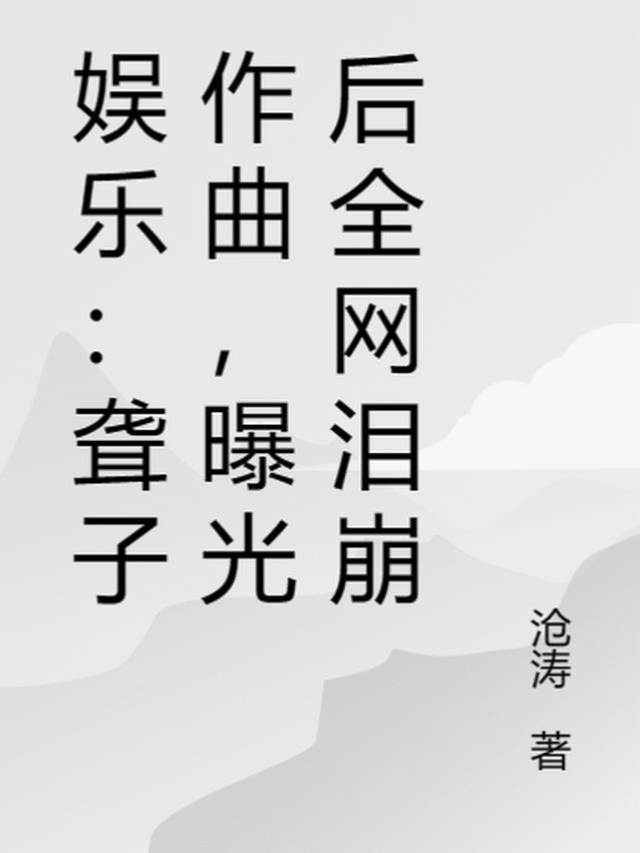
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
微風小說網提供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在線閱讀,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由滄濤創作,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最新章節及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目錄在線無彈窗閱讀,看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就上微風小說網。
23.8萬字8.18 480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