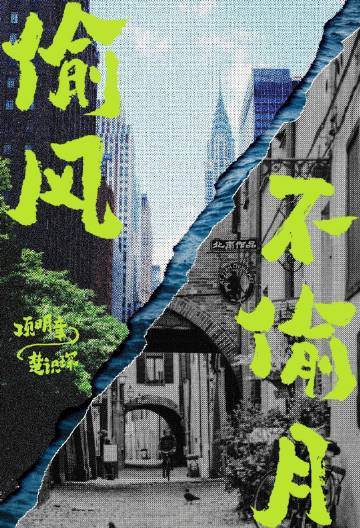《和隱婚老公戀綜曖昧,氣哭女嘉賓》 第207章 受傷
就在這時,電火石間,一道影猛地竄出,隨著匕首的鈍聲傳來,有人被推倒,有人被撞擊,還有驚呼尖的聲音在夜裏響起,四周的保鏢和藏在暗的人手聞聲而,卻在看清眼前一幕時,驀得停下作。
原本狼狽蜷在地的傅玉書,此時此刻,正站在傅玉棋後,本該刺向傅玉嫿脖頸的匕首,如今就握在他的右手,抵在傅玉棋的脖頸。
傅玉嫿被他擋在後,順利逃傅玉棋的控製。
所有這一切,發生在瞬息之間,眾人甚至來不及反應,就已經看到局勢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讓你的人,放下武。”
“傅玉書,你真是好得很!我還是低估了……”
“閉。”
傅玉書打斷了傅玉棋的聒噪,手裏的刀往前送了送,很快,有什麽東西將傅玉棋淺的外衫染出一層暗。
“將武踢過來。最邊上那個,用服將所有人的手綁到後,五分鍾的時間,慢了,我就殺了他。”
“你們不要聽他鬼扯!傅玉書,我就不信你真的會殺了……”
一聲悶響,替代了傅玉棋的嚷。傅玉書以手作刀,直接砍向傅玉棋後脖頸,直接將他敲暈了過去。
將傅玉棋趴放在地上,傅玉書直接坐在他的背上,匕首尖端抵在他的脖頸。
“還有四分半。”
傅玉書人狠話不多的模樣,終於讓這些對傅玉棋忠心耿耿的人想起,他們麵對的,不是以往那些人,而是名聲在外的傅家家主。
幾乎是下意識的恐懼,讓這些人再也不敢反抗,真照著傅玉書的要求,一個個認命似的被綁起來。
“過來。”
等候的功夫,傅玉書看向傅玉嫿,正招手,卻最終還是放下,甚至往擺下藏了藏。
Advertisement
傅玉嫿著傅玉書,沒有。
於是傅玉書耐著子解釋:“過來,我給你割繩子。我沒帶手機,你幫我給刁槐打電話,讓他帶人過來。”
傅玉嫿這才上前,依言照做。
傅玉書依舊坐在地上,抬頭,視線落在傅玉嫿脖頸的痕,頭微,“脖子上的傷,很疼吧?還有沒有傷到別的什麽地方?”
傅玉嫿搖了搖頭。
得益於傅玉書先前的警告,傅玉棋這半天隻是綁著,並沒有做出什麽過分的事。
脖子上的傷口看上去嚴重,其實並沒有那麽疼。
隻是著傅玉書這模樣,傅玉嫿難免再次想起曾經自己每一次傷後,傅玉書又心疼又生氣的畫麵。
現在的他,隻剩平靜。
傅玉嫿覺得,自己已然看不懂傅玉書了。
刁槐早就在別墅外的半山觀景臺帶人候著,電話接通的一瞬間,幾乎是原地彈起來,領著人火速趕往衡山小築。
一到現場,看到一群被綁起來的人,先是一愣,不過他很快看到傅玉書,連忙上前,“先生。”
“收拾一下現場,順便打電話給南城警方,讓他們過來拎人。至於傅玉棋……”傅玉書看一眼下的人,“也一並過去。”
說著,傅玉書準備起,卻在即將站起的時候,子晃了晃,又坐了回去。
得虧傅玉棋還暈著,沒有任何不適。
“坐久了,有點暈。”傅玉書難得解釋了一句,然後朝著刁槐出右手,“拉我一把。”
刁槐連忙將人拉起來。
傅玉書走到一旁,從草坪上撿起先前掉落的男款風,走過來遞給傅玉嫿。
“夜裏涼,先穿上擋擋風,別冒了。等會讓刁槐送你去醫院做個檢查,磕到的地方……讓大夫開點藥。”
傅玉嫿著他,沒有說話,也沒有接。
Advertisement
一整天下來,信息太多,到的衝擊太大,此刻甚至有些理不清自己的緒,也有些看不明白傅玉書。
見不吭聲,傅玉書輕歎一口氣,隻當是被晚上的事嚇壞了,一時反應不過來,於是雙手抖開風,替傅玉嫿披在上,然後退開兩步。
“今天發生這樣的事,是我的錯,怪我沒有看好玉棋。不過不管你願不願意相信,我保證,今後你在南城,不會再到這樣的事。”
說著,傅玉書看向刁槐,“去開車,送嫿嫿去醫院。”
嫿嫿兩個字,仿佛一顆石子跌落湖心,雖隻在表層激起漣漪,卻最終一路落至湖底河床。
刁槐來到傅玉嫿邊,手做請,“玉嫿小姐,請——”
“你還想瞞我多久?”
傅玉嫿著傅玉書,忽然開口,完全無視了一旁的刁槐。
同樣在今天到大量信息衝擊的刁槐見此,頓時極有眼力見的往後退了幾步,把地方給當事人讓出來。
傅玉嫿一步步朝著傅玉書走去,在距他隻有一步之遙時,忽然抬手一把揪住傅玉書的領,將他猛地往下一拽,讓那張清冷玉麵和自己視線平齊。
“我不是傅家的兒,母親當年也不是你害死的,當初的現在的所有的一切都跟你沒關係。傅玉書,所有這些你到底還要瞞我到什麽時候?是不是就算傅玉棋真的殺了我,你也依舊不肯對我說一句實話?”
“有我在,沒人能得了你。哪怕是傅玉棋。”
傅玉書睫微閃,眼底映著細碎的燈,不知怎的,有種莫名破碎蒼白的,說出口的話,也不是什麽豪言壯誌,卻又讓人無比篤定,他做得到。
但傅玉嫿問的,明明不是這個,想聽的,也不是這個答案。
Advertisement
“今晚我想繼續住在衡山小築,還是以前我的房間,傅先生若是想清楚了,可以隨時來找我。我再給你最後一晚上的時間考慮,要不要跟我說實話。若傅先生依舊覺得沒什麽話可與我說,等過了今夜,我會立刻返回M國,從今往後,不再踏足南城,以免礙了傅先生的眼。”
傅玉嫿定定地著傅玉書的眼睛,說完這些話後,鬆開傅玉書的領。
視線移向別墅,傅玉嫿不再看他,也不等傅玉書的回複,抬手攏了攏上的風,朝著宅邸走去。手到風時,傳來一陣濡,傅玉嫿作微頓片刻,抬手放在眼前。
昏暗的燈下,手指上沾滿了不知名的深,風一吹,帶著一鐵鏽般的腥氣。
傅玉嫿腦袋一轟,不知道想到什麽,猛然回頭。
與此同時,後不遠,刁槐驚呼出聲。
“先生!您的手!”
-
被醫院的消毒水氣息包裹,傅玉嫿終究沒能留在衡山小築過夜。
隨著刁槐那一聲喊,終於知道那濡風的是什麽。
是。
傅玉書的。
剛才為了從傅玉棋手裏奪刀救人,傅玉書直接用手去擋刀,整個左手差點被那把匕首刺了個對穿,為了避免被其他人發現後,他隻一人難以震懾那麽多人,也為了避免傅玉嫿擔心,傅玉書一直強忍著疼痛,連句悶哼都沒有,乃至於就連傅玉嫿都沒有發現他的異常。
直到最後流得太多,終於被刁槐發現異常。
VIP病房裏,傅玉書被按著躺在病床上,左手用紗布裹了厚厚的一圈,讓那清冷矜貴的公子模樣,多了幾分說不清的稽與俗常煙火氣。
按照醫生的說法,若是再晚到半個小時,傅玉書的左手便是神仙也難救。
傅玉嫿坐在旁邊,脖子上也纏了一圈紗布,兩個人四目相對片刻,傅玉書忽然抬起頭看向刁槐,刁槐當即眼觀鼻鼻觀心,默默溜出病房。
門關上後,房間裏隻剩下傅玉書和傅玉嫿兩個人。
“你在療養院裏和傅鴻遠說的那些話,我全都聽到了。傅玉書,我討厭被人瞞在鼓裏,你若真的如傅玉棋所言,是為了保護我,那麽我想,我有知道所有真相的權利。”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816 章
傅先生,別來無恙
"三年前她九死一生的從產房出來,扔下剛出生的兒子和一紙離婚協議黯然離開,三年後薄情前夫帶著軟糯萌寶找上門……傅雲深:"放你任性了三年,也該鬧夠了,晚晚,你該回來了!"慕安晚冷笑,關門……"媽咪,你是不是不喜歡我!"軟糯萌寶拽著她的袖子可憐兮兮的擠著眼淚,慕安晚握著門把手的手一鬆……*整個江城的人都道盛景總裁傅雲深被一個女人勾的瘋魔了,不僅替她養兒子,還為了她將未婚妻的父親送進了監獄。流言蜚語,議論紛紛,傅大總裁巋然不動,那一向清冷的眸裡在看向女人的背影時帶著化不開的柔情。"晚晚,你儘管向前走,我會為你斬掉前方所有的荊棘,為你鋪一條平平坦坦的道路,讓你一步一步走到最高處。""
152.3萬字8 29672 -
完結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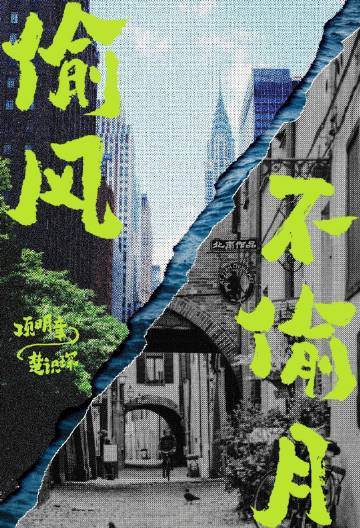
偷風不偷月
穿越(身穿),he,1v11945年春,沈若臻秘密送出最后一批抗幣,關閉復華銀行,卻在進行安全轉移時遭遇海難在徹底失去意識之前,他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后來他聽見有人在身邊說話,貌似念了一對挽聯。沈若臻睜開眼躺在21世紀的高級病房,床邊立著一…
39.3萬字8 6359 -
完結420 章

莫少逼婚,新妻難招架
沈南喬成功嫁給了莫北丞,婚後,兩人相敬如冰。 他憎惡她,討厭她,夜不歸宿,卻又在她受人欺辱時將她護在身後,「沈南喬,你是不是有病?我給你莫家三少夫人的頭銜,是讓你頂著被這群不三不四的人欺負的?」 直到真相揭開。 莫北丞猩紅著眼睛,將她抵在陽臺的護欄上,「沈南喬,這就是你當初設計嫁給我的理由?」 這個女人,不愛他,不愛錢,不愛他的身份給她帶來的光環和便意。 他一直疑惑,為什麼要非他不嫁。 莫北丞想,自己一定是瘋了,才會在這種時候,還想聽她的解釋,聽她道歉,聽她軟軟的叫自己『三哥』。 然而,沈南喬只一臉平靜的道:「sorry,我們離婚吧」
108.5萬字8 44387 -
完結211 章

重逢大佬紅了眼,吻纏她,說情話
那年裴京墨像一場甜蜜風暴強勢攻陷了許南音的身體和心。 浪蕩不羈的豪門貴公子放下身段,寵她入骨,她亦瘋狂迷戀他。毫無預兆收到他和另一個女人的訂婚帖,她才知道自己多好騙…… 四年後再重逢,清貴俊美的男人將她壓在牆上,眼尾泛了紅,熱吻如密網落下。 許南音冷漠推開他,“我老公要來了,接我回家奶孩子。” “?”男人狠揉眉心,薄紅的唇再次欺近:“奶什麼?嗯?” 沒人相信裴京墨愛她,包括她自己。 直到那場轟動全城的求婚儀式,震撼所有人,一夜之間,他們領了證,裴公子將名下數百億資產全部轉給了她。 許南音看著手邊的紅本本和巨額財產清單,陷入沉思。 某天無意中看到他舊手機給她發的簡訊:“心肝,我快病入膏肓了,除了你,找不到解藥。你在哪裡?求你回來。”她紅了眼眶。 後來她才明白,他玩世不恭的外表下藏著多濃烈的愛和真心。 他愛了她十年,只愛她。
38.8萬字8.33 6925 -
完結105 章

被讀心后,她發瘋創飛所有人!
溫馨提示:女主真的又瘋又癲!接受不了的,切勿觀看!(全文已完結)【微搞笑+玩梗+系統+無cp+讀心術+一心求死“瘋癲”又“兇殘”女主+火葬場+發瘋文學】 她,盛清筱一心求死的擺爛少女,有朝一日即將得償所愿,卻被傻逼系統綁定,穿越進小說世界! 一絲Q死咪?是統否? 強行綁定是吧?無所謂,我會擺爛! 盛清筱決心擺爛,遠離劇情,研究自殺的101種辦法,系統卻不干了,又是開金手指讀心術,又是給她回檔! 很好! 既然如此,那大家都別活了! 果斷發瘋創飛所有人,上演現實版的皇帝登基! 后來,幡然醒悟的家人分分祈求少女不要死! 對此,盛清筱表示:關我屁事! 死局無解,救贖無用,唯有死亡! 最想活的系統綁定最想死的宿主,開局則死局! 【女主一款精神極不穩定的小瘋子,永遠不按套路出牌,隨心所欲,瘋癲至極,一心求死最終得償所愿!】 本小說是在作者精神狀態極度不穩定下所創造出來的癲文,沒有邏輯,就是癲。 *回檔很重要
19萬字8 600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