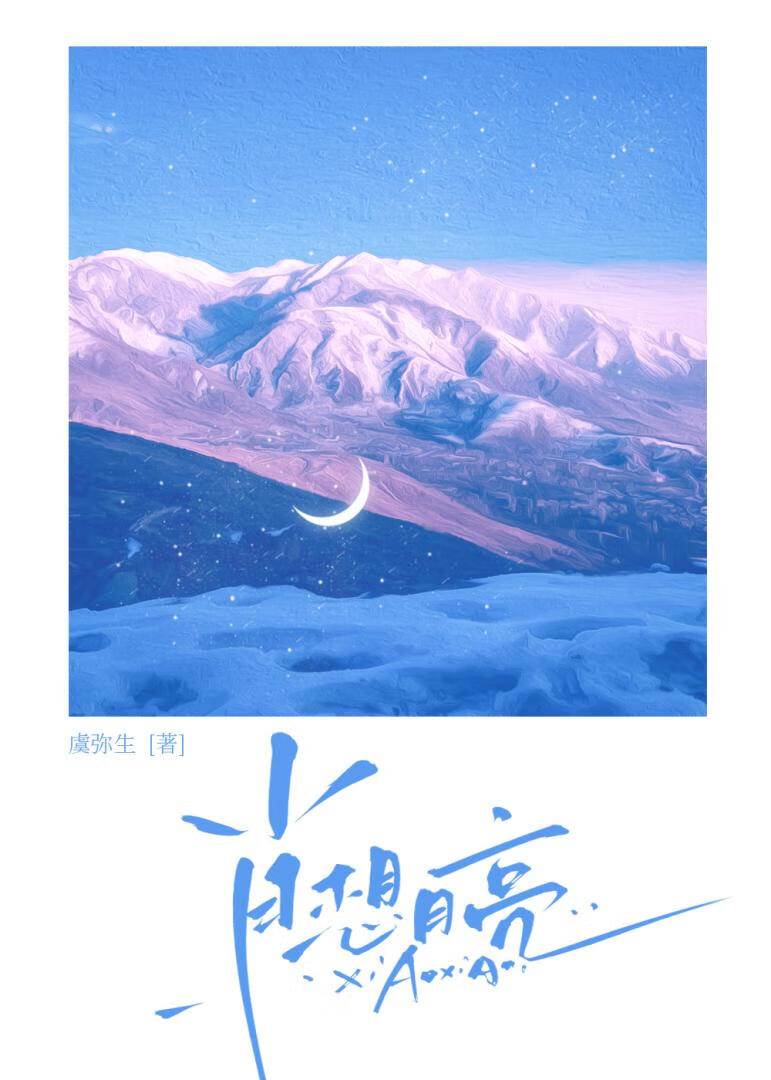《師尊她養虎為患》 第8頁
其實對于小白虎而言,疼痛是最不值一提的事。在大雪天,對于痛的知覺會變得非常麻木。
然而,傷也意味著。
就算是山間的猛,在嚴寒的冬天也很難尋找到合適的獵。更何況有一條不再靈敏,這樣一只傷的,在這寸草不生的冬天,幾乎沒有活下來的可能。
——而侍衛們,只在乎討好虎族,本不會在意他的死活。
于是,在這個萬籟俱寂的冬夜,等到警覺地確定所有的侍衛都已經離開后,小白虎還是出來覓食了。
可是走了不到半座山,小白虎就不得不停下來、緩解一下那條傷的疼痛。
好香。
他不控制地盯著遠暖黃窗戶里那咕嚕嚕的粥。
小孩兒吞咽了一下食的香氣,企圖緩解腹部的燒灼。
然而,在聽到了開門聲后,小白虎立馬警覺地藏了起來。
……
姜貍低頭看著那只虎爪印,很自然地順著腳印找了一圈,發現那虎爪消失在了林深。
并沒有再追下去,而是回到了那間木屋。
想了想,姜貍找了個大碗,將自己的晚飯分了一大半出來。
藏在一塊大石頭后面的小白虎遠遠地聽見了大門“吱呀”一聲,下意識地擺出了進攻的姿態,把傷藏在后面,警惕著那邊的靜。
“咚”
——是什麼東西放在地上的聲音。
許久之后,小白虎從大石頭后面出一個腦袋來。
Advertisement
地上放了一碗散發著溫度的粥。
……
姜貍早上起來的時候發現粥都凍得發了。
經過了一整夜,那梅花腳印也早就被大雪覆蓋。
姜貍比畫著自己爪子的大小,認為不太可能是玉浮生;畢竟玉浮生的本是一只巨虎。
不過,白天姜貍仍然去了一趟鎮上,買了一些靈。
快天黑的時候,又在門口放了一碗粥。
想起了很多年前自己在滄州逃亡的經歷,姜貍在陶罐下面放上了有點余溫的炭火,讓粥不至于涼得太快。
然而一整夜,外面都再也沒有任何靜。
……
第二天,腸轆轆的小白虎仍然一無所獲。
但是小白虎發現了一件很奇怪的事。
那戶人家門口又放了一碗粥。
小白虎知道山腳下會有人捕獵野。
一年前,也是這樣的一個冬天,渾被水打的小白虎也曾試圖靠近人族的居所取暖。但是很快,小白虎就得到了一個嚴峻的教訓:一只捕夾。
小孩兒警覺地看著那碗粥,朝著粥出了尖銳的牙。
……
第三天。
小白虎是被醒的。
玩忽職守的侍衛們仿佛終于想起來了山上的院落里還有一個小孩。
院落的大門被推開了。
侍衛們丟過來了一只烤兔子。
就在腸轆轆的小孩兒下意識地準備去抓那只兔子的時候——
他聽見了那三個侍衛正在談:
“什麼妖皇太子?你看,他既不會說話,連吃東西都只會用手抓。”
Advertisement
“不信?那你看他一會兒怎麼吃不就知道了?”
那三個侍衛發出了放肆的大笑聲。
小孩兒的作僵住了。
他出了尖銳的牙,朝著他們發出了從嚨里的、屬于虎類的嘶啞威脅聲;甚至還擺出了進攻的姿態,仿佛下一秒就要撲上來咬死他們。
但是越是出那種被激怒、如臨大敵的樣子,對面的侍衛就笑得越發放肆。
“喲,多兇啊,只可惜咯,半點靈力都沒有。”
“小太子,你吃呀,怎麼不吃了?”
舉在小孩面前的烤兔子很香。但是小孩兒卻再也沒有手。
而是用那雙漂亮的、碧綠的眼睛死死地盯著那三個侍衛,看著他們的管上下起伏,想象著牙齒刺破皮、咬斷他們脖頸的畫面。
小孩兒的牙齒在嘎吱嘎吱地打架,仿佛是在嚼碎骨頭一般,碧綠的眼睛,像是燃燒起來的鬼火。
但是漸漸地,火熄滅了。
忍下去。
侍衛們來的次數不多,每次丟過來一些殘羹冷炙,也僅僅是為了取樂看笑話。
一開始小白虎聽不懂,他不知道他們為什麼笑;后來漸漸地,他知道了他們那是在笑他用人形吃東西,卻像是類一樣,太野、太難看。
小白虎也曾經嘗試著學他們的樣子,但是他們笑得更大聲了。
每一次,每一次都是這樣。
——忍。
忍下去。
但是……到底要忍多久呢?
沒有吃那只烤兔子的下場就是半夜得睡不著。
Advertisement
小孩兒睜著眼睛看著那扇風的窗里飛進來的雪花。
突然間想起來了那碗飄著香味的粥。
第四天。
侍衛們沒有來,那只烤兔子也不翼而飛。
小白虎醒得很早。今天那條傷沒有什麼知覺了。
小白虎在山里逡巡了很久,翻找過每一個可能藏著獵的角落,但是傷拖慢了小白虎的速度,能夠逡巡的范圍變小了很多;敏銳的聽覺也因為變得遲鈍了很多。
一無所獲的小白虎來到了山腳下,又看見了那碗粥。
小士: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640 章

被退親后我嫁給了當朝大佬
林家大姑娘曾是名滿京城的高門貴女,但是自從落水后就各種不順。 先是自小定親的未婚夫來退婚了。 沒關係,驍勇善戰的鎮國公世子也很棒! 然後鎮國公世子尚主了。 沒關係,太傅家的探花郎才貌雙全、文采非凡。 結果探花郎跟他的表妹暗通款曲了…………幾經輾轉,聖上下旨將她賜婚給全京都未婚女郎都夢寐以求的無雙公子。 從此誥命加身,一路榮華……曾經看不起她的人,最後還不是要在她面前低頭行禮!
106.1萬字8 15617 -
完結175 章

閃婚後偏執大佬他熱情似火
【閃婚甜寵 先婚後愛 雙潔】*十八線小明星鍾鹿在一場飯局上被人算計,陰差陽錯招惹了一個男人。後來她才知道,那個男人是商場上令人聞風喪膽的狠角色厲競東,聽說他為了奪權上位弄死了大哥、弄癱了二哥、將親爹氣到中風,妥妥瘋批偏執反派一個!從此鍾鹿遇到那人就繞路走,甚至決定假裝那一晚失憶。誰知某次宴會,她卻被這位大佬給堵在牆角,對方瞇著眼慢悠悠地說:“聽說鍾小姐失憶了?沒關係,我幫你回憶一下那晚,鍾小姐左邊胸口有顆痣,側腰——”鍾鹿用力捂住他的嘴,欲哭無淚地招供:“我記起來了,記起來了……”原以為這位大佬不過是作弄作弄她,可她怎麼覺得他看她的眼神越來越灼熱?後來某一天。大佬:“結婚嗎?能幫你虐渣打臉,還能讓你在娛樂圈風生水起的那種?”鍾鹿沒有任何猶豫地拒絕:“不結。”開什麼玩笑,跟這種兇狠偏執的大佬結婚,她分分鍾能被弄死吧?大佬挑了挑眉,一個冰涼且極具威脅性的眼神看過來:“不結?”鍾鹿想了想自己聽說的那些關於他的詞:狠戾殘酷、兇名遠播、隻手遮天,縮了縮脖子,她顫巍巍地應道:“結、結一下,也不是不可以……”
32.8萬字8 46156 -
完結179 章

肆意誘吻
【先婚後愛 男二上位 蓄謀已久 雙潔 3歲年齡差 男二女主久別重逢】【人間尤物嬌軟女主 深情款款釣係小茶總】(強調,不是大女主戲份,不是女強文)以前她聽媽媽說,等她大學畢業就跟江望訂婚,然後結婚,這一等便是很多年。公司倒閉,父母離世,她也沒等到江望提的結婚。隻等來了江望讓她去相親。*後來,溫宴初褪下了為他穿上的枷鎖,重新做回自己。一身清爽白裙,宛如盛開的雪蓮,明豔的讓人心動。曾經放浪不羈的江望將人緊緊擁入懷中,聲音哽咽,似是祈求,“初初,我們結婚吧。” 女孩從他懷中掙紮出來,神色自若,“不好意思,我......”身後傳來一聲醇厚低沉的聲音,“老婆,該回家了”江望回頭看見的是十年前被他趕跑的男人。 小姑娘笑顏如花,躲進男人懷中,這場麵讓江望覺得異常刺眼和諷刺。時俞抓住小姑娘的手放在自己胸口。“老婆,我吃醋了。”“他隻會傷你心,不像我隻會疼你。”*“時俞,你的手機密碼是多少?”“0521”小姑娘睫毛顫抖,摁開了手機的秘密。男人的聲音很輕,“記住了嗎?是多少?”“0521”嗯,我也愛你。你以為的意外巧合,都是我對你的蓄謀已久
31.7萬字8.18 12231 -
完結283 章

虐哭嬌寵寶貝,厲爺他偏執的要命
【腹黑】 【偏執】 【甜虐】 【追妻】 【小哭包】 【he】(非女強~)偏執腹黑大灰狼&乖巧溫柔小白兔G洲人盡皆知,厲爺身邊的小姑娘,有著傾國姿色,更有曼妙身軀,堪稱“人間尤物”,隻可惜是個說不清話的小結巴。他以贖罪的理由將人欺負盡,卻又在她委屈落淚時自己偷偷心疼。他一遍遍告訴自己不可以對她好,可是又一次次清醒著墮入名為愛的深淵,甘願放下一切,對她俯首稱臣。“疼嗎,疼才能長記性。”嘴上說著殘忍的話,卻又認命般俯下身子輕輕吻去她眼角的淚花。......令眾人萬萬沒想到的是,最後這個小結巴居然還真就成了厲家主母,為此厲爺還特意舉辦了宴會,並且在宴會上高調宣稱:“我夫人不是小結巴,日後若再讓我聽到此類稱呼,莫怪厲某沒提醒過諸位。”這哪裏是宣布,這分明是警戒嘛!看著昔日裏高高在上的某厲爺此刻貼在小姑娘身邊,聽著她的話點頭哈腰時,他們相信了!厲爺居然真的是的妻管嚴!!!明明挨打了卻還笑得跟傻子一樣。.......愛恨糾纏,嗜命囚歡,所幸一切為時未晚。有情之人皆得償所願。【雙潔小甜虐文一枚啦~歡迎觀看。】
60.6萬字8.18 21634 -
完結21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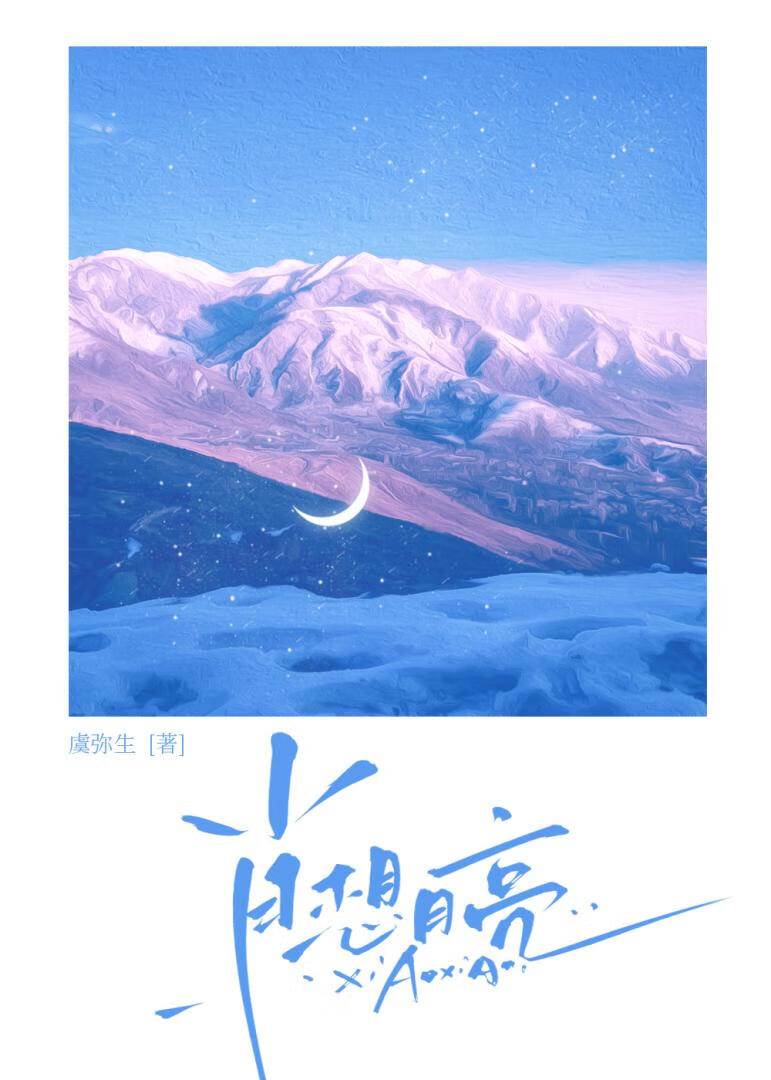
肖想月亮
林應緹第一次見江席月是在養父母的倉庫裏。 少年清俊矜貴,穿着白襯衫,雙手被反捆在身後,額前黑髮微微濡溼。 他看向自己。嗓音清冷,“你是這家的小孩?” 林應緹點頭,“我不能放你走。” 聞言,少年只是笑。 當時年紀尚小的她還看不懂江席月看向自己的的淡漠眼神叫做憐憫。 但是那時的林應緹,沒來由的,討厭那樣的眼神。 —— 被親生父母找回的第九年,林應緹跟隨父母從縣城搬到了大城市,轉學到了國際高中。 也是在這裏,她見到了江席月。 男生臉上含笑,溫柔清俊,穿着白襯衫,代表學生會在主席臺下發言。 林應緹在下面望着他,發現他和小時候一樣,是遙望不可及的存在。 所以林應緹按部就班的上課學習努力考大學。她看着他被學校裏最漂亮的女生追求,看着他被國外名牌大學提前錄取,看着他他無數次和自己擦肩而過。 自始至終林應緹都很清醒,甘願當個沉默的旁觀者。 如果這份喜歡會讓她變得狼狽,那她寧願一輩子埋藏於心。 —— 很多年後的高中同學婚禮上,林應緹和好友坐在臺下,看着江席月作爲伴郎,和當初的校花伴娘站在一起。 好友感慨:“他們還挺般配。” 林應緹看了一會,也贊同點頭:“確實般配。” 婚宴結束,林應緹和江席月在婚禮後臺相遇。 林應緹冷靜輕聲道:“你不要在臺上一直看着我,會被發現的。” 江席月身上帶着淡淡酒氣,眼神卻是清明無比,只見他懶洋洋地將下巴搭在林應緹肩上。 “抱歉老婆,下次注意。”
33萬字8 62 -
完結205 章

東宮福妾(清穿)
程婉蘊996多年,果然猝死。 穿越後好日子沒過幾天,被指爲毓慶宮一名不入流的格格。 程婉蘊:“……” 誰都知道胤礽晚景淒涼。 可如今胤礽還是個剛滿十五歲的少年,清俊明朗、溫潤端方、自矜驕傲。 程婉蘊掰着指頭算了算,距胤礽圈禁而死少說還有20幾年。 那就……先躺會吧。 廢就廢吧,反正她是努力不動了。 圈就圈吧,再哪兒躺不是躺。 別人忙爭寵,冬天穿紗在花園跳舞。 程婉蘊圍爐看雪邊啃噴香烤鴨。 別人忙宮鬥,暗中挑撥引宮中責罰。 程婉蘊養着娃兒不忘擼貓養狗。 別人忙站隊,福晉側福晉分庭抗禮。 程婉蘊嘬着奶茶出牌:“碰!” 她稀裏糊塗躺到康熙四十七年,後知後覺迷惑:怎麼還沒被廢? 胤礽自納了程氏後, 與她同眠,偶爾會做奇怪的夢,次次成真。 後來,他想起來的越來越多。 原來那是他的前世——父子不和、兄弟鬩牆、幼弟夭亡、廢黜幽死。 他憑殘缺記憶,步步爲營,仍走得如履薄冰。 而程氏……沒心沒肺睡得噴香。 胤礽:好氣。 但還是溫柔垂眸,替她掖好被角。 許是長生天知道他前路坎坷,才賜了個小福星給他。 他持劍裹血遍體鱗傷,她是他歸路的桃花源。
105.5萬字8 16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