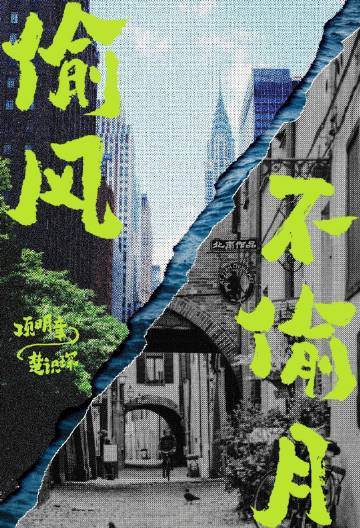《他的白茉莉花》 Chapter53 你要摸摸看嗎
宋茉的手穿進他的指,扣,指尖用力得仿佛要掐進他的。
對著他聲嘶力竭,質問如刀深剖進他的心,心如刀割。
怦怦——怦怦——
男人心髒鼓著,心裏說不上什麽覺,是痛是喜是酸,眼神鷙灼亮,和十指相扣的那隻手使力,將瞬間拉到自己膛前,手臂青筋微微凸起,眼神像要把生吞了。
靜靜抬頭看著他。
通紅的眼眶裏,無聲無息流著淚。
沈斯京垂頭,膛劇烈起伏。
他低聲呢喃的名字,聲音很沙啞,仿佛含著鐵鏽氣,輕聲問:“你有多我?”
像一捧冰雪砸澆到宋茉的天靈蓋,淋得神誌陡然清醒。
瞳孔驟,臉雪白,猛然開被他炙熱抓握的手,推拒他邦邦的肩膀,冷聲提醒道:“你說錯名字了,不是我,是小紅帽。而且也沒有這句臺詞。”
沈斯京盯著,臉微微發沉。
“行了,到這裏就差不多沒了。”
宋茉咬。
平靜低頭收拾臺詞本,將他手上的也收了過來:“跟你對臺詞沒什麽覺,以後不用你了,我還是找唐聞白吧。”
這句話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抬頭看他,眼睛清澈溫,波。
沈斯京正僵在原地看著,表說不清的極為複雜,像在抑什麽,想說什麽,脊背不可抑製地繃,最後隻語焉不詳地沉聲道:“臺詞念得不錯。”
宋茉眨眨眼,低頭。
微不可察地唔了一聲。
“當然,這句話我排練了很久。”
-
淩晨剛過十二點,後半夜飄起細雨,烏雲覆在明月上,遮著深暗的天。
“那麽多年了,你為什麽不我?”
房間,男人大馬金刀地半仰在寬敞遊戲椅上,高大威武,雙手抱著後腦勺,黑眸惺忪困倦,回想著生今天喊的那句話,勾著,眼瞳閃過一瀲灩芒,長眉飛揚。
Advertisement
掏出煙,菱將燃著的煙草霧三兩下吸吐,碾滅進煙灰缸。
然後進浴室裏洗了個澡,換上寬鬆黑和灰運,去到宋茉房間敲兩下門。
人在裏麵,但沒開門。
他頓了頓,低頭撥通的手機,靠著牆慢慢等著。
鈴聲響了好幾分鍾才接通。
兩邊同時默然,男人撓了撓眉心,深吸氣,率先開口。
“在睡覺?”
“沒,弄學校的事。”
“很忙?”
“還可以。”
“要不要吃麵?我下去煮點,一起吃。”
那邊敲擊鍵盤的聲音倏忽停下,宋茉安靜幾秒。
“不用了。”聲線平平,輕呼吸似乎裹挾著細雨,穿過沉鬱深藍的夜,“我今天沒心。”
“那下來喝點酒。”
良久,說:“好。”
宋茉下到來,客廳裏已經烘著熱乎乎的暖氣。
沈斯京坐在餐桌旁,他剛喝一杯酒,口順苦,爽得他嘶聲,穿著件單薄的黑寬鬆,頂著漉漉糟糟的蓬發,兩條長大剌剌敞開,高將他的下半拉得極為修長好看。
比起往常的糙,多了幾分慵懶隨意的氛圍。
看見來了,他下朝對麵位置一抬,那裏已經擺好了一杯紅酒給。
“坐。”
男人嗓音仿佛被煙酒泡過,不鹹不淡的微醺嗓音異常強勢。
宋茉垂眸,坐到他對麵椅子上。
“怎麽突然想喝酒了?”問。
“你剛才不也在房間裏喝嗎?我看了一瓶酒。”他勾著深長的眼神斜向,淡聲說,“喝了酒還要學習,這麽用功。”
宋茉一頓,沒說什麽。
酒量不錯,但今天心事著,狀態不好,一不小心貪杯,又睡不著,隻好用學習麻痹自己。
“給你倒的是紅酒,可以多喝點,度數不高,對好。”他說,“我經常喝。”
Advertisement
宋茉淡淡道:“怪不得你大冬天老是隻穿一件,這麽健康。這是你自己買的吧,看起來也不暖和,劣質,不如了著出去,反正沒差。”
許是喝了酒的緣故,說話比往常的多了些明顯的刺。
沈斯京勾著角,反相譏:“和你那小狗一樣,我挑服眼不行,需要一個審好的媳婦,能幫忙選服。”
這是在商場裏他第一次見唐聞白時,唐聞白朋友對宋茉說的話。
聽出了他在怪氣,宋茉冷斜睨他一眼。
沈斯京愜意起去浴室吹頭發,吹風機轟轟響,腦海三番兩次閃過宋茉那張熏然醉的臉,心裏有點發,頭發吹到三分幹就踢踢踏踏下了樓。
回到餐桌時,那一大瓶紅酒已經了一大半。
他重新坐在宋茉對麵,目掃向。
宋茉纖手握著冰鮮的玻璃酒杯,晃漂亮鮮紅酒,仰頭,慢悠悠啜飲,似天鵝般的脖頸延,仿佛蒙上薄薄嫣,長袖往下墜,出白皙的腕骨,上麵一點點灰印。
沈斯京瞳孔濃黑如墨,盯著泛紅的臉頰,眼睛微微赤紅。
他迅速將酒一飲而盡,掠了眼的手腕,又飛快收回。
“手怎麽了?”
“前陣子不小心被燙傷,已經好了,留了點印。”
沈斯京微微蹙眉。
說完,宋茉忽然抬眼看著他,眸微閃,聲音輕:“你要看嗎?”
男人一頓,抬睫和對視,麵龐沉靜如水。
宋茉將手平放在桌子上。
穿著,袖子長到半遮住的手背,但沒挽上去,仿佛靜待著他的選擇——如果想,就自己開這袖口。
片刻後。
沈斯京結滾一下,出手,極緩、極慢地,稍許試探地,將修長有力的手指輕輕探進白針織的袖口裏——他沒選擇開袖口,而是進去,藏起來。然後,糲指腹順著手背細瘦的青筋,一路至的手腕,停頓,兩人呼吸似乎也在這一刻停滯。
Advertisement
過了一會兒,男人指節微了,他盯著,開始了緩慢的挲、磨纏。
一下一下的,在那點皮上來回輕輕,空氣中晦傳來皮挲的聲音。
輕輕的、窸窣的、抑的。
兩人在昏暗的線裏,默然對視。
沈斯京沉著呼吸,手指繼續慢慢著,力度忽而稍重,宋茉另一隻手撐著下,一言不發靜靜看著他。
同時陷微妙的沉默。
猶如氣泡藏在平靜的海麵下,微微汩汩冒著泡。
氣氛變得緩慢,黏膩。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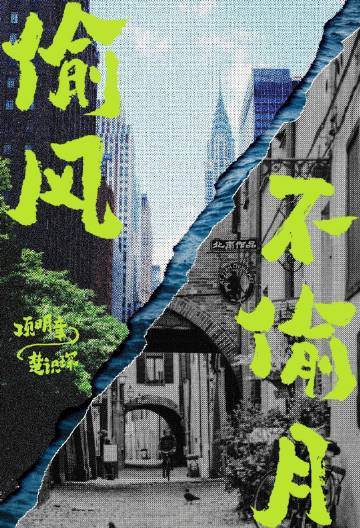
偷風不偷月
穿越(身穿),he,1v11945年春,沈若臻秘密送出最后一批抗幣,關閉復華銀行,卻在進行安全轉移時遭遇海難在徹底失去意識之前,他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后來他聽見有人在身邊說話,貌似念了一對挽聯。沈若臻睜開眼躺在21世紀的高級病房,床邊立著一…
39.3萬字8 6359 -
完結1407 章

嫁給傻王爺后被寵上天
令人聞風喪膽的女軍醫穿越到了段家廢柴二小姐的身上,爹不疼,沒娘愛,被迫嫁給奄奄一息的傻王爺。誰料到傻王爺扮豬吃老虎,到底是誰騙了誰?...
243.7萬字8 16239 -
完結7 章

霸道專寵,葉總裁他又兇又甜
陰差陽錯,她成了總裁的合同替身情人。她給他虛情,他也不介意假意。她以為是義務,卻在偏心專寵下不斷沉淪。她把自己的心捧出來,卻遇上白月光歸國。她經歷了腥風血雨,也明白了如何才能讓愛永恒……合同期滿,葉總裁單膝跪地,對著她送出了求婚戒指,她卻把落魄時受他的恩賜全數歸還。這一次,我想要平等的愛戀!
1.5萬字8 99 -
完結143 章

被我強取豪奪的太子爺回來報仇了
【久別重逢+破鏡重圓+雙初戀+HE+男主一見鐘情】五年前得意洋洋的晃著手中欠條威脅顧修宴和她談戀愛的黎宛星,怎麼也沒想到。 五年后的重逢,兩人的身份會完全顛倒。 家里的公司瀕臨破產,而那個曾因為二十萬欠款被她強取豪奪戀愛一年的窮小子卻搖身一變成了百年豪門顧家的太子爺。他將包養協議甩到了黎宛星面前。 “黎主播,當我的情人,我不是在和你商量。” - 身份顛倒,從債主變成情人的黎宛星內心難過又委屈。 會客室里,外頭是一直黏著顧修宴的女人和傳聞中的聯姻對象。 這人卻將她如小孩一樣抱了起來,躲到了厚厚的窗簾后,按在了墻上。 黎宛星:“你要干嘛!” 顧修宴勾起嘴角,“偷情。” - 顧修宴在金都二代圈子里是出了名的性子冷淡,潔身自好,一心只有工作。可突然有一天像被下了降頭一樣,為了黎宛星公開和顧家兩老作對。 身邊的人好奇的問:“怎麼回事啊?這是舊情復燃了~” 顧修宴淺抿了一口酒,“哪里來的舊情。” - 這麼多年來,一直以為是自己先動心的黎宛星在無意間聽到顧修宴和朋友說。 “我喜歡黎宛星,從她還沒認識我的時候就喜歡她了,是一見鐘情。” 黎宛星一頭霧水。 什麼一見鐘情,當年難道不是她單方面的強取豪奪嗎?
27.3萬字8 14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