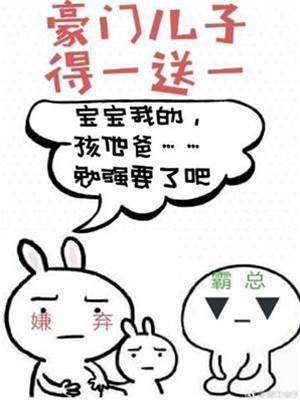《步步為餌》 第026章 暫收鳳冠
“相聚?”將離困地看向白餌,他最親的九哥已死,又如何再聚?
白餌不作聲了,闔上了疲憊的眼眸,很快就睡著了。
將離靜靜看著白餌沉睡的臉龐,一個那麽要強的子,現在看來,竟像個無依無靠的孩子,而往後,該有多個夜涼如水的日子,要這般提心吊膽地睡著。
夜寒霜重,月華如練,死牢一隅,兩道重疊的影子拉得格外長。
二日,紫竹林外,浮破寺。
午後的直直地照在浮破寺的窗戶上,窗戶上的玻璃都破了,一陣清風吹來,窗欞上爬滿的一層厚厚的蜘蛛網輕輕飄搖著,網上的蜘蛛似乎到了驚嚇,飛快地沿著窗欞,一直爬往牆角,牆上的跡猶在。
那是十多個浮僧的鮮。漠滄風人屠城,殘暴無比,這些浮僧自然難以幸免,牆上留下的跡,都是他們死死守護浮的象征,每一寸痕,都代表著忠誠、本心。
寺中大堂正中,供著一尊佛像,佛像左右各有兩隻高高的燈盞,火隨風浮,照得佛像後那牆畫壁熠熠生,畫壁中的天宮愈發靈生姿。
佛像穿著一破了幾個大的骯髒袈裟,佛像的手指頭也掉了好幾,一切似乎麵目全非,但佛像上那對慈善的眼睛卻從未變過,他認真地注視著下正在虔誠焚香的男子,角流出的,始終看不出,是喜是憂。神仙的心思,凡人莫猜。
佛像下的人是黎桑非靖,他左右擺滅了燃起的火焰,麵朝佛像,三支香與額相齊,拱手作揖。每一個作都認真到了極致。隨後用右手攬著袖子,左手將三炷香地直直的。每步流程,每個細節似乎都十分嫻。
“皇兄!都什麽時候了,你還有心思在這裏燒香拜佛?”黎桑鈺掩上門,一步步朝佛像下走去,手裏的竹籃重重落在香案上。竹籃裏有一些食。
Advertisement
黎桑非靖跪在團上,雙目閉,並沒有做聲,而是認真叩拜。禮畢之後,他才小心起,攬著袖子,不不慢地從香案上取了三支神香,轉朝向黎桑鈺:“祭拜一下先皇先後吧!”沉重的兩道眉了下去,神香遞到了手邊。
“父皇沒有死,我不拜!”黎桑鈺長袖一揮,三支神香轉瞬撲落塵埃。一夜之間,父皇變先皇?嗬,嗬嗬!要接這個事實,難如登天!
腮幫登時僵,黎桑非靖抬手而去,一記耳狠狠落在黎桑鈺的臉上:“先皇的頭顱正高高懸掛在聚龍城的城門之上,骨未寒!你為黎桑公主,自欺欺人,屢屢冒犯,這是對先皇的大不敬!”
打散的青淩地遮住了黎桑鈺半張黯然失的臉,半晌才抬眸:“你以為你有多明白?你以為你有多敬重?大廈將傾,國將不國,可你還不是照樣在這裏做著一些既可笑又毫無用的事嗎?”
隻不過是不想接這個事實罷了,他卻一點幻想的東西都不給留,憑什麽!
“先皇逝世,你以為我不難過嗎?大廈將傾,你以為我不恨嗎?我為了召集朝中權貴,險些落風人之手,如今還是負重傷!”黎桑非靖暗淡的眸子湊得更近,“而你呢?你又做了什麽?國難當頭,朝中多大臣匍匐風人腳下,搖尾乞憐,忠心事主、願意追隨的人本沒有幾個!你倒好,因為自己一時的任,重傷將離在前,走將離在後,如今這局麵豈是你想掌控就能掌控的嗎?”
聽到悉的字眼,黎桑鈺就不滿了:“那是他咎由自取!”將離隻不過是一個替自己賣命的殺手,皇兄竟拿他來,可笑!
Advertisement
“刑場當天,多毅然反抗之士落漠滄皇的手中?這些你難道沒看見嗎?若不是將離那夜提醒並誓死阻攔,恐怕你早已主送風人的刀下,了風人的刀下鬼!”黎桑非靖一語道破,猶如當頭棒喝。
聞言,黎桑鈺下意識低下頭,好像意識到了什麽。誓死阻攔?將離挨數刀竟是為了泄心頭之恨?如今想起,若非是將離的緣故,以的子,估計那夜早就衝去死牢,拯救父皇。這麽說來,那飛出的三銀針,豈不是......但,但要向一個手下認錯,那是萬萬不能,這可不符的份。
黎桑鈺忽然抬起頭,怯弱卻不失自尊地回道:“將離他隻是一個聽命於我們的殺手,皇兄你何必為一個殺手說話!”
“將離來自神將司,他的謀略與武功深不可測,眼下,將離亦是我們唯一可信之人,日後,你對他的態度,還是放尊重些好!”落魄至此,還是這般高傲,究竟何時才能正真長大!黎桑非靖看著鈺,眼裏充斥著擔心。
天大地大,冠最大,可不能低頭,黎桑鈺強:“皇兄!”
“好了,休要多言,為今之計,唯有速速找到將離,再進行我們下一步的計劃。那夜他挨了數刀,又中銀針,估計這會很可能已經落風人手中,你速速去把他找回來!”黎桑非靖筆直立著,兩手落在後,語氣變得嚴肅。
堂堂黎桑公主去尋一個下人?天下之大稽!這會兒,自是不願意,索背過去,喃喃道:“憑什麽我去?我才不去!”
“事因你而起,你不去誰去?”黎桑非靖無奈呼出一口冷氣,繼續道,“莫非,你是想讓我負著傷去?”
Advertisement
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了,黎桑鈺退無可退,亦無辯駁。今天這事本就是做得不對,如今將離的事也被搬出來了,總之都是理虧,再胡鬧下去,就真的有失理智了......不過,眼下的局勢看得清楚,皇兄傷還沒好,而時間也越來越,很多事,確實不能再耽擱了。
黎桑非靖見不做聲了,便提起香案上的籃子,輕輕轉佛像旁的燈盞,佛像後的畫壁隨之分兩半,緩緩拉開,裏麵是一個被黑暗欺的室。
“切記自己的言行!早去早回!”黎桑非靖提醒完,便了室。
看見室的門緩緩闔上,黎桑鈺也走了,不過,剛才那句話,由於窗外的風太大,好像沒聽見。
囚奴工地。
寒冬料峭,燦然。偌大的工地上空萬裏無雲,偶爾有飛鳥劃過。
隨著一陣指揮聲,一厚重的木梁懸空而起,無數塵埃紛紛墜下,木梁準地落在兩拔地而起的柱子上,六七個囚奴轉眼像了氣的紙燈籠,幹癟無力,這一,好像用完了他們畢生的力氣。
揮舞著長鞭的風人時不時飄在工地上,所到之,必傳來此起彼伏的鞭子聲。
鞭子聲得越近,囚奴們幹活發出的聲音就越大,這邊呼喚同伴,那邊賣命嘶喊,各種聲音抑揚頓挫。
“王福,咱們都幹了這麽久了,修建府邸這麽大的工程量,到底是為誰修的啊?”白餌掉額頭上的大汗,回頭向王福。
王福猛地從地上抱起一袋沉甸甸的沙袋,瞇著眼,牙咬得的,憋出幾個字:“你若問我,我且問誰?”僵地步子搖了片刻,沙袋重重落到推車上,這才如釋重負,“風人要幹什麽,與我們有何幹係?咱們隻管好好幹好自己的活,有口熱粥吃就行咯!”
Advertisement
“我看你就是頭豬,除了吃,你還能幹啥!”實在是無語了,白餌索捧起旁邊的大籠子,恨不得往他頭上蓋。
將離懷抱雙手,閑坐一旁,揶揄:“這籠子裝他合適的!”
此話一出,兩個人不彎腰捧腹,不能自已。
王福這就來氣了,白餌昨日把他耍得團團轉就罷了,今日還來取笑,更過分的是,將離還同他一起戲謔,真是世態炎涼。
“將離,你可別忘了昨天是誰給你找的藥,誰給你的藥,今天,你們福哥我不伺候了!哼!”憤憤不已的王福一把推開眼前的糟心籠子,徑直地走開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道不同,不相為謀,哼!
看著王福失意離開的樣子,白餌急了,他不藥了,那誰!?索追了上去。
看著漸漸消失的白餌,將離剛想追上去攔,一隻手卻被人反手抓住。
“將離,快跟我走!”悉的聲音傳來。
將離回頭,麵無表地看著突然出現的黎桑鈺:“你來作甚?”其實,他也不過是明知故問,和黎桑太子的境況他豈會不知?他們始終是要依靠他的,而唯一讓他到好奇的是,哪來的勇氣,肯紆尊降貴來這裏找他?
“本公主是來救你的,快跟本公主走!”黎桑鈺看著他這副表,一下子就不爽了,花了那麽大的力氣,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他卻仍舊擺出一副自視甚高的樣子,哪怕連一個意外的神都沒有嗎?
“你還是快走吧,這裏不安全,到時候,還指不定誰救誰。”將離直了腰板,兩手於前,微風時不時揚起他額前一縷發,整個人顯得氣神十足,完全看不出過什麽傷。
“你!”你簡直膽大包天,竟敢以下犯上,今天定要你嚐嚐本公主的厲害!黎桑鈺把邊的話活生生給憋了回去,自知這裏絕對不是吵架的地方,若是引來風人,的份因此曝,豈不是得不償失。於是,話鋒一轉:“你走不走!”
“恕難從命。”將離淡定回道,這裏終究還是風人的地方,黎桑鈺掀不起多大的風浪,何況,現在絕不是離開的時候。
看著黎桑鈺怒的神,恐怕又要惹出事端,罷了,不與爭執,先走為妙。思及此,將離準備轉就走。
看著將離漠視的眸子,黎桑鈺忍無可忍,猛地出劍鞘中的長劍,決意要往將離上劈去。
“將離小心!”
遠,白餌驚慌的聲音傳來。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1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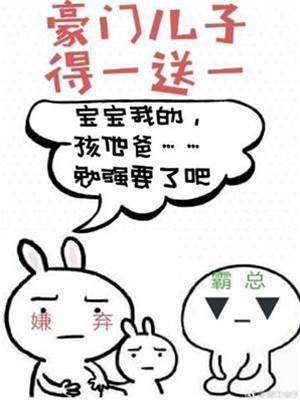
豪門兒子得一送一
別人去當后媽,要麼是因為對方的條件,要麼是因為合適,要麼是因為愛情。 而她卻是為了別人家的孩子。 小朋友睜著一雙黑溜溜的大眼,含著淚泡要哭不哭的看著林綰,讓她一顆心軟得啊,別說去當后媽了,就算是要星星要月亮,她也能爬著梯子登上天摘下來給他。 至于附贈的老男人,她勉為其難收了吧。 被附贈的三十二歲老男人: ▼_▼ ☆閱讀指南☆ 1.女主軟軟軟甜甜甜; 2.男主兒砸非親生; 3.大家都是可愛的小天使,要和諧討論和諧看文喲!
31.8萬字8.33 47271 -
完結72 章

心機女的春天
韓熙靠著一張得天獨厚的漂亮臉蛋,追求者從沒斷過。 她一邊對周圍的示好反應平淡,一邊在寡淡垂眸間細心挑選下一個相處對象。 精挑細選,選中了紀延聲。 —— 韓熙將懷孕報告單遞到駕駛座,意料之中見到紀延聲臉色驟變。她聽見他用浸滿冰渣的聲音問她:“你設計我?” 她答非所問:“你是孩子父親。” 紀延聲盯著她的側臉,半晌,嗤笑一聲。 “……你別后悔。” 靠著一紙懷孕報告單,韓熙如愿以償嫁給了紀延聲。 男人道一句:紀公子艷福不淺。 女人道一句:心機女臭不要臉。 可進了婚姻這座墳墓,里面究竟是酸是甜,外人又如何知曉呢?不過是冷暖自知罷了。 食用指南: 1.先婚后愛,本質甜文。 2.潔黨勿入! 3.女主有心機,但不是金手指大開的心機。
22.8萬字8 6822 -
完結857 章

重生九零肥妻歸來
中醫傳承者江楠,被人設計陷害入獄,臨死前她才得知,自己在襁褓里就被人貍貓換太子。重生新婚夜,她選擇留在毀容丈夫身邊,憑借絕妙醫術,還他一張英俊臉,夫妻攜手弘揚中醫,順便虐渣撕蓮花,奪回屬于自己的人生。
159.8萬字8 97590 -
完結523 章

重生蜜戀:偏執九爺他淪陷了
前世,云漫夏豬油蒙心,錯信渣男賤女,害得寵她愛她之人,車禍慘死!一世重來,她擦亮雙眼,重啟智商,嫁進白家,乖乖成了九爺第四任嬌妻!上輩子憋屈,這輩子逆襲!有人罵她廢物,醫學泰斗為她瑞殺送水,唯命是從,有人嘲她不如繼姐:頂級大佬哭著跪著求她叫哥!更有隱世豪門少夫人頭街為她撐腰!“你只管在外面放建,老公為你保駕護航!”
88.6萬字8.18 140070 -
完結167 章

聖佛子人設崩了,原是寵妻狂魔
【強製愛 男主偏執 雙潔】南姿去求靳嶼川那天,下著滂沱大雨。她渾身濕透如喪家犬,他居高臨下吩咐,“去洗幹淨,在床上等我。”兩人一睡便是兩年,直至南姿畢業,“靳先生,契約已到期。”然後,她瀟灑地轉身回國。再重逢,靳嶼川成為她未婚夫的小舅。有著清冷聖佛子美譽的靳嶼川,急得跌落神壇變成偏執的惡魔。他逼迫南姿分手,不擇手段娶她為妻。人人都說南姿配不上靳嶼川。隻有靳嶼川知道,他對南姿一眼入魔,為捕獲她設計一個又一個圈套......
29.1萬字8.18 45878 -
完結150 章

垂涎你許久
【破鏡重圓+強取豪奪+雙潔1v1】向枳初見宋煜北那天,是在迎新晚會上。從那以後她的眼睛就再沒從宋煜北臉上挪開過。可宋煜北性子桀驁,從不拿正眼瞧她。某次好友打趣他:“最近藝術係係花在追你?”宋煜北淡漠掀眸:“那是誰?不認識。”後來,一個大雨磅礴的夜晚。宋煜北不顧渾身濕透,掐著向枳的手腕不肯放她走,“能不能不分手?”向枳撥弄著自己的長發,“我玩夠了,不想在你身上浪費時間了。”……四年後相遇。宋煜北已是西京神秘低調的商業巨擘。他在她最窮困潦倒時出現,上位者蔑視又輕佻的俯視她,“賣什麽價?”向枳躲他。他卻步步緊逼。無人的夜裏,宋煜北將她堵在床角:“說你後悔分手!”“說你分手後的每個日夜都在想我!”“說你還愛我……”四年後的宋煜北瘋批難纏,她嚇到想要跑路。逃跑時卻被宋煜北抓回。去民政局的路上,她被他紅著眼禁錮在懷裏:“再跑,打斷你的腿!”
25.4萬字8 850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