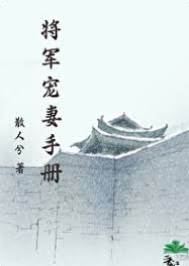《燕宮殺,公子他日日嬌寵》 第392章 長歌
也是,魏國是橫亙在與那人之間最敏的話題,每當提起魏國與魏公子來,那人總是疑神疑鬼的。
小氣鬼,杯弓蛇影的,是一點兒信任都沒有。
小七直起來,繼而傾上前,捧住了那人的臉,一雙桃花眸子注視著那人的目,問道,“燕國兵馬充足,糧草充沛,公子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公子說,是與不是?”
捧住了那人的臉,便似金烏一掛,頓時那人疑慮頓消。
那人笑道,“商。”
那倒也是,你可還記得,從前從前勞作一月才能賺來一枚刀幣,如今一條魚一顆蛋竟也要賣上一刀幣甚至十刀百刀,還想著多多益善,果真是有些黑心了。
不止如此,還打起了與魏國進行糧草貿易的主意,要在魏燕之間開辟一條通商之道,兩國互利,更利燕國。
的確,的確商無疑。
不止如此,還打起了公子的主意,“公子應是不應?”
那人抬手將的荑覆在掌心,笑道,“應了。”
“那公子借不借地?”
你瞧那人心不在焉的,“我都是你的,談什麼‘借’與‘不借’,生分。”
小七不肯,素指在那刀削斧鑿般的臉上輕敲幾下,“公子好好說話,到底借是不借?”
那人眸溫潤,一只手不安分地在腰間游移,“借你。”
小七乘勝追擊,又追問起來,“我還要幾百個庶人墾田,公子肯不肯幫?”
那人不好好說話,修長的指似耙子一般,輕易地便扣住了的,眸一深,看起來心神已,好似正事兒沒有說完,就要當場要了似的。
Advertisement
小七一掌拍掉了那人的爪子,“公子肯不肯幫?”
那人只是笑,目就落在一張一合的瓣上不肯挪開,眸濃得化不開,“幫你。”
言罷上一熱,那手又覆了上來,左右拿起來。
br> 小七臉一紅,又去敲他,凝著眉頭鄭重其事的,愈發顯得形態可,“但我也不能白忙,蘭臺賣出去的每一條魚、每一只鴨、每一匹布,我都與公子一九分,公子許是不許?”
一九分是多錢,假使賣了一千,便能分得一百。假使賣了一萬,便能分一千。假使能賣十萬萬,便能分一萬萬。
那人挑眉笑,“你要那麼多錢干什麼?”
小七坦言,“用來付公子的租金,自己也要留下安立命的本錢。”
你想,從前為了賺五百刀幣,費了多腦筋和工夫呀,不就得看人臉,還得守夜呀,起舞呀,人家一不高興,都得給沒收了。
還有先前在薊城大營曾許諾給的封地,京畿一帶那可是極好的地段兒,對不對?
說得跟真的一樣,但何時可去過那片封地,何時可收過那片封地的租金,沒有,沒有,連個鬼影子都沒有。
遑說沒有租金,單說失憶之后,就因了和大表哥的事,不是也被鄭寺人趕出茶室,似個婢子一樣立在門外去侍奉起那蘭臺的主人了嗎?
可見是唯有自己手,才能足食,單靠旁人是絕對不行的。
那人怔了片刻,若有所思的,人也安分了不,“你要多我給你多,什麼都是你的,你何必留什麼本錢?”
小七侃然正,一字一板道,“我不想靠公子活著,也不要公子的錢,我想要什麼,自己去掙。”
Advertisement
公子的永遠是公子的,公子的東西他想收就能收走。但自己的東西,永遠都是自己的。
自己掙錢自己花,把腰包
賺得鼓鼓的,搖桿直了,人才有底氣。
這才是正道。
那人方才微的眼神看起來已經神思清明,眸中卻多了幾分黯然失落,也不知到底在琢磨些什麼。
小七繼續道,“將來我還想再開一家酒肆,只賣桃花酒,也只賣黃河魚。”
將來載酒園林,與舊好新知,做些茶甘飯,在燕國也能活自己想要的模樣。(載酒園林,尋花巷陌,當日何曾輕負春,出自陸游《沁園春·孤鶴歸飛》)
為公子謀兵馬糧草,是告訴公子,小七與公子共進退。
為自己謀安立命的本錢,是告訴公子,小七愿留在蘭臺,也愿在薊城扎。
見那人若有所思,小七問他,“公子不愿意?”
那人回神,好一會兒贊許起來,“小七,你真了不起。”
并沒有什麼了不起的,與公子原本是兩條路上的人,公子是不必勞作便什麼都有的人,卻是除了勞作什麼都不會有的人。
公子如今重,將來呢?
將來年老而衰,衰必弛,又心堅,不肯低頭服的子,因而極不討人喜歡,就這麼一個人在燕國似無的浮萍般,怎麼能不為將來思慮呢?
那人以額相抵,低低道,“都依你。”
好呀,真好。
小七心里歡喜,勾住那人的脖頸,也不需說什麼客氣的話,彼此心里在想什麼,彼此大約也都懂得。
因而當那人說,“小七,去看看外面吧。”
Advertisement
窗外的日愈發地濃,陶罐里的桃花全都綻開,把這四面風的新宅盈出了滿滿的桃香。
盈滿了桃香,盈滿了日,也盈滿了盼頭,盈滿了。
小七沒有一刻覺得燕國是這樣的好,也沒
有一刻覺得蘭臺是這樣的好。
因而欣然應了,那人攜的手起了,踩著與桃林老宅一樣的木地板,一步一步地往外走去。
你瞧,他們穿著一樣的袍。
白的長袍,于袖口繡著幾朵銀邊的山桃,在他們腳畔出一圈圈好看的漣漪。
你不知道那人為了小七到底費了多心思。
的荑被那人的手心攥得暖暖的,他說,“我給你想了一個名字。”
小七不抬頭問道,“公子想的什麼名字?”
那人面溫潤,他含笑說道,“長歌。”
春祺夏安,秋綏冬寧,長歌有和,獨行有燈。
猶記得從前有人問,“什麼名字?”
說小七。
小七呀,小七原也不算是什麼名字。
那人笑了一聲,“真是賤名。”
低垂著頭解釋,“父親說,賤名好養。公子覺得不好聽,便為小七賜個名字罷。”
那時的小七多希公子能賜一個名字吶,不是定要什麼名字不可,但他若愿賜名,便也能多活一陣子。
可那時的公子嗤了一聲,他不肯賜,他說,“不過是個俘虜,早晚要埋進坑里,何必浪費心力。”
那時的公子許瞻金尊玉貴,干干凈凈。
他只是靠在那里,并沒有說一句話,那通天潢貴胄的氣度卻人無躲藏。
那時的魏俘小七蓬頭垢面,凍得鼻尖通紅,糙的魏軍袍子被馬鞭得出了里絮著的棉花,靴底沾染的雪泥在爐子烘烤下化出一灘黑水。
而今金尊玉貴的公子與那個蓬頭垢面的小七擁在一起,金尊玉貴給蓬頭垢面起了好聽的名字,也神肅然地稱許一句,“小七,你真了不起。”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455 章

神醫王妃超難寵
她是古醫世家嫡系傳人,穿越成了他的沖喜王妃,盡心盡力救了他的命后,他心中的白蓮花出現,直接遞給她一封和離書。古代的棄婦不好當,但她從此腰桿挺直了,也不抱狗男人大腿了,直接走上了人生巔峰。皇帝跑來獻殷勤,世子爺十六抬大轎娶她進門,富商抱金山銀山送給她……某日,他出現在她面前,冷著臉:“知道錯了嗎?知道錯了,就……”回來吧。她笑著道:“下個月初八,我成親,王爺來喝杯喜酒吧,我給孩子找了位有錢的后爹。”
270萬字8.33 353404 -
完結1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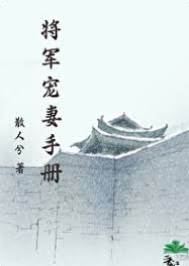
將軍寵妻手冊
雲府長女玉貌清姿,嬌美動人,春宴上一曲陽春白雪豔驚四座,名動京城。及笄之年,上門求娶的踏破了門檻。 可惜雲父眼高,通通婉拒。 衆人皆好奇究竟誰才能娶到這個玉人。 後來陽州大勝,洛家軍凱旋迴京那日,一道賜婚聖旨敲開雲府大門。 貌美如花的嬌娘子竟是要配傳聞中無心無情、滿手血污的冷面戰神。 全京譁然。 “洛少將軍雖戰無不勝,可不解風情,還常年征戰不歸家,嫁過去定是要守活寡。” “聽聞少將軍生得虎背熊腰異常兇狠,啼哭小兒見了都當場變乖,雲姑娘這般柔弱只怕是……嘖嘖。” “呵,再美有何用,嫁得不還是不如我們好。” “蹉跎一年,這京城第一美人的位子怕是就要換人了。” 雲父也拍腿懊悔不已。 若知如此,他就不該捨不得,早早應了章國公家的提親,哪至於讓愛女淪落至此。 盛和七年,京城裏有人失意,有人唏噓,還有人幸災樂禍等着看好戲。 直至翌年花燈節。 衆人再見那位小娘子,卻不是預料中的清瘦哀苦模樣。雖已爲人婦,卻半分美貌不減,妙姿豐腴,眉目如畫,像謫仙般美得脫俗,細看還多了些韻味。 再瞧那守在她身旁寸步不離的俊美年輕公子。 雖眉眼含霜,冷面不近人情,可處處將人護得仔細。怕她摔着,怕她碰着,又怕她無聊乏悶,惹得周旁陣陣豔羨。 衆人正問那公子是何人,只聽得美婦人低眉垂眼嬌嬌喊了聲:“夫君。”
17萬字8.33 56909 -
完結504 章

侯府忘恩義?攝政王撐腰,不原諒
駱寧替太后擋刀重傷,換取家族爵位。她南下養病三年,回來后卻發現,表妹占據了她的院子。 表妹也取代了她的地位。駱寧的父母、兄長疼她、祖母賞識她;就連駱寧的竹馬,也暗慕她,說她處處比駱寧優秀。 駱寧大鬧,他們聯手害死了她。 做鬼十八年,看到了他們的下場,她重生了。 她又活了。 這次,她想要活得痛快。 ——*——*—— 駱寧重生后為復仇,找攝政王做靠山。 “明面上你是雍王妃,實際上你是本王之奴。他日,助你假死脫身,更名換姓。封你為郡主,有封地、俸祿,同郡王。” 她同意了。 她鎮得住側妃、斗得贏野心勃勃的門閥、哄得了太后。 幾年后,攝政王成了新主。 跋扈狠戾的年輕帝王,用很縹緲的聲音問她:“郡主印換皇后金印,可愿意?” 她忠誠聽話,頭一回忤逆他:“不愿!”
90.4萬字8.33 13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