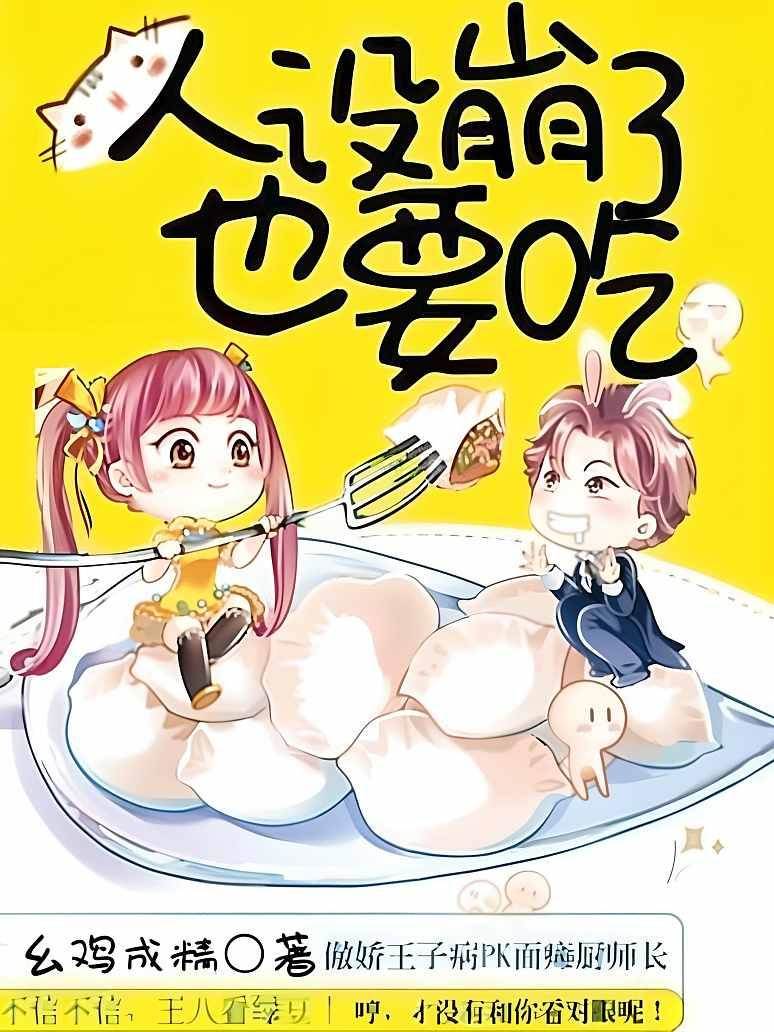《誘吻月亮》 第150章 容遇番外3
十歲的年齡差是個巨大的鴻,容遇每次見都抑著愫,在過界的邊緣小心試探。
開學後,薑有容把重心放在學業上,容遇的新電影在黎拍攝,兩個人偶爾微信聯係。
直到忽然有一天,薑有容發微信問他:【電影什麽時候殺青?】
容遇:【大概四月初。】
薑有容:【一點。】
容遇:【二號,殺青回國,正好清明祭祖。】
薑有容沒回複,容遇便接著問:【怎麽?想來探班?】
薑有容秒回:【答對,畢竟當初電影選角我也小小地參與了一下,去給男主角送一束花說句殺青快樂也是理所當然嘛。】
要來,容遇很高興。
可要來給男主角送花,容遇很不樂意。
糾結了一會兒,容遇無奈一笑。
算了,能來就好。
容遇:【到時候把航班號發我。】
-
殺青那天,薑有容飛機延誤,沒趕上劇組的殺青儀式,容遇派去的車把薑有容接回來的時候,劇組演員已經差不多走完了,隻剩下導演組的部分工作人員。
編劇見著一水靈靈的大姑娘手捧鮮花從車裏下來時,打趣一聲:“呦,誰家朋友來了。”
容遇抬眸去,遙遙與相。
“容容。”容遇起相迎,腦子裏那點衝差點驅使他把眼前這個人抱進懷裏。
薑有容鬱悶,幹地笑了一聲:“本來算好時間了的,沒想到飛機會晚點幾個小時。”
“沒關係。”容遇低頭,笑著了沾上雨水的頭發。
黎今天下小雨,風裏夾雜著一春天的味道。
“送你,殺青快樂。”薑有容還背著包,懷裏抱著一大束人魚姬花束,容遇高他許多,仰著頭朝他遞出這束花時眼神真誠,無形中勾人心魄。
這花是來劇組這邊時在路邊的一個小花店買的。
Advertisement
容遇接過花,揶揄一聲:“改送我的?還是專門送我的?”
薑有容抿著笑意,不再逗他:“廢話,我專門請一天假過來祝賀你殺青快樂,不送你送誰?容叔叔你怎麽這麽好騙,我又不你電影的男主角,怎麽可能專門來看他。”
容遇眉目舒展,滿臉春風得意。
因為一束花,更因為。
人魚姬是玫瑰,男之間不輕易送玫瑰,更何況,人魚姬適合人之間相互贈送,花語是至死不渝的。
這姑娘,怕是不知道其中的含義。
“就請了一天假?”容遇微微一蹙眉。
薑有容抓著背包帶子,解釋道:“我後麵兩天沒課,又正好趕上清明放假,喜提一個小長假。”
容遇手自然地把背包摘下來拎在手裏,帶著往裏走:“先坐著等我十分鍾,一會兒帶你去吃飯。”
薑有容乖巧點頭。
編劇旁觀了一會兒,小聲跟容遇流:“敢是你小子的朋友啊!”
容遇噙著笑意,低聲道:“還不是。”
編劇:“嘖,都抱著花來找你了,還不舍得捅破這層窗戶紙?”
容遇一怔。
是啊,如果在眼裏他不特殊不重要的話,又怎會特意請假過來。
這不是城市與城市之間的距離,這是越一個國家的距離。
八千多公裏,飛行近十個小時。
容遇微微失神,在心裏預謀著什麽。
薑有容跟容遇吃了飯之後就犯困,在回酒店的路上就已經昏昏睡了,外邊的雨越下越大,薑有容聽著雨聲逐漸沒了意識,就這麽睡了過去。
睡夢中似乎能到有人抱著自己,囈語一聲:“容叔叔。”
容遇腳步倏然停止,不可置信地看著正往自己口上蹭的小姑娘。
在喊,自己的名字?
把帶回套房,容遇抱著進了主臥,小心翼翼將放上床的時候,正想要起,卻被這力氣大如牛的姑娘鎖著脖頸狠狠往下一扯。
Advertisement
他整張臉在上。
“容容,鬆手。”容遇呼吸微沉,結不自覺滾著。
他本就有所圖謀,如今這波作,更是讓他方寸大。
薑有容沒鬆開,反而抱得越發的,像是將他當了陪睡的玩偶,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容遇才抓住機會解自己,著氣直直盯著睡一頭豬的薑有容。
“薑有容,你撥人的方式,了不得啊。”容遇給蓋好被子,坐在床邊又看了許久。
不經意間的撥,最為致命。
更致命的是,這小姑娘不自知。
-
清明過後,容遇不知道從哪裏淘來的一個玉雕件當做禮送給薑有容。
就喜歡這種小件,收到禮當天不釋手地捧著把玩,當著容遇的麵拍了照片:“曬個朋友圈嘿嘿嘿。”
容遇手指一頓,肅聲道:“薑容容,你知道你朋友圈屏蔽了你帥氣的偶像叔叔麽?”
薑有容睜大了眼睛:“……”
糟糕,忘了這茬了。
“沒關係,給你一次機會解釋。”容遇挑眉,手背在沙發後枕著後腦勺,表揶揄。
薑有容輕咳:“就……主要是……”
支支吾吾半天,僵地扯了扯:“我微信通訊錄有好幾個標簽,沒想好把你放進哪個,就隻好暫時屏蔽你,你等著,我馬上給你放出來!”
喜歡發朋友圈,但幾乎每條朋友圈都會屏蔽不同的分類標簽。
比如發追星這一類朋友圈會屏蔽長輩,發家庭大合照時會屏蔽同學和網友。
雖然喊容遇叔叔,但實際又沒拿他當長輩。
他也不是同學和網友。
想把他放進好朋友的標簽,又怕自己哪天在朋友圈發瘋被他看見。
糾結來糾結去,一個衝就設置了僅聊天的朋友權限。
設置之後就徹底把這事兒忘得一幹二淨了,直到現在容遇提起。
Advertisement
容遇角微,嘖了一聲:“所以你現在打算把我放在哪個分類標簽?”
薑有容嘟噥一聲:“好朋友唄。”
容遇失笑一聲,湊過去看作。
標簽分類得很明細,其中有一個分組是家人,後麵括號有一個數字五,想來是以南棲月為首的同齡家人。
“陸北庭在哪個分組?”容遇問。
“家人啊。”薑有容白了他一眼,“他可是我姐夫。”
“那你哥呢?”容遇繼續問。
薑有容輕咳:“他這人管我太多了,丟長輩那一組去了。”
容遇撲哧笑出聲,沒忍住了臉上的。
“你怎麽老我!”薑有容嗔了一聲,耳朵微微發熱。
容遇沒說話,他在盤算著,要怎麽才能夠被移到家人這一標簽裏。
“不自。”容遇口而出。
空氣似乎凝固了幾秒鍾,薑有容眼神躲避了一下。GgDown8
容遇捕捉到這一秒,直白地問道:“薑有容,你跟你那個十八歲小學弟相親對象,還有聯係麽?”
“沒有啊。”薑有容不明所以,好端端怎麽提起這茬。
“你爺爺,還給你介紹世家公子哥麽?”他心跳得微快。
“我最近不追著秦羽跑了,他也就打消念頭了。”
所以這事兒解決之後也不需要岑馳來做幌子了,之後的聯係便逐漸沒了。
容遇微微勾:“你不是喜歡追星麽,不追著秦羽跑了,那你追誰?”
“你啊!”薑有容口而出。
說完自己都愣了愣。
“我……我的意思是,我之前說過的嘛,你唱歌好聽,我……”有些語無倫次,手指下意識地拽著角。
“容容。”他結微滾。
“啊?”薑有容看過去。
“我想確認一件事。”他微微屏息著。
這段時間以來,他不是沒有察覺,他們兩個人之間的關係潛移默化地發生了許多變化。
Advertisement
這姑娘其實聰明得很,或許沒有自己想象的這麽天真。
可能,察覺了他的心意。
又或者,對他的心意,跟他一樣。
薑有容:“嗯?”
“過來點。”他微微沉聲,看著的眼神是無盡的和。
薑有容的食指暗暗掐了掐大拇指,慢吞吞朝他挪去,呼吸不自覺地放輕。
“抬頭。”容遇目閃爍,愫外泄。
薑有容照做,忽而目相對,微微愣神,再想退後逃開的時候,那帶著木質冷香的氣息了下來,一雙薄在的角,輕輕一啄,隨而了。
忘了做反應,大腦宕機,整個人呆住了。
容遇氣息不穩,心跳如鼓,想要確認的事已經確認完畢,撲麵而來的是令人不已的欣喜與狂歡,他薄微,忽然抬手上的臉頰,張含住的瓣,逐漸深。
舌尖被卷走那一刻,薑有容倏然回神,驚慌失措地將他推開,捂住朝他瞪眼:“你……你變態!你舌頭……”
容遇微微,撲哧笑出聲,手將拉近自己懷裏抱著,慢慢平複自己的呼吸。
薑有容咬著沒敢。
沒想明白,好好的,事怎麽就發展這樣了。
“容容,你喜歡我。”容遇沉著聲,語氣帶著十足的篤定。
不等薑有容答話,他低頭注視的眼睛,深繾綣地抵著額頭:“我喜歡你,喜歡好長一段時間了,每天都在暗你。”
「失策,後麵還有一章,晚點發。」
。您提供大神汀獻的吻月亮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007 章
渣總追妻火葬場
本書停更,請大家在站內搜索《重生后,渣總追妻火葬場》觀看全本小說~ 關於渣總追妻火葬場: 她,放棄了一切,隻為了愛他,但在他的眼中,她卻是一個心機深沉的惡毒女人,為了能夠嫁給他,不惜逼走他的愛人……直到她愛得累了,終於決定離開他了,他卻才幡然悔悟……
184.4萬字8.18 113934 -
完結517 章

婚不設防:帝少枕上寵
一紙成婚卻是噩夢的開始,他不僅把女朋友的死算在她的身上,還禁錮她的人生自由。本以為會日久生情,她懷了他的孩子,原以為他會給她一個家,卻沒想到那個女人出現后,一切都變了。靳墨琛,如果你愛的人只是她,請你放過我!…
53.2萬字8 41211 -
完結560 章

離婚后,前夫夜夜跪求我復合(姜暖席南嶼)
【雙潔+1V1+專情男主追妻火葬場】男人看著離婚協議書:“贍養費,你要多少?”“我要你有多遠滾多遠!”結果冷靜期還沒過,男人就慫了。“老婆,我們不離婚好不好?”“我哪里做的不好,我改。”姜暖只留給他一個妖嬈明媚的背影,姐姐獨自美麗。領了離婚證后,席南嶼覺得他老婆越過越滋潤,越來越漂亮,氣色紅潤萬人迷,桃花朵朵開不敗。他急了,連夜發帖:前妻太受歡迎了怎麼辦?
94.9萬字8.08 87319 -
連載551 章

傅律師,太太說她不回頭了
【先虐后爽】協議結婚五年,即使得知傅斯言在外養了個嬌俏情人,沈輕紓也依舊選擇隱忍。 直到她發現,視如己出的兒子是傅斯言與情人所生。 她才知道,原來這場婚姻從開始就是一場騙局。 情人以正室自居,帶著傅斯言擬定的離婚協議找上門。 那天,沈輕紓查出懷孕。 男人臟了,那就不要了,兒子是情人的,那就還給情人。 斷愛絕情的沈輕紓展露鋒芒、獨美搞錢。 昔日欺辱她的親人后悔了,爭先恐后上門巴結; 曾嘲笑她靠男人上位的富家子弟后悔了,紛紛重金求愛; 被其他女人教壞的孩子后悔了,哭著喊她媽媽; * 那天深夜,沈輕紓接到一個陌生電話。 電話里傳來傅斯言醉意濃沉的聲音:“阿紓,你不能答應他的求婚,離婚協議我沒簽字。”
110.4萬字8 92 -
完結7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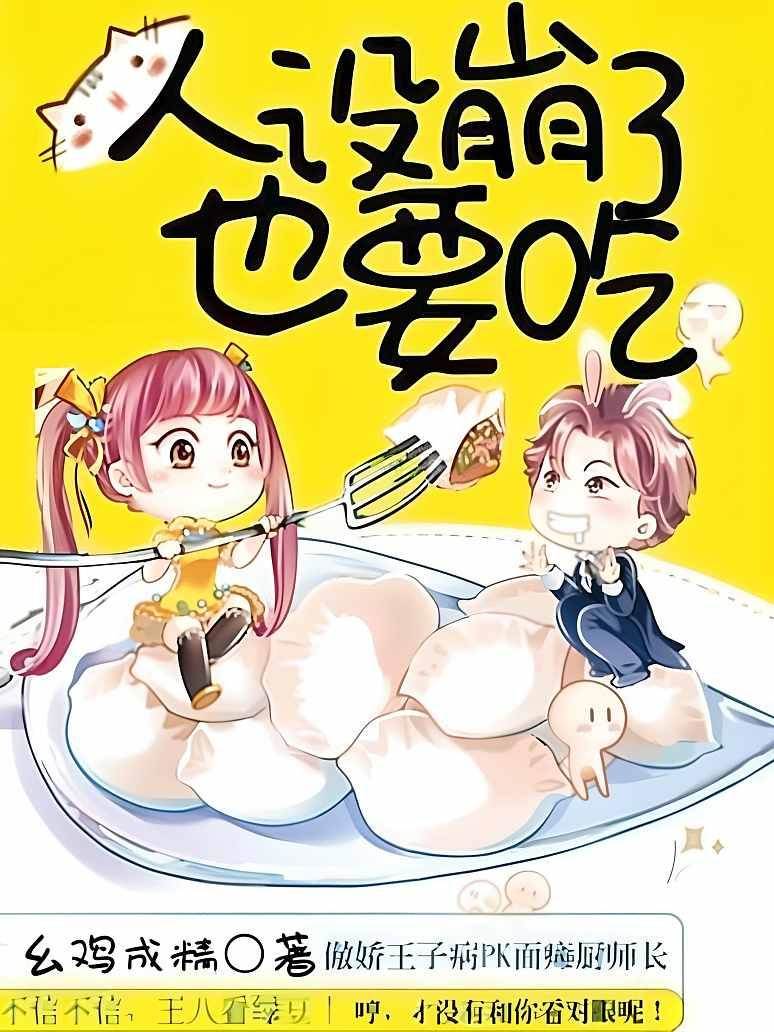
人設崩了也要吃
【那個傲嬌又挑剔的王子病和他面癱很社會的廚師長】 當紅明星封人盛,人稱王子殿下,不僅指在粉絲心中的地位高,更指他非常難搞。直到有一天,粉絲們發現,她們難搞的王子殿下被一個做菜網紅用盤紅燒肉給搞定了…… 粉絲們痛心疾首:“不信不信,王八看綠豆!” 季寧思:“喂,她們說你是王八。” 封人盛:“哼,才沒有和你看對眼呢!” 季寧思:“哦。” 封人盛:“哼,才沒想吃你做的綠豆糕!” 季寧思:“滾。”
17.1萬字8 7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