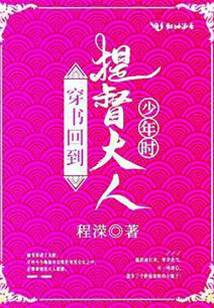《嬌嬌貴女一紅眼,禁欲王爺折了腰》 第105章 各自為謀
次日。
沉碧服侍沈定珠吃飯的時候,看見一張白生生的俏臉,兩眼下浮著淡淡的烏青。
頓時笑了出來。
沈定珠抬眸,目漆黑,有些幽怨“你笑什麼?看我這樣,你還笑得出來。”
沉碧連忙收斂了一點,才低聲音,忍不住竊喜“主子,奴婢是替您高興,覺得暢快,青禾那個小浪蹄子,總該知道誰才是真正寵的人兒了吧?”
沈定珠想到青禾,口那又微微發痛了起來。
昨晚,蕭瑯炎將青禾裝的錯,都一并算在了的上,對“扁圓”,還不住地低聲冷問“下次還敢不敢往本王房里塞人!”
沈定珠抱著他的手冤“青禾自己有那心思,王爺怎麼還怪妾……哎呀!”
剛說完,蕭瑯炎手上便又下了些力氣,低呼一聲。
只聽蕭瑯炎道“本王寵你,哪怕是做做樣子,也足夠嚇住外人,你拿出幾分寵妾的架勢,將趕走,有何不可?”
“還是說,沈定珠你不得本王房中有人,好讓你既本王的厚待,又不用伺候,嗯?”
他說著,修長的手指,猶如點火一般,灼燙地燎過每一細的。
沈定珠最后說都說不出來了,因為越解釋,蕭瑯炎的“懲罰”越兇,最后只能抱著他的胳膊,哭著求饒。
還保證,一定將青禾收拾得服服帖帖,讓再也不敢肖想爬床。
所以這會聽到沉碧的話,沈定珠目幽怨,黑如兩潭水汪汪。
“青禾不懂事,再這樣下去,我也容不下。”不然,青禾放肆一次,苦的是!
Advertisement
沉碧頭一次聽見沈定珠表態,以往他們談論青禾的時候,沈定珠還會強調,寵不寵幸青禾,那是蕭瑯炎的自由。
可現在,的主子終于知道針對那個不守規矩的宮了!
沉碧面大喜,多多給沈定珠添茶肩“主子,要不要將青禾過來敲打一番?”
沈定珠搖頭,纖細的指尖勾住耳邊的一縷碎發,送到耳后。
“青禾是宮里的宮
,咱們的敲打,起不了什麼威懾的作用,你去將來,我自有辦法。”
沉碧立刻去了,不一會,青禾面繃,不愿地跟在沉碧后面。
見到沈定珠以后,青禾也沒有什麼周全的禮儀。
“沈姨娘找奴婢何事?”
“也沒什麼,就是王爺錯將你當了我,原本是要罰你的,可王爺說你伺候得好,細致溫,便我想個法賞你。”
沈定珠指了一下旁邊的柜子“我的裳都是新做的,還不曾穿過幾次,既然王爺賞識你,我的服,你隨便挑一件走。”
青禾眼底劃過一抹亮,角著才沒有當場喜上眉梢。
昨晚見蕭瑯炎醉了,一扶著的胳膊,就喊沈定珠,故而青禾也沒有說破,以為蕭瑯炎是醉得認不清人了。
當時為蕭瑯炎寬的時候,王爺也沒有向平時一樣嚴詞拒絕。
故而,青禾甚至想如果就這樣,被當沈姨娘,從而侍寢了,于來說更是一樁妙事。
只可惜,不知怎的惹惱了蕭瑯炎,被他趕了出來,后面沈姨娘去了,一整夜王爺都在拿泄火。
青禾認定這火是挑起來的,說明寧王對不是全然沒有覺,男人麼,恐怕都拒絕不了那回事。
Advertisement
這會,聽沈定珠這麼說,青禾抿了抿,還佯裝推辭“多謝沈姨娘好意,不過,您的東西奴婢可不能收。”
沈定珠笑了起來,眉眼彎彎,眸清淺澄黑。
“我的東西你不敢,但王爺代讓我照顧好你,你就得收。”
說著,主走到柜子邊,拉開柜門,纖纖玉指招了招“來,你瞧瞧,總有一件喜歡的,挑了以后,你只能私下穿,明白我的意思?”
青禾心頭突突地跳,止不住的歡喜
,心中更是大膽猜測。
地穿?大概是明白了,還要私底下伺候王爺的意思。
于是,青禾也不再忸怩,走到柜子前,果真瞧了起來,可打量了幾眼,都沒有喜歡的裳。
沈定珠帶來的服,說是新的,但腰都卡的太瘦了。
們材相差太遠,青禾也瘦,但跟沈定珠的前凸后翹相比,更像是干瘦,口都沒有二兩,腰也顯得直上直下。
穿這樣的服去伺候蕭瑯炎,豈不是自取其辱?
青禾搖搖頭“沈姨娘好意,奴婢心領了。”
沈定珠看出的神,笑著合上柜門“大抵是沒瞧上吧?無礙,我正有一件嶄新的,還沒全然收過尺寸的裳。”
拉著青禾,讓去繡坊司“你就告訴宮,替我取那日代下去的朱紅珍珠緞。”
聽到朱紅,青禾嚇了一跳“那個,奴婢穿不得。”
沈定珠拉著,小聲道“我不也是私底下嗎?左右都是穿給王爺看的,你怕什麼。”
青禾眼中劃過狐疑,但沈定珠說得篤定,到底還是去了繡坊司。
Advertisement
原本青禾小心翼翼的,以為有詐,可聽繡坊司的說,前陣子沈姨娘確實來過,要了一匹朱紅的珍珠緞做子。
還是和太子蕭玄恪一起來的。
青禾領了服,回來以后,如樣給了沈定珠,便本分地退了出去。
沉碧看著走了,低聲問“主子,沒有上鉤呢。”
沈定珠卻氣定神閑,練了幾頁紙的字,烏發落在雪白的脖頸邊,微垂的眼眸閃爍著貓瞳般的靈神采。
道“不急,青禾又不傻,自然不會貿然闖禍,且等著,忍不了多久。”
這日,沈定珠總算肯去東宮,看蘇問畫了。
蘇問畫憔悴消瘦了許多,因為心事重重,再加上喝一些原本就虛補的保胎藥。
向沈定
珠抱怨,蕭玄恪徹底不理會了。
“定是與傅云秋那個賤人有關,”蘇問畫氣憤地說,可聲音也只敢在嗓子眼,“拿著段,不肯來宮里,皇后娘娘便派人來警告我,要安分養胎。”
蘇問畫發愁“表姐,我現在最害怕的,是皇后娘娘發現我假孕,太子殿下也不護著我了,要不然……”
轉了轉眼眸,直勾勾地盯著沈定珠“你替我打掩護,帶我出宮,躲幾天清凈,可好?”
沈定珠笑了“你可真會為難我,王爺都不許我經常離開玉章宮,我又如何帶你出去?”
蘇問畫繃著臉,像是有些不高興,撇頭看著旁不語。
“你真沒用。”發泄般地說。
沈定珠垂眸,語氣有些淡然“其實我來,也是想告訴你一件事,太子殿下并非對你無意,那天他跟我去繡坊司,還是讓宮人為你做了那件朱紅珍珠緞的子。”
“只不過……”沈定珠有些猶豫。
“不過什麼?”蘇問畫反倒是被勾起了焦急,“你快說啊。”
沈定珠無奈笑笑“只不過,玉章宮里有個宮,替我將服直接拿了回去,我現在若再將服轉贈給你,意味就變了。”
蘇問畫豁然站起來,杏仁眼里充斥著薄怒“哪個宮,敢如此大膽?表姐,你沒有代送到東宮來嗎?”
“我有呀,”沈定珠無辜道,“誰知怎麼想的?否則,我也不至于專程跑一趟向你解釋。”
太子送的服,和太子送給的服跑到了沈定珠那,傳出去,這就是兩層意思了。
蘇問畫咬,片刻后,眼里泛起冷。
“表姐,明晚我去玉章宮,挑個寧王不在的時候,你將那宮給我置!”
沈定珠似乎有些不放心“這能行嗎?皇后娘娘不是才警告過你安分?”
蘇問畫憔悴消瘦的瓜子臉上,浮出一冷意“我倒是有個辦法,讓助我離眼前的困局!”
猜你喜歡
-
完結133 章

偏執太子是我前夫/歲時有昭(重生)
容舒嫁顧長晉時,并不知他心有所屬,更不知她娘為了讓她得償所愿,逼著顧長晉的心上人遠嫁肅州。成婚三年后,顧長晉被當朝皇后尋回,成了太子,而容家一朝落難,抄家罷爵,舉家流放肅州。容舒連夜去求顧長晉,卻被他囚禁在別院。入主東宮后,他更是連夜去了肅…
54.7萬字8 87962 -
完結125 章

枕叔
赫延王府來了個姝色無雙的表姑娘,走路裙裾不動釵墜不晃,人人都夸她名門之儀。長輩有意選她當三郎媳。年關將至,赫延王府的主人封岌歸京。寒酥隨王府眾人迎他凱旋,卻在相見時,臉色煞白,禮數盡忘。沒有人知道,她赴京途中為求自保,是如何進了他的帳入了他…
46.1萬字8.33 60128 -
完結25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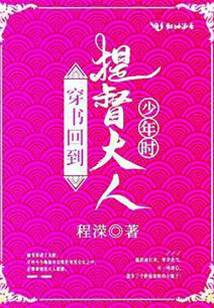
穿書回到提督大人少年時
她書穿成了女配,可憐兮兮地混在公堂的男男女女中,正等著知縣大人配婚。 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 按照劇情她注定是炮灰,超短命的那種。 她不認命,急切的視線在人堆裡可勁兒地扒拉,終於挖掘出他。 夭壽呦,感情這小哥哥,竟是男二! 連女主都無法覬覦的狠人! 這位爺有秀才功名在身,卻被至親算計,入宮成為殘缺不完整的太監。 他生生地熬過種種苦難,任御馬監掌印太監,最後成了人人敬畏的提督大人。 他曾顛沛流離,人人嫌惡,也曾位高權重,人人討好。 成為看盡人生百態,孑然一生的權宦。 但這都不是重點,重點是他壽終正寢! 只要她抱緊他的大腿兒,定能擺脫螞蝗般的至親,待日後做了大宦官之妻,更是吃香的喝辣的,還不用費勁巴拉的相夫教子。 小日子簡直不要太美好,撿大漏啊! 他一朝重生,再回少年時,尚未入宮,更未淨身。 眼下,他還是小三元的窮秀才,父暴斃而亡,母攜家資再嫁。 他浴血歸來,渾身戾氣,可一時善心,就多了個嬌嬌軟軟的小娘子! 說啥他這輩子也不淨身了,好好地考科舉,走舉業,給她掙個誥命夫人做,再生幾個小崽子玩玩兒……
44.7萬字8 23040 -
完結1362 章
相公高中后我決心跑路
白心月穿書了。 穿成了科舉文男主韓文旭的童養媳,全文中最傻的炮灰。 原主作天作地不說,還想偷韓文旭的束脩逃跑,被韓家人抓住后,不出三章就一命嗚呼…… 白心月撓頭:這個路線,我不走。 生活本來就舉步維艱,還有個該死的系統不停瞎指揮! 白心月握拳:我要反抗! 穿到原主偷束脩的橋段,白心月掏出僅有的三文錢,嬌羞的用腳尖畫圈圈:“我給相公存點束脩。” 面對原主嫌惡的顧母,白心月主動示好:“母親,我以后肯定孝順你。” 碰上不搭理原主的韓文旭,白心月一邊計劃逃跑,一邊繼續羞答答的叫:“相公,辛苦了。” 利用金手指,白心月努力賺錢,成功收編顧氏一家,就連冷面冷言的韓文旭也 “心月,待我科舉中考,娶你可好?” 嗚呼?這……自己逆襲成女主了?
245.3萬字8 1388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