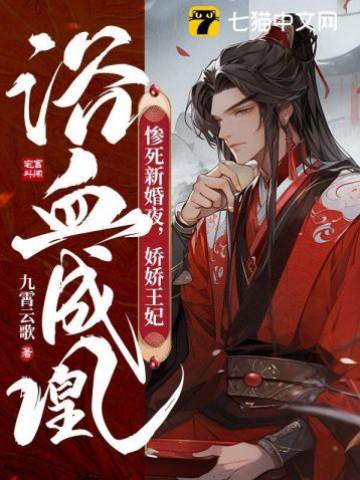《藏玉納珠》 第4章
第4章
玉珠的點頭終於讓老祖宗的笑意蔓延到了眼角,輕拍著玉珠的手說:「既然回來了,就別在出府了,在家裡好好的將養,你母親那裡也是太沒章法,待我申斥了,讓給你陪個不是……」
玉珠連忙道:「這不太折殺了我,萬萬不可……」
一時這頓祖孫的晚飯飯吃起來倒是順心合意。
食完飯後,玉珠本來想回轉自己一直寄居的老宅,可老太太也不放人,只讓先回自己原先的閨房,至於存放的雜,僕役命人搬回來便是。
玉珠在蕭家的主母面前從來是不會說半個「不」字的,當下用餐完畢,以茶漱口後,便一告退,自回閨房安歇去了。
蕭老太太一時也有些乏累了,在婆子柳媽的服侍下,用巾帕子拭一番,便寬躺下準備休息。
柳媽出去倒水,不一會回來,小聲地對老夫人說大爺在外面候著呢。
可老祖宗卻只讓柳媽藉口已經睡下,便將大爺蕭山先打發了。
等柳媽回來,便依著往常的習慣將溫過的手進被子裡替,然後小聲道:「爺眼看著是又要魔的景,老祖宗您怎麼還要留六小姐在府裡?」
柳媽是老祖宗當年出嫁時帶來了,一輩子沒有嫁人,是個府裡的老人兒。蕭老夫人倒是沒有避諱,歎了口氣道:「若是放在外面,只怕山兒便也要長住在外,樂不思蜀了。將自己的六妹養個外室……好說不好聽,不用皇帝下旨,我就算蒙著老臉下黃泉也愧見列祖列宗。原本指他娶了媳婦能收心,可你看他屋裡的陳氏,也是個拿不起來,虧得還是總兵的兒,沒有半點虎門將的氣息。既然是這樣,倒不如六丫頭回來……」
Advertisement
說到這,蕭老夫人想起更重要的事:「對了,不是說明兒,溫將軍便要到了,你告訴景年屋裡的,此事關係著我們蕭府上下,若再一味小肚腸,專營著王家的那點子破事,便自裹了行囊回娘家去……還有,六丫頭穿得太素淨了,既然回了娘家,不必為那王家小子祈福,去庫房裡取幾匹鮮亮的綢緞,給做幾件新,也不至於家裡的貴客輕看了……」
柳媽點頭稱是,替蕭老夫人蓋了被子便悄悄退下了去……
單說玉珠回了自己的房中,也不知是不是大習慣了自小便睡的枕榻,竟是一夜都沒有眠。
第二天一大早,玨兒取來溫水替六姑娘淨面時,略微心疼地看著那雙秋眸之下,平添了兩抹黑暈。六姑娘平時就總是搬弄那些個雕品,勞神費眼,加之皮太白,黑了眼圈便明顯得很,
玨兒心疼地趕取來桌上的茶壺,用絹帕裹了泡開的綠茶葉替玉珠輕輕敷著眼下道:「明明睡得早,怎麼這眼兒還了這樣,要不一會吃了早飯,再躺下休息回籠睡上一覺吧。」
玉珠微啟角笑道:「還當我們是在舊巷裡肆意度日,想怎麼著都?只怕一會便要有人來了吧。」
六姑娘的話剛落了地,果然外面的亭廊傳來的輕快的腳步聲,不一會五姑娘便神采飛揚地推門進來了:「六妹,你可聽說溫將軍下午便要來我們府上做客!」
看著蕭珍兒興難當的臉兒,玉珠輕輕地移開覆在眼下的茶包道:「你說的……可是溫疾才將軍?」
蕭珍兒揮手摒退了自己的丫鬟,然後自搬了凳子坐在了蕭玉珠的旁,微圓的臉兒上竟染上了抹紅暈,低低道:‘妹妹可知,溫將軍的人因為小產崩,幾個月前亡故了。」
Advertisement
這樣的人間慘劇,搭配上五姑娘那一臉撿了荷包的竊喜,實在是有些讓人愕然。
不過在屋整理箱的玨兒倒是知道裡的緣由的。
這位溫疾才是西北的一員虎將,他是蕭家大爺在外求學時的同窗,二人莫逆,當時溫將軍還未如現今一半權勢滔天,溫棟樑也會三五不時地來蕭府做客。
蕭珍兒見了溫將軍幾次後,便儼然將溫郎視作了夢中如意郎君。這般國之棟樑,生得高大健碩、儀錶堂堂,怎麼能不讓人心生慕呢?奈何彼時溫將軍眼裡的芙蓉俏棠是蕭府的二姑娘蕭璐兒,想當初真是差一點,這位溫將軍便了蕭家的姑爺。只是後來,那溫將軍不能與皇上一較高下,場失意之餘,便不再似從前那般頻繁地往來蕭府了。
至於蕭珍兒,單論容貌而言,與胞姐蕭璐兒若牡丹與雛之別;若再加上談吐氣質,便是牡丹與狗尾草之差。
可是溫將軍雖然不曾留心蕭珍兒,五姑娘卻就此埋下種一顆,再看其他男兒難免心生比較,以至於難揀選出整齊的出來。
後來聽聞溫將軍迎娶了一位來自江南的大家閨秀,痛哭了幾次後,才淡了做將軍夫人的心思。可哪裡想到,蒼天不負癡心人,這般矜持著不嫁,竟然等來了正室崩升天的一日,怎麼能不五小姐欣喜若狂?
玨兒想到這,卻忍不住翻了個白眼。那個溫將軍打起仗來勇猛無比,的確是個棟樑,可是他的風評在西北的各大府宅裡也是風號浪吼。只那府裡養著的若干小妾不提,在歡場之上也是能熬度的一員健將。
至於那正室崩,據說也是與府的爭風吃醋有關。這麼一看二小姐還真不愧隨了蕭府老祖宗的七竅心肝,一早便看出溫將軍並非良人,趁著選秀了宮去了。也不知五小姐這般的心急了溫府,那短缺的心眼能不能得住府的勾心鬥角。
Advertisement
玨兒心裡正想著,便聽外屋裡五姑娘接著言道:「人都說溫將軍此番,既是出遊散心,也是要在府宅裡找尋一位合適的子續娶……他別的府宅不去,單來了蕭府……妹妹你說,他會不會向爹娘提親?」
六姑娘聞言道:「這……不大好說,而且我不曾與溫將軍見過,並不知溫將軍是怎樣的人品,可是依著姐姐的品貌,找個年齡相當的年才俊似乎更加穩妥……」
「六妹是不是認為我不配溫將軍?」五姑娘最聽不得旁人提起不能嫁溫疾才,說話頓時有些發急。可一看六妹因為自己提高了嗓門立刻頓口不語,又有些過意不去。昨日因為母親大鬧一場,才知六妹在王家了怎麼樣的委屈。如今祖母才溫暖了六妹的心腸,自己這般臉酸,當真是不妥。
於是不由得又降低了嗓門聲道:「六妹,你說這話,足可見是見識不夠。若是你見過溫將軍便知,那些個府宅裡將養的公子怎麼及得上溫將軍分毫?……不過說來也是湊巧了,為何溫將軍來府上時,你總是不在府裡?不是去廟宇上香,便是隨著祖母去吃素齋泡溫泉了……」
聽了這話,六姑娘只是笑了笑說了句「湊巧罷了」,也沒有再開口說出溫將軍有何不妥之言。
倒是五姑娘想起了自己此來的用意,著六妹的胳膊道:「昨日見你穿的那一窄甚是別致,好過那些大紅大綠的衫,我那些個服都穿得有些發厭,不知能不能穿幾天你的服改一改通的氣韻?」
玉珠愣了一下,道:「昨日母親派人來我吃飯,收到帖子時,時候已經不早了,是以走得急些,也沒有來得及換衫,那一窄是我裁來雕玉做活時穿的,只因為袖服帖,作也便利些,你沒見過,所以覺得新鮮,可是若穿著它來見貴客,面料總是不夠莊重富貴,不若我再給你挑選些合適的可好?」
Advertisement
在穿戴上,蕭珍兒一向信服玉珠,恰好去舊巷的僕役們也送來了六姑娘的箱。
於是玉珠略微翻找了一下,選出件淡藕的長讓蕭珍兒換上,又巧手輕施黛,就算是野草也生出了幾分芍藥的嫵。
蕭珍兒攬鏡自照,不由得慨道:「我們姐妹三個,只有你隨了祖父書房學習了書畫,有了丹青的功底就是不同,怎麼只是改了改我的眉,整個臉兒就似變了模樣呢?」
就在這當口,柳媽也給六姑娘的屋裡送來了料,又與講府裡下午來貴客,讓六姑娘打扮得整齊些一同見客。
聽了這話,蕭珍兒剛剛塗抹的水的臉兒似乎又白了幾分,有些發急地握了絹帕,一雙眼兒不由自主地掃向了還沒有梳妝的六妹。
若是換了旁人,這般模樣只怕是蓬頭垢面的無法見人,可是玉珠就算是頭髮散,未施黛,竟也有種別樣的慵懶之。
好不容易盼走了二姐,可是卻來了比牡丹還要命的瑤池聖蓮,狗尾草的命運便只有在狂風裡打滾了。
不過玉珠倒是好笑地看著蹙眉瞪的五妹:「這般的臉急,好像我搶了你裡的糕餅。可是為何?」
「祖母為何特意你梳洗打扮?難道自覺母親對不住你,要給你尋一門富貴的姻緣?」
玉珠站起來,將挑剩的服逐一疊起遞給玨兒讓收起,語調依然溫溫道:「溫將軍何許人也?這等朝中的大員的妻子哪一個不是家清白?我不過是剛被休離回家的棄婦而已,只姐姐你願意高看我罷了,在外人面前可莫說這等無的笑話。」
經玉珠這般提醒,五姑娘也醒過腔來:是呀,六妹在夫家鬧的事實在是太不堪,若是溫將軍有心,只要打聽了一二,單是與族弟在書房裡不清不楚這一件事,也止了六妹的豪門之路。」
想到這,在替六妹惋惜之余,不由得有升騰起了幾分竊喜。當下也不遠在六妹的房裡耽擱,便要帶著丫鬟去宅院的花房暖室裡摘取些鮮花薰染去了。
昔日溫將軍雖然有職,卻並未如今日一半權傾朝野。出蕭府也不過是下馬扣環罷了。
可是如今他一路青雲直上,手握西北重兵,再不可與昔日小子同日而語,所以將軍的車馬未到,老祖宗已經親自拄著拐杖帶著府裡的一干眾人來到府門外迎接。而玉珠也隨著眾人出來,遠遠地站在了眾人之後。
蕭山從昨夜起一直不得與說話,如今看依舊是一簡素的服,並未見太多修飾,心不由的一寬,只轉過頭來,立在老祖宗的後,一心等將軍的車馬。
可是立在瑟瑟的寒風裡半響,卻始終未見有車馬的蹤影。命僕役去前方打探,好一會才見他一路飛奔地回來,扶著狗皮帽子著聲道:「來了!來了!好長的一隊車馬!」
聽了這話,凍得有些發僵的眾人不由得抖擻起神,著脖子往遠。
僕役之言不假,的確是威武雄壯的一隊車馬,一路拉得老長,在黃土路上掀起了煙塵滾滾。
西北的員不似京城裡的大員那般講究,就算品階再高,出巡時也是五輛高蓋馬車而已。
可是出現在眾人眼前的車隊,卻是鎏金的蓋角,車雕刻有的圖紋,連車軾上也鑲嵌著鴿蛋大的寶石,就算是在略微混沌的下,也閃耀著別樣的彩。而車下的侍從們也都是著錦緞,臉上洋溢著一種說不出的傲慢氣息。這種迥異于平常的華貴奢靡的氣勢,再次震撼得蕭府的眾人發不出聲音來。
當車隊漸漸停歇下來時,蕭山才發現自己的好同窗並沒有坐在馬車裡,而是騎著一匹高頭大馬走在了前面。
他在蕭府眾人的面前停下,也沒有下馬,只是沖著蕭府老太太一抱拳道:「老祖宗別來無恙!」
老夫人連忙施禮,客氣地請將軍府歇一歇腳。
可是溫將軍在馬背上與蕭山客氣地寒暄幾句後,便客氣地說道:「幾日前就收到了簫兄盛邀的書信,原本是想叨擾幾日,奈何近日要陪伴貴客,今日只是路過,就不叨擾府上了?」
如今溫疾才是蕭府的救命稻草,誰知他竟然連馬都不肯下,這不僅讓蕭山開始有些發急,正待要說些什麼,最華貴的那輛馬車華蓋裡有人出聲了。
只是這聲音如刀切兵戈一般刺耳,帶著說不盡的翳:「商賈門前不宜久留,溫兄,你的污濁之氣沾染得太多了……」
這話裡簡直是對西北名家蕭家最無的奚落嘲諷,但又是事實,就算出了一位皇室的寵妃,蕭家始終是買賣玉的商賈之家。
只是不知車裡的是什麼人,竟然對西北的大將軍這般毫無掩飾地出言不遜。
溫疾才被車裡之人出言嘲諷,臉上也是一,只是抱歉地沖著蕭山握了握拳,便催馬鐙,引領著車隊繼續前行了。留給蕭府一干人等的,只是一時彌散不開的迷離黃土。
就算是養氣功夫了得的蕭家老爺,此時也是在自家府門前的石獅子上狠狠地磕打了幾下水煙煙斗道:「丟人啊!丟大發了!」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97 章
首輔大人最寵妻
前世她是繼母養廢的嫡女,是夫家不喜的兒媳,是當朝首輔強占的繼室……說書的人指她毀了一代賢臣 重活一世,靜姝隻想過安穩的小日子,卻不想因她送命的謝昭又來了 靜姝:我好怕,他是來報仇的嗎? 謝昭:你說呢?娘子~ 閱讀指南: 1.女主重生後開啟蘇爽模式,美美美、蘇蘇蘇 2.古代師生戀,男主做過女主先生,芝麻餡護犢子~ 3.其實是個甜寵文,複仇啥的,不存在的~ 入V公告:本文7月7日V,屆時三更,麼麼噠 佛係繼母養娃日常 ←←←←存稿新文,點擊左邊圖片穿越~ 文案: 阿玉穿成了靠下作手段上位的侯門繼室,周圍一群豺狼虎豹,閱儘晉江宅鬥文的阿玉表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奈何,宅鬥太累,不如養包子~~ 錦陽侯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明明是本侯瞧不上的女人,怎麼反被她看不上了? 阿玉:不服?休書拿去! 侯爺:服……
52.4萬字8 32349 -
完結2123 章

醫妃獨寵俏夫君
21世紀的暗夜組織有個全能型殺手叫安雪棠,但她穿越了。穿越第一天就被賣給了一個殘障人士當妻子,傳聞那人不僅雙腿殘疾還兇殘暴戾。可作為聲控顏控的安雪棠一進門就被那人的聲音和俊美的容貌蠱惑住了。雙腿殘疾?冇事,我能治。中毒活不過半年?冇事,我能解。需要養個小包子?冇事,我養的起。想要當攝政王?冇事,我助你一臂之力。想要生個小包子?呃…那…那也不是不行。
363萬字8.5 1190101 -
完結134 章

棄婦覺醒后(雙重生)
前世蘭因是人人稱讚的好賢婦,最終卻落到一個被人冤枉偷情下堂的結局。 她被蕭業趕出家門,又被自己的家人棄之敝履,最後眼睜睜看著蕭業和她的妹妹雙宿雙飛,她卻葬身火場孤苦慘死。 重生回到嫁給蕭業的第三年,剛成為寡婦的顧情被蕭業領著帶回家,柔弱的女子哭哭啼啼, 而她那個從來冷漠寡言的丈夫急紅了眼,看著眼前這對男女,蘭因忽然覺得有些可笑,她所有的悲劇都是因為這一場不公平的婚姻。 既然如此,那就不要了。 和離後的蘭因買宅子買鋪子,過得風生水起,反倒是蕭業逐漸覺得不習慣了, 可當他鼓起勇氣去找蘭因的時候,卻看到她跟朝中新貴齊豫白笑著走在一起。 那是他第一次知道蘭因居然也能笑得那麼明媚。 蘭因循規蹈矩從未對不起誰,真要說,不過是前世那個被冤枉跟她偷情的齊豫白, 他本來應該能走得更高,卻被她連累,沒想到和離後,她竟跟他慢慢相熟起來。 齊豫白冷清孤寂,可在黑夜中煢煢獨行的蘭因卻從他的身上感受到久違的溫暖和疼愛, 他和她說,你不是不配得到愛,你只是以前沒有遇對人。 大理寺少卿齊豫白冷清克制,如寒山雪松、月下青竹,他是所有女郎心中的檀郎, 也是她們愛慕到不敢親近的對象,所有人都以為像他這樣的高嶺之花一輩子都不可能為女人折腰。 不想—— 某個雪日,眾人踏雪尋梅路過一處地方,還未看見梅花就瞧見了他與和離不久的顧蘭因站在一處, 大雪紛飛,他手中的傘傾了大半,雪落肩頭,他那雙涼薄冷清的眼中卻含著笑。 齊豫白活了兩輩子也暗戀了顧蘭因兩輩子。 這輩子,他既然握住了她的手,就再也不會鬆開。
59.3萬字8 47762 -
完結6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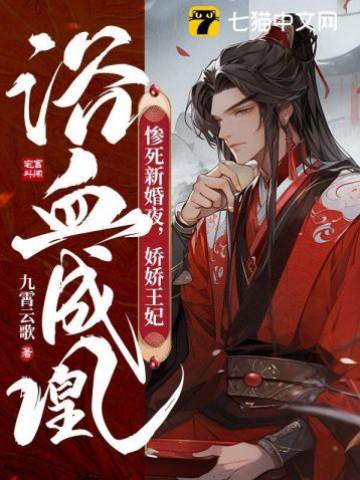
慘死新婚夜,嬌嬌王妃浴血成凰
葉沉魚身為被抱錯的相府假千金,被自己最在乎的“親人”合謀欺騙利用成為毒殺攝政王的兇手,含冤而亡。一朝重生,她回到了真千金前來認親的那一日。 葉沉魚決定做回自己,她洗脫自己的污名,褪下一身華服,跟著鄉野出身的父母離開了相府。 本以為等待她的會是艱苦難熬的生活。 誰料,她的父母兄長個個都是隱藏的大佬,就連前世被她害死,未來權傾天下的那位攝政王,都成了她的……小舅舅。 葉沉魚一臉的郁悶:“說好的苦日子呢?” 蕭臨淵:“苦了誰,也不能苦了本王的心尖尖。”
109.2萬字8.18 1441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