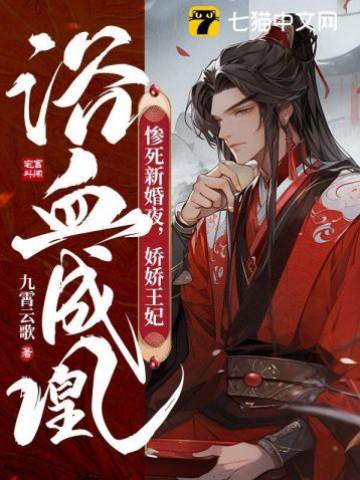《嫁給男主的病秧子哥哥》 076
好氣又好笑,倒也鬆了口氣。好在他不是真的犯病,而是故意裝來嚇的。
隻還有些不放心,回到正院,就對櫻桃道:“使人去看看,長青院請常大夫去了沒有?”
若是請了常大夫,就說明大兒子不是裝模作樣騙的,而是真的子不適。若是沒請,那就是板上釘釘的騙了。
“是,夫人。”櫻桃領命去吩咐了。
不多時,下人回稟,櫻桃學話給侯夫人:“長青院並沒有使人去請常大夫。”
“哼!”侯夫人聽了,一顆心終於放下來,卻是忍不住拍了下桌子,“這混小子!”
一個兩個,長大了都變了混小子!
想到一向沉著穩重,又孝順之極的大兒子如今也會騙人了,侯夫人忍俊不。又是心酸,又是欣,喃喃道:“一個兩個,都是討債鬼。”
“夫人,那咱們請的戲班子……”櫻桃便問。
侯夫人想了想,道:“先留著吧。”萬一兒子明日又改了主意,不出去了,待在府裏豈不是悶?
“明日再說吧。”道。
直到小兒子回來了。
“母親!”賀文璟一進門,就笑盈盈的,“明日元宵節,咱們都出去看花燈,母親和父親去不去?”
侯夫人沒好氣地道:“我一把年紀了,出去怕被散了骨頭。”
“母親不怕,有父親在呢!”賀文璟道,“父親就算自己散了架,也不會人到母親一頭發的。”
侯夫人豎起眉頭,又要他:“一天到晚沒個正形!”
櫻桃便笑道:“奴婢覺著,二爺說得有道理。再說,夫人看起來年輕極了,宛若剛出嫁不久,哪裏就稱得上一把年紀了?”
賀文璟連忙接話:“就是!我看母親年輕得很!自我小時到現在,母親可沒變過樣!”
Advertisement
侯夫人已是被哄住了,還要板著臉道:“你是說我未老先衰?十八年前就這副模樣?”
賀文璟沒辦法了,求救似的看櫻桃,櫻桃隻是笑,賀文璟沒辦法,拿了撣子過來,遞給侯夫人:“母親打我吧,我不會說話。”
侯夫人接過去,佯裝他:“你真要學學怎麽說話了,我的好兒子!”
高高揚起,輕輕落下,竟隻是給他了灰塵,然後遞到一旁,問道:“你們去玩就是,我和你父親就不去了。”
“怎麽不去?”賀文璟道,“咱們一家人都出去,鶴樓有我同窗,回頭我和他說下,給咱們留間好包廂,一家人去賞燈豈不是好?”
他是接了哥哥的拜托來的,一定要說母親和父親出去玩。哥哥很拜托他,賀文璟當然要辦好這件事。
他纏著侯夫人說個不停,一點也不怕侯夫人板著臉,最終侯夫人被他磨得沒辦法,隻得道:“好好好,我答應了還不行嗎?”
賀文璟就笑起來:“那好,我跟哥哥說一聲。”
“嗯?”侯夫人挑起了眉頭。
賀文璟說了,也不怕,反正母親是同意了的,就笑道:“我這就去啦!”
好氣又好笑,倒也鬆了口氣。好在他不是真的犯病,而是故意裝來嚇的。
隻還有些不放心,回到正院,就對櫻桃道:“使人去看看,長青院請常大夫去了沒有?”
若是請了常大夫,就說明大兒子不是裝模作樣騙的,而是真的子不適。若是沒請,那就是板上釘釘的騙了。
“是,夫人。”櫻桃領命去吩咐了。
不多時,下人回稟,櫻桃學話給侯夫人:“長青院並沒有使人去請常大夫。”
“哼!”侯夫人聽了,一顆心終於放下來,卻是忍不住拍了下桌子,“這混小子!”
Advertisement
一個兩個,長大了都變了混小子!
想到一向沉著穩重,又孝順之極的大兒子如今也會騙人了,侯夫人忍俊不。又是心酸,又是欣,喃喃道:“一個兩個,都是討債鬼。”
“夫人,那咱們請的戲班子……”櫻桃便問。
侯夫人想了想,道:“先留著吧。”萬一兒子明日又改了主意,不出去了,待在府裏豈不是悶?
“明日再說吧。”道。
直到小兒子回來了。
“母親!”賀文璟一進門,就笑盈盈的,“明日元宵節,咱們都出去看花燈,母親和父親去不去?”
侯夫人沒好氣地道:“我一把年紀了,出去怕被散了骨頭。”
“母親不怕,有父親在呢!”賀文璟道,“父親就算自己散了架,也不會人到母親一頭發的。”
侯夫人豎起眉頭,又要他:“一天到晚沒個正形!”
櫻桃便笑道:“奴婢覺著,二爺說得有道理。再說,夫人看起來年輕極了,宛若剛出嫁不久,哪裏就稱得上一把年紀了?”
賀文璟連忙接話:“就是!我看母親年輕得很!自我小時到現在,母親可沒變過樣!”
侯夫人已是被哄住了,還要板著臉道:“你是說我未老先衰?十八年前就這副模樣?”
賀文璟沒辦法了,求救似的看櫻桃,櫻桃隻是笑,賀文璟沒辦法,拿了撣子過來,遞給侯夫人:“母親打我吧,我不會說話。”
侯夫人接過去,佯裝他:“你真要學學怎麽說話了,我的好兒子!”
高高揚起,輕輕落下,竟隻是給他了灰塵,然後遞到一旁,問道:“你們去玩就是,我和你父親就不去了。”
“怎麽不去?”賀文璟道,“咱們一家人都出去,鶴樓有我同窗,回頭我和他說下,給咱們留間好包廂,一家人去賞燈豈不是好?”
Advertisement
他是接了哥哥的拜托來的,一定要說母親和父親出去玩。哥哥很拜托他,賀文璟當然要辦好這件事。
他纏著侯夫人說個不停,一點也不怕侯夫人板著臉,最終侯夫人被他磨得沒辦法,隻得道:“好好好,我答應了還不行嗎?”
賀文璟就笑起來:“那好,我跟哥哥說一聲。”
“嗯?”侯夫人挑起了眉頭。
賀文璟說了,也不怕,反正母親是同意了的,就笑道:“我這就去啦!”
一轉,大步跑走了。
侯夫人看著他矯健拔的背影,直是頭痛:“一天天的,長個頭不長心。”
“奴婢說,二爺既孝順又懂事,脾氣還好,滿京城也找不出幾個比二爺還好的。”櫻桃便道。
侯夫人心裏高興,上還要道:“別誇他,那個混小子。”
說完又道:“既如此,請的戲班子就他們不必來了。至於銀子,照給就是了。”
他們這樣的人家,不論缺不缺銀子,麵子是不能丟的。既然請了人,之前還說好了,如今雖然不許人來了,錢卻不能給,以免人說。
“是。”櫻桃應了一聲,便出去跟管事們傳話了。
賀文璟辦了事,就去長青院炫耀,賀文璋眉眼和地看著他,讚許道:“我就知道,文璟靠得住。”又說,“之前我還跟你嫂子說,文璟很有本事,托他辦什麽都。”
“那是。”賀文璟得意地道,在長青院喝了杯茶,就走了,“我得去跟朋友說一聲,讓他在鶴樓給咱們留個包廂。”
他如風似的來,又如風似的走。屋裏頭,賀文璋和於寒舟都鬆了口氣。總算侯夫人不生氣,也不傷心了。
次日一早,賀文璋穿戴得整整齊齊,打扮得神神,領著於寒舟去正院給侯夫人請安。
Advertisement
侯夫人見他臉上果然沒了頹敗之,冷哼了一聲。
賀文璋也沒指把母親瞞過去,總歸母親能原諒他就好了,他笑著說道:“母親,我今日子好多了,既然母親準我出門,那下午我和就出門了。”
侯夫人簡直都想衝他翻白眼了。也就是這些年來一直疼著他,不習慣對他嚴厲,才沒有擺臉。
“嗯。”不鹹不淡地道。
賀文璋笑容滿麵,躬行禮:“多謝母親疼。”
隻見他一臉笑盈盈,好不高興的樣子,侯夫人便有不滿也都散了,說道:“別離了下人,聽到了沒有?”
“聽到了。”賀文璋應道。
待到傍晚,紅霞遍天時,一家人便出了門。
先在鶴樓的包廂裏坐了,用了晚飯,又吃了盞茶,待街上的人流多了起來,人聲也熱鬧起來,賀文璟先坐不住了:“我跟朋友約了時辰,我先走了。”
“去吧。”侯夫人便道。
賀文璋跟著也站起來,說道:“我帶下去走走。”
侯夫人多囑咐了一句:“萬萬不可離了下人,記住了沒有?”
“記住了。”賀文璋道。
侯夫人又看向於寒舟,說道:“你一向穩重,隻是太聽璋兒的話了,今日你多注意些,可不許慣著他。”
“我記住了,母親。”於寒舟也道。
侯夫人便點點頭,允兩人離去了。待人都走了,才看向侯爺道:“咱們也下去走走?”
“好。”侯爺的眉目有些溫和,站了起來。
侯夫人抿笑著,使人拿了麵紗來,仔細戴上。又從包袱裏拿出早就準備好的虎臉麵,給侯爺戴上了,二人這才挽著手下樓了。
於寒舟和賀文璋此刻走在街上。
街上的人很多,有載歌載舞的,有耍猴兒的,有吞劍玩火的,兩旁掛滿了燈,亮如白晝,大人孩子都在笑著嚷著。
“吵不吵?”於寒舟便問賀文璋。
賀文璋彎腰低頭:“你說什麽?”
“我問你,吵不吵。”於寒舟便附在他耳邊說道。
著溫熱的氣流拂在耳朵上,賀文璋的麵上熱了熱。他其實聽見了的,就是想跟挨得近些。眼瞼垂了垂,他偏過頭,也附在耳邊,說道:“不吵。”
他聲音太小,於寒舟沒聽清,就又把耳朵往他邊湊了湊:“沒聽清,你說什麽?”
賀文璋的角勾了勾,更湊近半分,才增大了聲音:“我說,舟舟真好看。”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97 章
首輔大人最寵妻
前世她是繼母養廢的嫡女,是夫家不喜的兒媳,是當朝首輔強占的繼室……說書的人指她毀了一代賢臣 重活一世,靜姝隻想過安穩的小日子,卻不想因她送命的謝昭又來了 靜姝:我好怕,他是來報仇的嗎? 謝昭:你說呢?娘子~ 閱讀指南: 1.女主重生後開啟蘇爽模式,美美美、蘇蘇蘇 2.古代師生戀,男主做過女主先生,芝麻餡護犢子~ 3.其實是個甜寵文,複仇啥的,不存在的~ 入V公告:本文7月7日V,屆時三更,麼麼噠 佛係繼母養娃日常 ←←←←存稿新文,點擊左邊圖片穿越~ 文案: 阿玉穿成了靠下作手段上位的侯門繼室,周圍一群豺狼虎豹,閱儘晉江宅鬥文的阿玉表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奈何,宅鬥太累,不如養包子~~ 錦陽侯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明明是本侯瞧不上的女人,怎麼反被她看不上了? 阿玉:不服?休書拿去! 侯爺:服……
52.4萬字8 32349 -
完結2123 章

醫妃獨寵俏夫君
21世紀的暗夜組織有個全能型殺手叫安雪棠,但她穿越了。穿越第一天就被賣給了一個殘障人士當妻子,傳聞那人不僅雙腿殘疾還兇殘暴戾。可作為聲控顏控的安雪棠一進門就被那人的聲音和俊美的容貌蠱惑住了。雙腿殘疾?冇事,我能治。中毒活不過半年?冇事,我能解。需要養個小包子?冇事,我養的起。想要當攝政王?冇事,我助你一臂之力。想要生個小包子?呃…那…那也不是不行。
363萬字8.5 1190101 -
完結134 章

棄婦覺醒后(雙重生)
前世蘭因是人人稱讚的好賢婦,最終卻落到一個被人冤枉偷情下堂的結局。 她被蕭業趕出家門,又被自己的家人棄之敝履,最後眼睜睜看著蕭業和她的妹妹雙宿雙飛,她卻葬身火場孤苦慘死。 重生回到嫁給蕭業的第三年,剛成為寡婦的顧情被蕭業領著帶回家,柔弱的女子哭哭啼啼, 而她那個從來冷漠寡言的丈夫急紅了眼,看著眼前這對男女,蘭因忽然覺得有些可笑,她所有的悲劇都是因為這一場不公平的婚姻。 既然如此,那就不要了。 和離後的蘭因買宅子買鋪子,過得風生水起,反倒是蕭業逐漸覺得不習慣了, 可當他鼓起勇氣去找蘭因的時候,卻看到她跟朝中新貴齊豫白笑著走在一起。 那是他第一次知道蘭因居然也能笑得那麼明媚。 蘭因循規蹈矩從未對不起誰,真要說,不過是前世那個被冤枉跟她偷情的齊豫白, 他本來應該能走得更高,卻被她連累,沒想到和離後,她竟跟他慢慢相熟起來。 齊豫白冷清孤寂,可在黑夜中煢煢獨行的蘭因卻從他的身上感受到久違的溫暖和疼愛, 他和她說,你不是不配得到愛,你只是以前沒有遇對人。 大理寺少卿齊豫白冷清克制,如寒山雪松、月下青竹,他是所有女郎心中的檀郎, 也是她們愛慕到不敢親近的對象,所有人都以為像他這樣的高嶺之花一輩子都不可能為女人折腰。 不想—— 某個雪日,眾人踏雪尋梅路過一處地方,還未看見梅花就瞧見了他與和離不久的顧蘭因站在一處, 大雪紛飛,他手中的傘傾了大半,雪落肩頭,他那雙涼薄冷清的眼中卻含著笑。 齊豫白活了兩輩子也暗戀了顧蘭因兩輩子。 這輩子,他既然握住了她的手,就再也不會鬆開。
59.3萬字8 47762 -
完結6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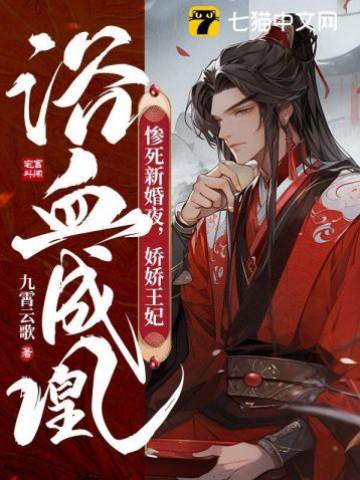
慘死新婚夜,嬌嬌王妃浴血成凰
葉沉魚身為被抱錯的相府假千金,被自己最在乎的“親人”合謀欺騙利用成為毒殺攝政王的兇手,含冤而亡。一朝重生,她回到了真千金前來認親的那一日。 葉沉魚決定做回自己,她洗脫自己的污名,褪下一身華服,跟著鄉野出身的父母離開了相府。 本以為等待她的會是艱苦難熬的生活。 誰料,她的父母兄長個個都是隱藏的大佬,就連前世被她害死,未來權傾天下的那位攝政王,都成了她的……小舅舅。 葉沉魚一臉的郁悶:“說好的苦日子呢?” 蕭臨淵:“苦了誰,也不能苦了本王的心尖尖。”
109.2萬字8.18 1441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