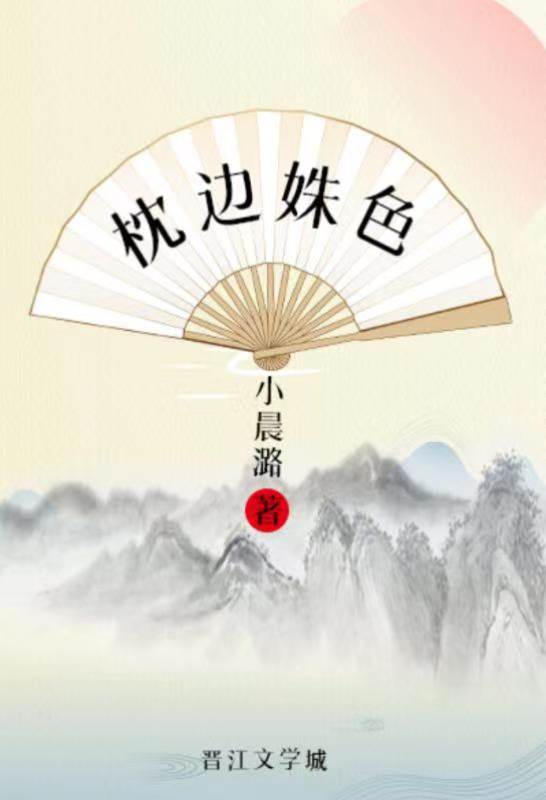《神醫魔后》 第48章 帝尊,臣困了
于是玄家傾全族之力,將夜無岸曾走過的那條通道徹底打通并穩固起來,一來留給玄家傳人往來穩定無岸海,一來也是留著應服那場大劫。
可平定無岸海時用的只是虛空化之法,真正能夠利用這條通道送走的全魂,只有五個。
爺爺說,阿珩阿染和卿卿都到了,再來,就是第四個,可剩下的靈脈怎麼辦呢?
夜家已經不存在了,那麼靈脈傳人慕驚語的穿越,又該如何進行?
上一次通過虛空化之法來到無岸海面時就發現,海上的海陣十分厲害,縱然是玄脈夜家的后人,也沒有辦法破解海陣達到在海域暢通無阻。
明知摯友就在此,卻不知該如何相聚。世五脈逃出四脈,還剩一脈卻失了穿越的介。
這一場劫數,終究是把們五家全都算計到了。
忽然就生出幾分煩躁來,夜溫言停下腳步,仰頭天。不知何時起竟下雪了,雪花不大,慢悠悠地飄落下來,落到臉上,很快就覆住了長長的睫。
這些事是此時此刻忽然想起來的,可是在穿越的最初,這些記憶卻并不完整,以至于當初一時間沒反應過來這個時代究竟是個怎樣的存在,又為何會吸引著們這些人前仆后繼,一個接一個地以各種方式來到這里。
停下腳步,催花為引,檢查自己的記憶。
如今已經沒有缺失了,想來是當初剛剛穿越,腦子里又一下子灌進來太多關于原主的記憶,所以一時間有些混。
眼下都想起來,許多事一下子明朗許多。
玄脈夜家啊,是因為過于強大嗎?是老天爺都在限制夜家的發展嗎?
否則為何自清末年間起,夜家就開始代代單傳,無論嫡系還是旁枝,再沒有多余的男丁出現?甚至到這一代直接就斷了香火?
Advertisement
二叔,三叔,夜傾城,那不過是爺爺的養子。時不知為何二叔三叔沒有半分靈力,直到長大才懂,那本就不是夜家的骨,是的爺爺不甘就這樣被老天爺算計,從孤兒院抱養來的孩子。
從前以為人丁興旺是好事,甚至有些旁枝還效仿此行,也去認養子,也去以這樣的方法向老天爺表達不滿和反抗。
可如今看來,終究是害了人家,終究是連累人家跟著夜家人一起喪命。
若早知道,若早知道,可前世今生,又哪來的“早知道”……
炎華宮,帝尊師離淵拉著欽天監監正云臣下棋。
這個棋打從云臣自一品將軍府回來就開始下,一直下到這會兒都快接近子時了。
云臣困得直耷拉頭,卻還在咬牙堅持著,不但堅持著下棋,還得堅持著給帝尊講故事。
恩,就講他這趟去一品將軍府,遇到了什麼人,發生了什麼事,四小姐夜溫言說了幾句話,幾句話里分別都講了什麼。
一下午加一晚上,這些事云臣前前后后已經講了十八回,明明都是差不多一樣的容,帝尊卻總是能從一模一樣的容里,挑出一兩樣新鮮的節來,這讓云臣好生佩服。
最后一子落下,云臣又輸了,帝尊給他下達了一道新的命令:“練棋,再這樣下去,本尊只能另外培養一個新的監正了。”
云臣連連答應著,心里卻不斷地哀嚎:難道帝尊大人您給欽天監選監正,就是為了陪您下棋嗎?
終于沒有再打開新的一局,云臣長長地松了口氣,就聽師離淵道:“本尊記得許多年前,皇家好像得了一塊暖玉,是從一火山口里生出來的東西,帶在上無論四季都散暖意。后來那東西給了誰?”
Advertisement
云臣想了一會兒,答:“聽說是給了六殿下,臣也只是聽說,因為東西是六殿下生下來不久就給了的,那時候臣還小,沒進宮做監正。”
師離淵點點頭,“哦。”再道,“明兒去要過來。”
云臣立即應下:“臣遵命。”至于為什麼要過來,他才懶得分析,反正這個天下只要帝尊說要什麼,就沒有人敢不給。區區一塊暖玉,帝尊看上了那是六殿下的福氣。
不過他心里也有一番猜測,夜四小姐臉蒼白常打冷,那塊暖玉怕不是要來送給四小姐的吧?
夜溫言走在皇宮里,并沒有第一時間往炎華宮的方向去,到是走著走著就走到了神仙殿。
先帝駕崩那晚,就是在神仙殿里治好了七殿下的嗓子。那個跟傾城長得很像的孩子,后天就要做這北齊國的皇帝了,很想去看看他。
神仙殿大殿前,吳否站在雪地里,仰著頭往房頂上看,一邊看一邊喊:“皇上,快下來吧!這還下著薄雪呢,屋頂,危險得很。”
聽到吳否說話聲,也抬頭看了去,果然看到房頂上有個人,正踩著被白雪覆蓋的琉璃瓦走來走去。雖然形還算平穩,但雪卻被踩得偶爾掉下來一塊兒,看著也嚇人。
每掉下來一塊雪,吳否都要打個激靈,權青城每跳一下,吳否都嚇得要閉上眼睛。
偏偏屋頂上的年皇帝還同他說:“吳公公你不要膽子那樣小,我從前雖不會說話,但功夫卻是一直學著的。就算及不上四哥五哥,也不至于就拙劣到會從屋頂上掉下去。”
吳否了一把腦門上的汗,一臉的無奈:“明日先帝落葬,雖有帝尊送您,但也得提早休息啊!”
“時辰尚早,不急。”
Advertisement
“還早?都快到子時了!”吳否實在是拿這個年皇帝沒有辦法,小孩子玩兒心重,總這樣下去可如何是好?他什麼時候能長大呢?
后有人在他肩頭輕輕拍了一下,帶著一子浸人的花香。
吳否嚇得一激靈,猛地回過頭來,赫然發現后竟站著一個不屬于皇宮里的人。
他眼,揮了揮眼前飄落的雪花,這才認出來人是于他有著救命恩的夜溫言。
可這夜四小姐何以大半夜的出現在皇宮里?又是如何做到能神不知鬼不覺地走到神仙殿,后竟沒有一位宮人或是軍侍衛跟隨過來?
“四,四小姐。”吳否開口,說話都結了,一時間更是沒想好是該行禮問安,還是該問究竟是怎麼進來的。
夜溫言也不說話,只沖著他笑笑,然后手朝著一個方向指了指。
那是炎華宮的方向,是上一次進宮時,云臣告訴的。
吳否明了,也不再疑了。先帝駕崩那天晚上他就意識到一個關鍵,這夜四小姐怕不是跟云臣有往來,而是跟云臣背后的那個人有幾分瓜葛。否則帝尊的聲音出現在承殿時,也不會點名道姓地提到夜家四小姐,云臣更不會對這位四小姐的態度那樣的恭敬。
可是這話他不能說,心里有數就行,上是萬萬不能講的。
眼下夜溫言指了炎華宮的方向,那就說明這一趟進宮是炎華宮那位應允了的。之所以神出鬼沒無人跟隨而來,怕也是炎華宮那位施了大法。
那是天大的本事,不是他這種凡人能夠覬覦的。
于是俯施禮,“奴才問夜四小姐安。”
夜溫言點點頭,“吳公公不必多禮,我去看看皇上,跟他說說話,公公在下面等著也可,先行回去歇著也可。不必擔心皇上安危,一切有我呢!”
Advertisement
說完,整個人輕飄飄地騰了空,看在吳否眼里那就如同仙一般,奔著屋頂上的權青城就去了。
吳否抹了把汗,心道果然是帝尊的人,這騰空飄起來用的絕對不是輕功,到像是仙法。
權青城也看到夜溫言玄妙般地騰空而起,但是他沒有驚訝,因為那天夜溫言給他治嗓子,用的就絕不是凡人手段。他一直將那視為他二人之間的小,每每想起總會在心中竊喜。
眼瞅著人飄到自己眼前,穩穩下落,權青城笑容燦爛,一雙桃花眼彎了好看的弧型。
他說:“姐姐你來啦!”
點頭,“恩,來看看。”
“我就知道姐姐不是普通人,你是神仙,就跟那位一樣。”權青城手也往炎華宮那邊指了指,然后蹲下來,用寬大的袖子在琉璃瓦片上掃出一塊干凈的地方來。“姐姐坐。”
夜溫言坐下來,見權青城也坐到邊,這才問道:“你大半夜的不睡覺,在這里走來走去的干什麼?吳公公在下面急得團團轉,要不是我到了,怕是他都得去求助軍把你給接下去。他說得沒錯,雪天瓦片太,很容易摔了。”
“不會的,我以前也經常這樣在屋頂上走。”權青城說,“從六七歲那時起,我就喜歡在屋頂上站著了。因為站得高看得遠,不像人在下面,轉頭就只能看到四面房屋那般憋屈。只是那時候沒有人管我,母妃總要去皇后娘娘那邊請安問禮,下人們也覺得我是個啞,將來肯定是沒什麼前途,所以本也沒把我放在眼里。”
“但是現在不一樣了。”告訴他,“現在你是皇帝,你的安危關乎著國運,就不可以再這樣任。就算會功夫,也要時時加倍小心。”
“姐!”他抓上的手腕,就像前世夜傾城一著急激時,也喜歡兩手抓著的腕一樣。“姐,后天就是登基大典了,這兩日群臣以及兩宮太后已經舉議了攝政王的人選。是小皇叔,我父皇最小的一個弟弟……”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74 章
錯嫁皇妃帝宮沉浮:妃
一夜承歡,失去清白,她卻成了他代孕的皇妃。紅綃帳內,他不知是她,她不知是他。紅綃帳外,一碗鳩藥,墮去她腹中胎兒,她亦含笑飲下。惑君心,媚帝側,一切本非她意,一切終隨他心。
64.9萬字8 15557 -
完結568 章

爽翻天!穿到古代搬空國庫去流放
【空間 女主神醫 女強 爽文 虐渣 發家致富 全家流放逃荒,女主能力強,空間輔助】特種軍醫穿越古代,剛穿越就與曆史上的大英雄墨玖曄拜堂成親。據曆史記載,墨家滿門忠烈,然而卻因功高蓋主遭到了皇上的忌憚,新婚第二日,便是墨家滿門被抄家流放之時。了解這一段曆史的赫知冉,果斷使用空間搬空墨家財物,讓抄家的皇帝抄了個寂寞。流放前,又救了墨家滿門的性命。擔心流放路上會被餓死?這不可能,赫知冉不但空間財物足夠,她還掌握了無數賺錢的本事。一路上,八個嫂嫂視她為偶像,言聽計從。婆婆小姑默默支持,但凡有人敢說赫知冉不好,老娘撕爛你們的嘴。終於安頓下來,日子過得一天比一天紅火。墨玖曄:“媳婦兒,我們成親這麼久,還沒有洞房呢!”赫知冉:“想洞房,得看你表現。”墨玖曄:“我對天發誓,一輩子心裏隻有你一個女人,不,下輩子、下下輩子也是。”赫知冉:“你說話要算數……”
104.2萬字8.43 421630 -
完結347 章

娘娘總是體弱多病
邰家有二女,長女明豔無雙,及笄時便進宮做了娘娘 二女卻一直不曾露面 邰諳窈年少時一場大病,被父母送到外祖家休養,久居衢州 直到十八這一年,京城傳來消息,姐姐被人所害,日後於子嗣艱難 邰諳窈很快被接回京城 被遺忘十年後,她被接回京城的唯一意義,就是進宮替姐姐爭寵 人人都說邰諳窈是個傻子 笑她不過是邰家替姐姐爭寵的棋子 但無人知曉 她所做的一切,從來不是爲了姐姐 所謂替人爭寵從來都是隻是遮掩野心的擋箭牌 有人享受了前半生的家人寵愛,也該輪到其他人享受後半生的榮華富貴
52.3萬字8 52 -
完結37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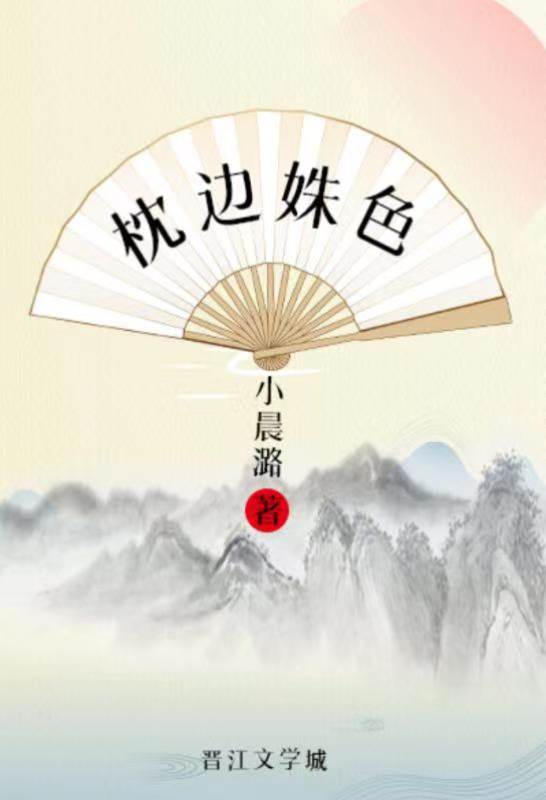
枕邊姝色(重生)
阮清川是蘇姝前世的夫君,疼她寵她,彌留之際還在爲她以後的生活做打算。 而蘇姝在他死後,終於明白這世間的艱辛困苦,體會到了他的真心。 得機遇重生歸來,卻正是她和阮清川相看的一年。她那時還看不上阮清川,嫌棄他悶,嫌棄他體弱多病……曾多次拒絕嫁給他。 再次相見。蘇姝看一眼阮清川,眼圈便紅了。 阮清川不動聲色地握緊垂在身側的右手,“我知你看不上我,亦不會強求……”一早就明白的事實,卻不死心。 蘇姝卻淚盈於睫:“是我要強求你。” 她只要一想到這一世會與阮清川擦肩而過,便什麼都顧不得了,伸手去拉他的衣袖,慌不擇言:“你願意娶我嗎?”又哽咽着保證:“我會學着乖巧懂事,不給你添麻煩……我新學了沏茶,新學了做糕點,以後會每日給你沏茶喝、給你做糕點吃。” 她急切的很,眸子澄澈又真誠。 阮清川的心突然就軟成一團,嗓音有些啞:“願意娶你的。” 娶你回來就是要捧在手心的,乖巧懂事不必,沏茶做糕點更是不必。
58.5萬字8 6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