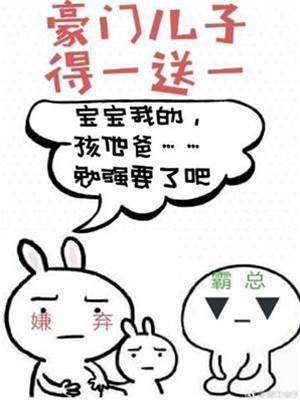《吻刺》 第79頁
就這麼幾秒鐘等喝水的功夫,也是單手著口袋,形慵懶。
方慈別開臉。
這還是第一次在事后的清晨相。
赧的覺竟比事進行時更甚。
又回頭,飛快地看了他一眼,說,“……你能不能穿上服……”
自己當然不知道,這時候的長發也是凌的,肩帶一邊落,瓷白的臉上有紅暈,漂亮的眼睫低垂著。
濃濃的事后氣息。
聞之宴深深看一陣,抬手了發頂,說,“我去洗澡。”
方慈重新躺回被窩。
太因宿醉而作痛,拿過手機,解鎖屏幕。
微信新消息史無前例的多。
略掃了一眼,先打開了跟陳巧月的對話框。
「C:你昨晚跟聞親了?!」
「C:可以啊你們倆!好張狂!我喜歡!」
「C:咋回事,快給我講講」
「C:好多人攛掇我找你算賬呢」
「C:你倆是要公開了嗎?宋裕澤咋辦?」
方慈默了默,打字回復:
「方慈:是不是都在傳了?都怎麼說的?」
圈里同齡的公子哥大小姐就那麼些個,一點消息都傳得飛快,一夜過去,估計早就有不版本了。
陳巧月發了幾條語音過來:
Advertisement
“我好幾個姐妹群都炸了。”
“說你膽兒真大,聞脾氣有點兒難捉什麼的。”
“不過們好像都認為只是逢場作戲。”
“畢竟嘛,聞這格,他會談?沒人信的。”
這倒也是。
圈里最不缺的就是逢場作戲這一套,怎麼可能有人就因為游戲上的一個吻,就斷定他們有特殊關系?
他們這圈子里,玩兒的比這大的海了去了。
沒人會真的往心里去。
放下手機,眼著天花板,甚至有幾分不真切的混沌。
真是喝多了,竟敢當著那麼多人的面去吻聞之宴。而他,竟還把摁到懷里,專心完了那規定的一分鐘。
手機再度嗡聲震。
一通電話,來顯是宋裕澤。
剛接通,那邊就殷切地,“方慈,是我,宋裕澤。”
“……嗯。”
“你怎麼樣?昨晚喝了杯尾酒吧,頭痛嗎?要不要我給你買點解酒藥?”
他這突然而來的關切,讓方慈心生幾分茫然。
宿醉的腦子,轉了兩秒,才艱難地想起來,這應該是之前簽的協議合同,被宋承業給知道了。
宋承業畢竟是生意人,這麼大的事兒,肯定不會貿然聲張,大概率是派宋裕澤來討好,順帶打探一下背后的“大佬”的份。
Advertisement
想到這兒,方慈話到邊的“不用了”也咽了回去,改口說,“行,你買了送到我宿舍。”
“誒誒好的,”宋裕澤忙道,“那你好好休息啊。”
掛了電話,宋家別墅,宋裕澤茫然更深,抬頭看他爸,“爸,方慈到底拿到我們家什麼把柄了?要這麼討好?”
“你別問那麼多,”宋承業整了整領帶,道,“反正就是很嚴重的事,你按照我說的去做,時刻注意方慈,我這邊空約一下方家父母。”
摁斷通話,方慈發了會兒呆。
想到電話里宋裕澤那幅從沒有過的討好語氣,不由覺得好笑。
這就是之前,聞之宴承諾過的,“我讓他怕你。”
果真是頂豪繼承人的夸張做派,花了十幾個億,讓為暗地里的東,讓宋承業方寸大,讓宋裕澤戰戰兢兢。
宋家總歸是不會再敢給臉看了,甚至,以后只有看臉行事的份兒。
這一晚,天翻地覆。
掀被子下床,夢游似的,一邊朝洗手間方向去,一邊思忖著。
聞之宴在更間,剛洗完澡換好服,轉頭看到這幅模樣,失笑著,幾步走過來,一把攬住的腰,幾乎是攜著把弄到淋浴間。
Advertisement
花灑打開,溫熱的水澆下。
方慈回神,“干什麼?”
聞之宴嗤了聲,低眸看,“……你猜?”
睜大了眼,手忙腳去推他的手臂,“你瘋了?剛起床……嗚……”
他眼睫被水打,一簇一簇地低垂著,笑得漫不經心,“你告訴我,我要干什麼。”
他的手墊在的脊背和瓷磚之間,大概是防止傷到。
脊背的皮一下一下從他掌心磨過。
渾沒有任何支撐點,只能用力攀了他的肩背,憤憤地去咬他的肩。
-
終于洗完。
方慈換好了服,又開始抖。
氣不過,涼涼地說,“聞之宴,我拜托你,知點節制。”
聞之宴懶洋洋笑道,“小姐,我今年21歲,現在節制,我不如去當和尚。”
冷冷看他一眼,轉頭對鏡弄領口。
頸上又是紅痕。
聞之宴倚靠著洗手臺,慢悠悠地,“而且,你不想多試試嗎?各個時間、各個地點。”
不搭理,心事重重的模樣。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1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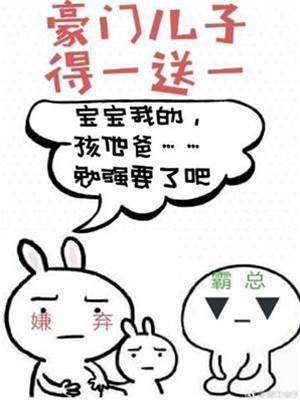
豪門兒子得一送一
別人去當后媽,要麼是因為對方的條件,要麼是因為合適,要麼是因為愛情。 而她卻是為了別人家的孩子。 小朋友睜著一雙黑溜溜的大眼,含著淚泡要哭不哭的看著林綰,讓她一顆心軟得啊,別說去當后媽了,就算是要星星要月亮,她也能爬著梯子登上天摘下來給他。 至于附贈的老男人,她勉為其難收了吧。 被附贈的三十二歲老男人: ▼_▼ ☆閱讀指南☆ 1.女主軟軟軟甜甜甜; 2.男主兒砸非親生; 3.大家都是可愛的小天使,要和諧討論和諧看文喲!
31.8萬字8.33 47271 -
完結72 章

心機女的春天
韓熙靠著一張得天獨厚的漂亮臉蛋,追求者從沒斷過。 她一邊對周圍的示好反應平淡,一邊在寡淡垂眸間細心挑選下一個相處對象。 精挑細選,選中了紀延聲。 —— 韓熙將懷孕報告單遞到駕駛座,意料之中見到紀延聲臉色驟變。她聽見他用浸滿冰渣的聲音問她:“你設計我?” 她答非所問:“你是孩子父親。” 紀延聲盯著她的側臉,半晌,嗤笑一聲。 “……你別后悔。” 靠著一紙懷孕報告單,韓熙如愿以償嫁給了紀延聲。 男人道一句:紀公子艷福不淺。 女人道一句:心機女臭不要臉。 可進了婚姻這座墳墓,里面究竟是酸是甜,外人又如何知曉呢?不過是冷暖自知罷了。 食用指南: 1.先婚后愛,本質甜文。 2.潔黨勿入! 3.女主有心機,但不是金手指大開的心機。
22.8萬字8 6822 -
完結857 章

重生九零肥妻歸來
中醫傳承者江楠,被人設計陷害入獄,臨死前她才得知,自己在襁褓里就被人貍貓換太子。重生新婚夜,她選擇留在毀容丈夫身邊,憑借絕妙醫術,還他一張英俊臉,夫妻攜手弘揚中醫,順便虐渣撕蓮花,奪回屬于自己的人生。
159.8萬字8 97590 -
完結523 章

重生蜜戀:偏執九爺他淪陷了
前世,云漫夏豬油蒙心,錯信渣男賤女,害得寵她愛她之人,車禍慘死!一世重來,她擦亮雙眼,重啟智商,嫁進白家,乖乖成了九爺第四任嬌妻!上輩子憋屈,這輩子逆襲!有人罵她廢物,醫學泰斗為她瑞殺送水,唯命是從,有人嘲她不如繼姐:頂級大佬哭著跪著求她叫哥!更有隱世豪門少夫人頭街為她撐腰!“你只管在外面放建,老公為你保駕護航!”
88.6萬字8.18 140070 -
完結167 章

聖佛子人設崩了,原是寵妻狂魔
【強製愛 男主偏執 雙潔】南姿去求靳嶼川那天,下著滂沱大雨。她渾身濕透如喪家犬,他居高臨下吩咐,“去洗幹淨,在床上等我。”兩人一睡便是兩年,直至南姿畢業,“靳先生,契約已到期。”然後,她瀟灑地轉身回國。再重逢,靳嶼川成為她未婚夫的小舅。有著清冷聖佛子美譽的靳嶼川,急得跌落神壇變成偏執的惡魔。他逼迫南姿分手,不擇手段娶她為妻。人人都說南姿配不上靳嶼川。隻有靳嶼川知道,他對南姿一眼入魔,為捕獲她設計一個又一個圈套......
29.1萬字8.18 45878 -
完結150 章

垂涎你許久
【破鏡重圓+強取豪奪+雙潔1v1】向枳初見宋煜北那天,是在迎新晚會上。從那以後她的眼睛就再沒從宋煜北臉上挪開過。可宋煜北性子桀驁,從不拿正眼瞧她。某次好友打趣他:“最近藝術係係花在追你?”宋煜北淡漠掀眸:“那是誰?不認識。”後來,一個大雨磅礴的夜晚。宋煜北不顧渾身濕透,掐著向枳的手腕不肯放她走,“能不能不分手?”向枳撥弄著自己的長發,“我玩夠了,不想在你身上浪費時間了。”……四年後相遇。宋煜北已是西京神秘低調的商業巨擘。他在她最窮困潦倒時出現,上位者蔑視又輕佻的俯視她,“賣什麽價?”向枳躲他。他卻步步緊逼。無人的夜裏,宋煜北將她堵在床角:“說你後悔分手!”“說你分手後的每個日夜都在想我!”“說你還愛我……”四年後的宋煜北瘋批難纏,她嚇到想要跑路。逃跑時卻被宋煜北抓回。去民政局的路上,她被他紅著眼禁錮在懷裏:“再跑,打斷你的腿!”
25.4萬字8 850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