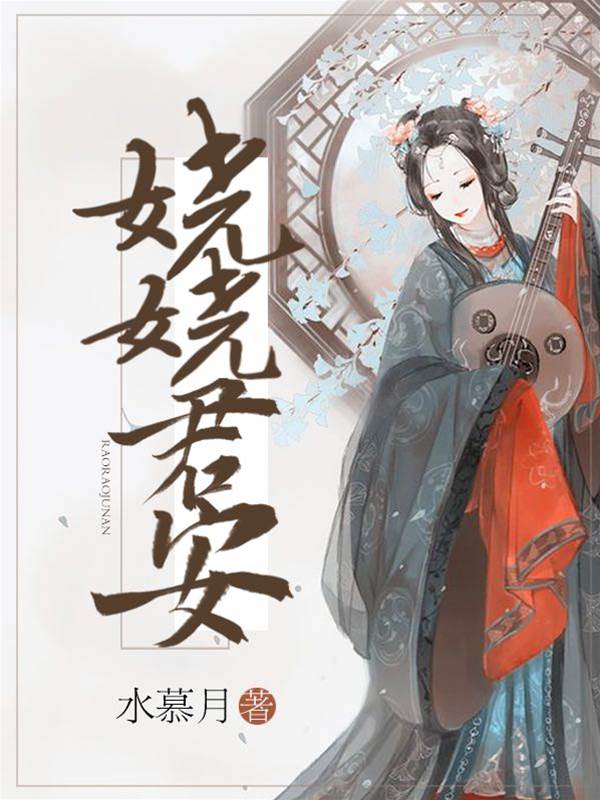《紅酥手》 第92頁
余嫻依舊不搭理他。
看來是真生氣了,蕭蔚不再拖沓,同解釋道:“世上之事,無論如何必有兩面,軍中有位副將,近幾年就專收殘疾士兵。你在繁華鄞江看那聾啞奴仆,自然覺得可憐,但在苦寒之地,戍守邊疆,正缺這些一心無可兩用的人才。聾兵守營帳;跛足站哨崗;眼盲者耳聰;聲滯者心專……各人有各人的用①。你二哥去了苦寒之地,沒人慣著他,軍中紀律嚴苛,他必須遵守,自食其力,不出兩年,心智大改。”
說罷,兩人走到了府門,小廝牽了馬車出來。待上了馬車,余嫻將一番話細想過,才問他,“你的意思是,二哥不僅不會死,而且于國于己都大有用?”
雙轅待要滾走時,良阿嬤趕上了,坐在外頭。
蕭蔚以巾帕拭臉上雪化后的水漬,“近幾年邊境安穩,又有名將戍守,就算有敵軍來犯,都是些小打小鬧,總歸不會起大。你二哥就算想上戰場,都沒機會,想死,就更不容易了。再說,苦寒之地距鄞江千里之外,人人只求眼前生活,沒人會把手到鄞江來,覬覦勞什子玉匣,就算有,你二哥當個無名小卒,難道還會仗著遠在鄞江的爹娘的勢報上名號嗎?誰也不會知道你二哥的份。他待在那里,最好不過了。”
第42章 面首的作用?嘶……
磨礪心, 是畢生所不能休止的歷練。二哥若將來有,再回過頭看,也許也會慨機緣。
Advertisement
回到蕭宅, 良阿嬤離開視線,余嫻與蕭蔚同去書房。
“你為何要幫二哥?”余嫻回想他方才說過的話,滿腹疑:“你不是說你我之間恐有海深仇,若真相確然,你就要向余府報仇麼?把二哥送到偏遠之地,豈不是饒他一命?”
待坐好, 蕭蔚關上了門,稍一思索, 反手銷。轉過頭見余嫻狐疑地盯著他的作,他坦然解釋, “你也不希我們聊正事, 有人來打擾吧。”
是嗎?這嫻的反鎖手法,是為了防正經進出嗎?余嫻擺弄手絹,想起那夜他發瘋的樣子, 不有點張。
蕭蔚慢悠悠解開外袍, “我只想在做壞事前,多做些好事。若能讓你開心, 日后我們形同陌路時, 你不要記恨我。”
作什麼要在說正事的時候服?奇怪了, 這屋子里的炭火什麼時候燒起來的,也許是他覺得屋熱吧, 余嫻別開眼, 額間一滴汗落下,才意識到自己還系著他的大氅, 遂抬手想解,一頓,又覺著在他解時自己也解,不太對勁。
“那你又為何幫我瞞份,連春溪和良阿嬤都不告訴?”方才在馬車,余嫻分明也能問他這問題,卻怕被良阿嬤聽了去,隨他到書房才問出口。蕭蔚走到前,幫解大氅,眸清明,一不易察覺的悅然藏在眸底,“你怕我被良阿嬤砍。”
他就站在前,低頭凝視,大氅被解開,余嫻也沒有掙扎,一片坦,“是,你若死了,我如何證明阿爹的清白給你看?話本子里從來沒有負心人便宜去死的道理,都是活著贖罪。”
Advertisement
“你不舍得我死,把話說得這麼漂亮。”蕭蔚毫不留地穿,見面紅耳赤作惱狀,還想反駁,他不再拐彎抹角,搶先道,“這些天我總在想,你為何不信我心悅你。直到看到了你二哥氣急敗壞的模樣,我才明白過來。原來你和你二哥一樣,惱怒后,總有一種不肯回頭的固執,俗稱。”
余嫻蹙眉,聽得逆耳,想側過不理他,卻被他夾住了雙,正對的是他勁瘦的腰腹,這位置頗為尷尬,他還居高臨下看著,的大外側擰不過他的側,不能轉,只好把頭偏向一邊。
他卻還在說,“你以為我早就深不渝,便為我付出真心,結果突然得知我并不真心喜歡你,覺得很丟臉。所以當我再像從前那般傾于你時,你總有千萬種借口說我的不是,好像只要說我有詭計,便將從前的事扳回了一城,彌補了從前沒看出我真面目的愚蠢似的。”蕭蔚附湊近,“是這樣嗎?”
是什麼是,余嫻絞著角,著他言又止,最后只能把頭再側到另一邊不看他,扯開話題:“元賀郡主邀我去冰嬉,不是我想同你講和,實則是也邀了你……定在十八日,你我姑且作一作相敬如賓吧。”
“相敬如賓,不好。”蕭蔚垂眸,耳尖變紅的一剎那,他手捧起了的臉,挽起角,“我對你已經假戲真做,就連你的氣急敗壞,我也越看越歡喜。薛晏確實是個自私小人,想不顧一切地要你,在你上留滿那種東西,哪怕將來海深仇難越,也想強迫你留在邊一輩子。但蕭蔚卻是理智的,知道不能這樣做,你愿意時,‘強迫’是調,你不愿意時,強迫只會讓你不開心,上次沒有把握好分寸,那樣魯莽,就鬧得你不開心,所以我更想要玉匣真相如你所言,你我能堂堂正正在一起,而現在,只等你愿意。”
Advertisement
只是真相究竟如何,兩人都抱著惶,生怕是萬劫不復,但又因著那一點希與期許,在跟命運較勁。
但他怎麼把薛晏那樣齷齪的心思都坦白給講?余嫻聽得汗和頭發都快豎起來了,這人到底設不設防?諸如那種東西之說,傳出去他還要面子嗎?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2229 章
帝凰之神醫棄妃
大婚當天,她在郊外醒來,在衆人的鄙夷下毅然地踏入皇城…她是無父無母任人欺凌的孤女,他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鐵血王爺.如此天差地別的兩人,卻陰差陽錯地相遇.一件錦衣,遮她一身污穢,換她一世情深.21世紀天才女軍醫將身心託付,爲鐵血王爺傾盡一切,卻不想生死關頭,他卻揮劍斬斷她的生路!
448.5萬字8.38 388648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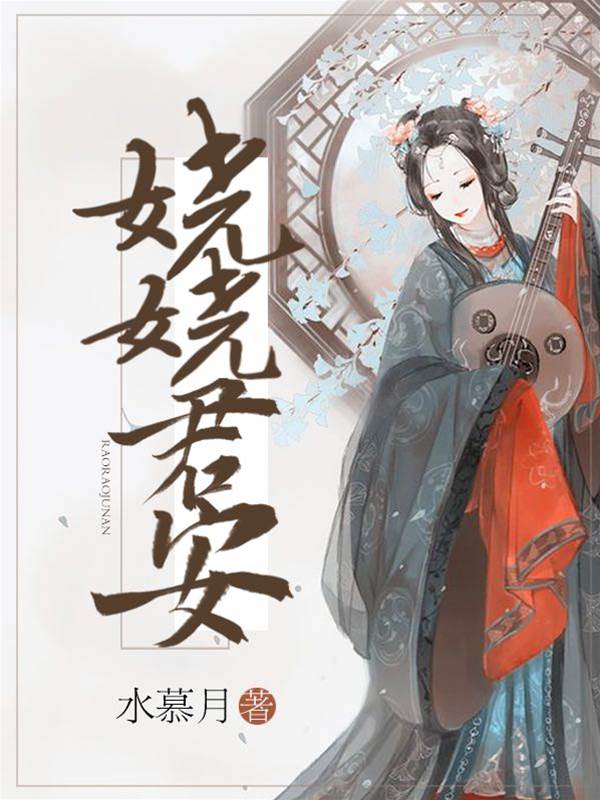
嬈嬈君安
原想著今生再無瓜葛,可那驚馬的剎那芳華間,一切又回到了起點,今生他耍了點小心機,在守護她的道路上,先插了隊,江山要,她也絕不放棄。說好的太子斷袖呢!怎麼動不動就要把自己撲倒?說好的太子殘暴呢!這整天獻溫情的又是誰?誰說東宮的鏡臺不好,那些美男子可賞心悅目了,什麼?東宮還可以在外麵開府,殿下求你了,臣妾可舍不得鏡臺了。
16.6萬字8 14823 -
完結648 章
重生后,我成了渣男他皇嬸
因道士一句“鳳凰棲梧”的預言,韓攸寧成了不該活著的人。外祖闔府被屠,父兄慘死。太子厭棄她卻將她宥于東宮后院,她眼瞎了,心死了,最終被堂妹三尺白綾了結了性命。再睜開眼,重回韶華之時。那麼前世的賬,要好好算一算了。可慢慢的,事情愈發和前世不同。爭搶鳳凰的除了幾位皇子,七皇叔也加入了進來。傳說中七皇叔澹泊寡欲,超然物外,
116.3萬字8.18 58167 -
完結242 章

教不乖,佞臣替人養妹被逼瘋
【傳統古言 廢殺帝王權極一時假太監 寄人籬下小可憐 倆人八百個心眼子】少年將軍是廝殺在外的狼,窩裏藏著隻白白軟軟的小兔妹妹,引人垂涎。將軍一朝戰死沙場,輕躁薄行的權貴們掀了兔子窩,不等嚐一口,半路被內廠總督謝龕劫了人。謝龕其人,陰鬱嗜殺,誰在他跟前都要沐浴一番他看狗一樣的眼神。小兔落入他的口,這輩子算是完……完……嗯?等等,這兔子怎麽越養越圓潤了?反倒是權貴們的小團體漸漸死的死,瘋的瘋,當初圍獵小兔的鬣狗,如今成了被捕獵的對象。祁桑伏枕而臥,摸了摸尚未顯孕的小腹。為了給兄長複仇,她忍辱負重,被謝龕這狗太監占盡了便宜,如今事得圓滿,是時候給他甩掉了。跑路一半,被謝龕騎馬不緊不慢地追上,如鬼如魅如毒蛇,纏著、絞著。“跑。”他說:“本督看著你跑,日落之前跑不過這座山頭,本督打斷你的腿!”
42.7萬字8.18 1579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