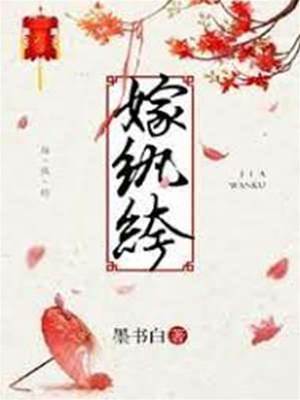《齊歡》 第七十八章 團聚
徐清歡聽到外麵的呼聲,整個人不一僵,難以控製的鼻子發酸,眼前一片模糊,幾乎忘記了屋子裏還有人在,轉就向外麵走去。
剛剛重生時,見到母親就愣在那裏,以為一切都是假的,母親還以為病了,聲喚了半,然後抱了母親,哭得像是個孩子。
在翔時生怕前世的事重演,若讓再錯過一家人團聚的時刻,即便重生又能如何。
一張悉的麵孔出現在眼前,就像見到母親那一刻一樣,的眼淚不由自主地淌下來。
經過了那麽多歲月,還能回到從前一家人重新站在一起。
老真是厚待,從到大所有的記憶湧上心頭,便是讓烈火灼燒十次,換來一瞬間的團聚,也值得了。
眼看著父親慈祥微笑的臉,一下子變得張起來,推開了擋在父中間的人,大步到了麵前。
“這是怎麽了?是不是一路上顛簸了委屈,就不該讓你們母兩個去翔。”
父親高大的影停在麵前,出一隻大手輕輕地拍的後背。
想起時候父親將扶上肩膀,帶著全家人一起出去看花燈,低下頭就能看到母親微笑,哥哥在向做的鬼臉。
母親擔憂胃口不好,從來不讓吃外麵的東西,哥哥就將買來的糖稀喂給,一轉頭被母親發現,麵目含淚,就算應付過關,轉頭就又會向哥哥張開。
如今還記得那糖稀的味道。
淚流到邊,竟然是甜的。
父親雖然已經許久不曾帶兵,卻仍舊每日堅持練拳腳功夫,騎自然也不會生疏,站在那裏腰背拔,上還是那種武將特有的風采。
“兒沒什麽委屈,兒隻是有些想念父親。”
如果再不話,恐怕父親護心切會將脾氣發在別人上。
Advertisement
聽到兒這樣,安義侯還是半信半疑地乜了眼被他推到一旁的兒子,離京這麽久,兒仿佛長大了許多,看起來比平日裏更加懂事,這不肖子卻越活越回去的樣子,安義侯眼角一跳,臉變得難看。
在父子倆剛剛對視,還沒有冒出火花之前,安義侯夫人恰時出現,安義侯的臉上的冰霜立即就像被風吹散了般:“素英,這一路辛苦你了。”
著也不顧邊有人,上前拉住了妻子的手。
安義侯夫人的臉立即紅了,埋怨著道:“不是讓人回去了,我們會徑直回家,侯爺在府中等我們就好了,怎麽還迎過來。”
安義侯道:“正好做完了事……在府中還要再等一……”
“侯爺還沒用飯吧,”安義侯夫人吩咐邊的媽媽,“快去準備一下。”
安義侯沒有拒絕,一雙眼睛看著妻子兒圍在邊甚為滿意,目落在徐清歡後的房間時,微微皺了皺眉,看向徐青安:“住進來的時候有沒有去問清楚,客棧裏都住了些什麽客人。”
“問了,”徐青安道,“母親和妹妹可以安心住,上麵這些房間都是留給眷的,不會有外人進來。”
安義侯指了指徐清歡後:“那間房呢?”
“是給妹妹的。”
門關著,屋子裏亮著燈。
徐清歡忽然想起宋暄還在裏麵。
父親怎麽突然關注起的屋子了?與宋暄私下裏見麵,隻有哥哥和邊的人知曉,還沒有稟告父母,若是就這樣被撞到,好像要費一番功夫來解釋。
徐清歡正要上前挽住安義侯的胳膊,安義侯卻向那間屋子走去。
宋暄坐在椅子上,目睹了安義侯一家人的團聚。
他的耳邊響起的是安義侯的腳步聲。
步伐輕快、有力,可見功夫依舊很紮實,這間屋子的門雖然被關上,約約還能過那扇菱窗看到安義侯的影。
Advertisement
安義侯輕聲安兒,一家人如此其樂融融。
這種氣氛卻與他格格不。
宋暄不由自主地微微攥起手,他耳邊是廝殺的聲音,眼前一片紅,一柄劍穿過他的,刺骨的寒意他如今都清楚的記得。
午夜夢回時,常常會被那種記憶中的疼痛驚醒,他至今過那麽多的傷,卻都沒有那次的疼痛。
宋暄站起,手握了劍柄,仿佛就要將利刃從中拔出,他的眼睛中是冷峻和化不開的寒意。
可最終他鬆開了手,轉向窗子走去。
安義侯推開了門,屋子裏空空如也,隻有桌上的一盞燈。
窗子打開著,一冷風從外麵吹進來。
見屋子裏沒人,徐清歡鬆了口氣。
“窗子也不關好,”安義侯道,“萬一了風可怎麽得了。”
雛見狀立即快步走進去將窗子關。
“都好,”安義侯將妻子、兒反複打量了一遍,看看邊的管事、廝、丫鬟,還有那隻神氣的鳥,然後才踏實地坐下,“我早就想去翔接你們,卻沒想到蘇懷出了事,莫須有的罪名下來,幸虧有簡王在其中周旋,本來就是捕風捉影的事,罪名倒是來得快也去得快。”
到這裏,安義侯臉上流不滿的神:“如今稅銀找到了,文書到了京城,簡王就拿著進了宮,一也沒耽擱就讓人將蘇懷放了出來,都察院還想生事,讓簡王幾句話頂了回去,來京中為蘇懷訴冤的百姓也散了,總歸是有驚無險。”
安義侯夫人道:“想想翔的事,到現在我還膽戰心驚,侯爺你也差點被牽連進去。”
安義侯並不清楚其中,看著妻眼睛紅了,心中更是一:“好了,現在不是沒事了,我是沒想到族中二哥、三哥早就包藏禍心……現在總算了結清楚……”
Advertisement
“到底有沒有了結,現在還不知道。”安義侯夫人看向徐清歡。
徐清歡點點頭:“父親,整樁案子都沒那麽簡單,不管是翔的案子,還是廣平侯府的細,我覺得有好多細節還不清楚。”就算現在最有嫌疑的人是王允,但相信憑王允一人也無法如此布局。
也許查到最後,就會發現就連王允,也是被人放置的一顆棋子。
提起廣平侯,安義侯麵沉重起來:“廣平侯被留在京中,等候案子審結,西北的兵權恐怕也要付給旁人了。”
“啊,”安義侯夫人有些驚訝,“廣平侯在西北這麽多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廣平侯夫人是細,別皇上不肯再相信廣平侯,素來與廣平侯不合的員也趁機在這件事上做文章,牆倒眾人推,可憐廣平侯一世英豪。”
這些話不宜在客棧裏太多。
一家人敘了幾句家常,安義侯才想起被丟在一旁的兒子:“你又有沒有惹禍?”
本著不好欺騙父親的神,徐青安點了點頭。
安義侯臉上呈現出暴風雨前的寧靜,幾乎從牙裏出幾個字:“知不知悔改。”
徐青安點頭,但是很快他有不自覺地搖頭。
他要……改什麽啊。
眼看著安義侯如雄獅般起,徐青安慌張地道:“爹,娘讓你嚇著了。”
趁著安義侯去看妻的功夫,徐青安像個紙片人般,靠著牆溜走了。
“在外不教子。”
安義侯默念三遍魔咒,恢複了正常,一臉虧欠地看妻:“都是我生了個不肖子,你消消氣,我給你腳。”
躺在床上,邊是妻,安義侯覺得一顆懸著的心終於落下,可不由自主地他又想起了朝局。
安義侯夫人道:“我在翔聽廣平侯進京求娶清歡,心裏有些焦急。”
安義侯道:“你們都不在家中,我怎麽可能會答應。”
“多虧你沒應,廣平侯世子爺八兇多吉了,這些年……大周糟糟,我真怕。”安義侯夫人著攥了安義侯的胳膊,將頭依偎了上去。
“到清歡的婚事,”安義侯歎了口氣,“當年我們都已經給訂過親了,我是真喜歡那個孩子……
如果不是出了那件事,如果一切都好的話,不定我們已經在為清歡籌備嫁妝了。”
安義侯夫人明顯地覺到安義侯的手臂在微微發抖,死死地攥了安義侯。
“可惜,沒有如果。”
…………………………
求票票求留言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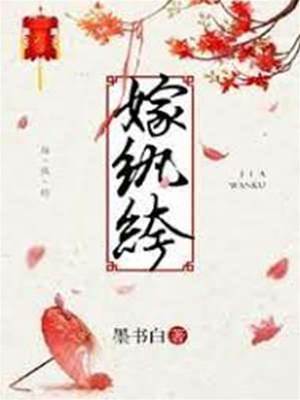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50163 -
完結1573 章

絕色神醫:驚世五小姐
【重生,1v1雙強甜寵,雙向奔赴。】 蘇慕绾重生到十四歲那年, 她還未和謝景年退婚, 她的爹娘還在,哥哥還未墜崖,壹切都還來得及, 這壹世她要讓蘇挽秋和謝珩亦付出代價,上壹世欠她的,她通通都要討回來。 這壹世,她不會再讓謝景年早逝,哥哥也不會落得壹個身死的下場,且看她如何妙手回春,手撕渣男賤女…… 某個午後: 壹絕色女子枕在壹位極俊極雅氣質出塵的白衣男子腿上,紅唇微啓,語氣慵懶又帶有壹絲魅惑:“阿景,這輩子妳都別想再逃~” 他薄唇輕啓,滿眼寵溺的低垂著眸子,看著懷中的小人兒:“嗯,不跑,我裏裏外外都是妳的。”
363.2萬字8.18 249619 -
完結522 章
寵后之路誤惹狼君萬萬歲
辛鳶對天發誓,當年她撿到家裏那頭狼時純粹是因為愛心,要是她知道那頭狼會有朝一日搖身一變成為九五至尊的話,她絕對……絕對會更早把他抱回家! 開玩笑,像這樣美貌忠犬霸氣護妻的狼君還能上哪找?不早點看好,難道還等著別人來搶嗎?某狼君:放心,誰來也搶不走! 辛鳶:我得意地笑了~
91萬字8 200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