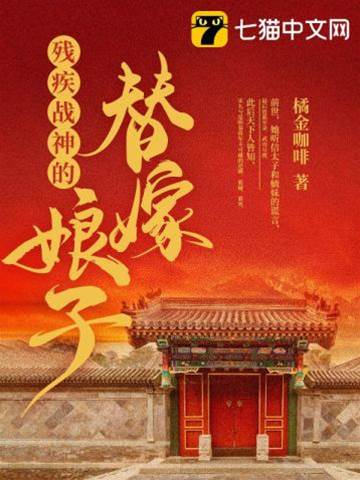《丞相夫人是首富》 第281頁
“進去說罷。”紀云汐打斷,將人帶了進去。
正廳之中,秋玉有些不自在地坐著。
在清河郡之時,大家都在黑暗的礦中住著,雖裳不同,可在礦里待久了,都會臟。
可這會,坐在這雅致致的正堂之中,看著主位上華麗的紀云汐,和來來往往說說笑笑的丫鬟,秋玉有些晃神。
還停留在清河郡那日,寶福死那日,每日每夜,都想著那一幕,怎麼睡都睡不好。
秋玉原以為,紀小姐,或者這些和寶福一起長大的丫鬟們,應當也會與一樣,可好像不是。
們似乎都忘記寶福的存在了。
秋玉眼里帶著幾分黯然。
紀云汐垂眸,抿了口茶,輕聲問:“你來找我,可是有何事?”
秋玉沉默片刻,還是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對著紀云汐福了福:“紀小姐,讓我當您的丫鬟罷!”
紀云汐眉眼了,臉上沒有太多波瀾:“為何?”
秋玉道:“是寶福救了我一命,我這條命就是的!您在寶福心里不僅僅只是主子,所以我想代替守護著您。”
此言一出,廳一片寂靜。
紀云汐著茶盞里著淡綠的茶水,好半天沒有說話。
秋玉又道:“我找到了我夫君和孩子,也安置好了。寶福救我一事,我和他們都說過了,來涼州府衙當您丫鬟,他們也同意。紀小姐無需擔憂,日后跟著您回上京城也無事。”
Advertisement
紀云汐將茶盞輕輕放下,對堂中的秋玉道:“不用了,你回去罷。”
秋玉一愣:“紀小姐可是嫌棄我?我”
紀云汐打斷:“我不缺丫鬟。”
秋玉沉默半晌,苦笑道:“是嗎?”
看向主位的紀云汐,又看了看后方站著的晚香,和當日一起在礦中燒火做飯的幾個丫鬟,們也在看著。
秋玉雙手捂著臉,問道:“紀小姐,這才多久,你們就不難過了嗎?”
為什麼好像,只有還記得,只有還在難過?
紀云汐扯了下角,看向外頭明的午后暖。
沒有多說什麼,輕嘆口氣:“回去罷,和家人好好過日子。”
說完后,紀云汐起,讓晚香們送一送秋玉,抬腳往后院而去。
嘎吱一聲,紀云汐推開了寶福的房間。
寶福的房間一塵不染,布局與在時一模一樣,雪竹每日晨間都會進來打掃一番。
一旁的桌上,放著一個古樸的骨灰盒。
骨灰盒旁,擺著一玉瓶,玉瓶之中,中紅的月季正在怒放。
這是那幾個丫頭今日剛換的花。
花旁邊,還有串糖葫蘆。
紀云汐手,輕輕了骨灰盒的邊緣,無聲道:“待回到上京城,我再將你安葬在院里的月季花田下。”
那月季是寶福親自種的,寶福最月季。
紀云汐坐了一會兒,關上門離去。
*
Advertisement
太子走了,涼州府衙的事沒人幫吳惟安,故而這幾日他都有些忙。
不過他心不錯,回到臥房之中時,角帶笑。
待他一看見房中整整齊齊擺著的幾大箱子時,腳步瞬間停了下來,問人榻上懶洋洋蜷著的人:“這、這些可是?”
“嗯,首款。”紀云汐隨手翻過一頁雜書,“你點點。”
現代給錢收錢都是轉賬,多數目一目了然。
到了古代,就麻煩了一些,不過也有銀票和金票,拿到錢莊兌換便可。
但吳惟安說,他不要銀票也不要金票,就要現的,黃燦燦的,會發的,黃金。
紀云汐滿足他。
雖然也不知,到時回上京城時,他準備怎麼把這些黃金帶回去。
不過這也和無關了。
紀云汐話音剛落,吳惟安便反手鎖上了臥房的門,而后將袖卷起,開始一箱一箱點黃金。
只是隨口說說的紀云汐:“你還真點?”
吳惟安:“不然?”
紀云汐的角輕輕了:“……”
懶得管他,看了幾頁雜書后有些犯困,便回到了床上,倒下就睡。
可箱子被搬的聲音,黃金與黃金相撞的聲音時不時傳來,弄得紀云汐很無奈。
過了一會兒,聲音總算停下,心滿意足的吳惟安去洗漱了。
紀云汐卻睡不著了。
將被子往下拉了一些,轉過頭朝堆著的箱子看去,目沉沉,似乎在思索著什麼。
Advertisement
洗漱回來,頭發還半的吳惟安看見的便是這一幕。
他不聲地走過去,遮住紀云汐看向他私人財產的視線:“不是困了嗎?怎麼還未睡。”
紀云汐看向他:“總覺得,有些虧。”
十萬兩黃金,可不是小數目。
而且,他的勢力,欠了不錢啊。
可不僅僅只是十萬兩黃金。
吳惟安走過去,在床邊坐下,輕聲道:“你哪里虧?”
紀云汐抬眸,定定看向他。
吳惟安俯,長發落下一縷,剛好落在紀云汐的脖頸間,微微:“我都是夫人的了,夫人哪里虧?”
他直直迎上的視線,瞳孔極黑,仿佛能吞噬一切。
紀云汐睫忍不住眨了下,又眨了下。
脖頸間實在太,手,就將他的發拂開。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904 章

田園錦色:空間娘子種田忙
她空間在手,醫術也有,種田養娃,教夫有方。他抬手能打,拿筆能寫,文武全才,寵妻無度!他們雙胎萌娃,一文一武,天賦異稟,最會與父爭寵!“孃親,爹爹在外邊闖禍了!”大寶大聲的喊道。“闖了什麼禍?”“孃親,爹爹在外邊招惹的美女找回家了……”二寶喊道。“什麼?該死的……”……“娘子,我不認識她……啊……”誰家兒子在外麵幫爹找小三,還回來告狀坑爹。他家就兩個!
266.7萬字8.18 93047 -
完結52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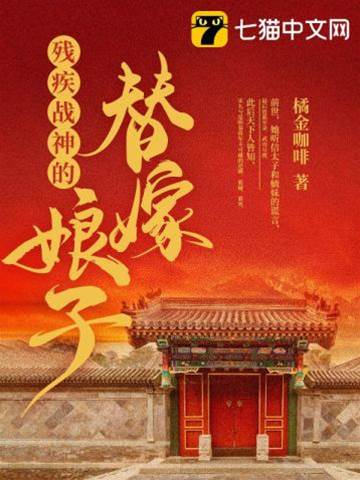
殘疾戰神的替嫁娘子
【重生+男強女強+瘋批+打臉】前世,她聽信太子和嫡妹的謊言,連累至親慘死,最后自己武功盡廢,被一杯毒酒送走。重生后她答應替嫁給命不久矣的戰神,對所謂的侯府沒有絲毫親情。嘲笑她、欺辱她的人,她照打不誤,絕不手軟。傳言戰神將軍殺孽太重,活不過一…
97.6萬字8.18 35390 -
完結530 章

撿了五個哥哥後,京城無人敢惹
流浪十五年,薑笙給自己撿了五個哥哥。 為了他們,小薑笙上刀山下火海,拚了命賺錢。 哥哥們也沒辜負她,為妹妹付出一切。 直到,將軍府發現嫡女被掉包,匆匆忙忙找來。 可也沒好好待她。 所有人譏她粗野,笑她無知,鄙她粗獷。 卻無人知道,新科狀元郎是她哥哥,新貴皇商是她哥哥,獲勝歸來的小將軍是她哥哥,聖手神醫是她哥哥,那一位……也是她哥哥。 假千金再厲害,有五個哥哥撐腰嗎? 不虐,男主未定,無固定cp,任憑大家想象 ???
101.3萬字8 193896 -
完結302 章
悍妃從商記
當再次醒來,看到兒子,她心情激動,卻不想卻深陷在一個帝王陰謀當中,且看花想容如何用自己的商業頭腦,打造一片,古代的驚天商業帝國……
77萬字8 1105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