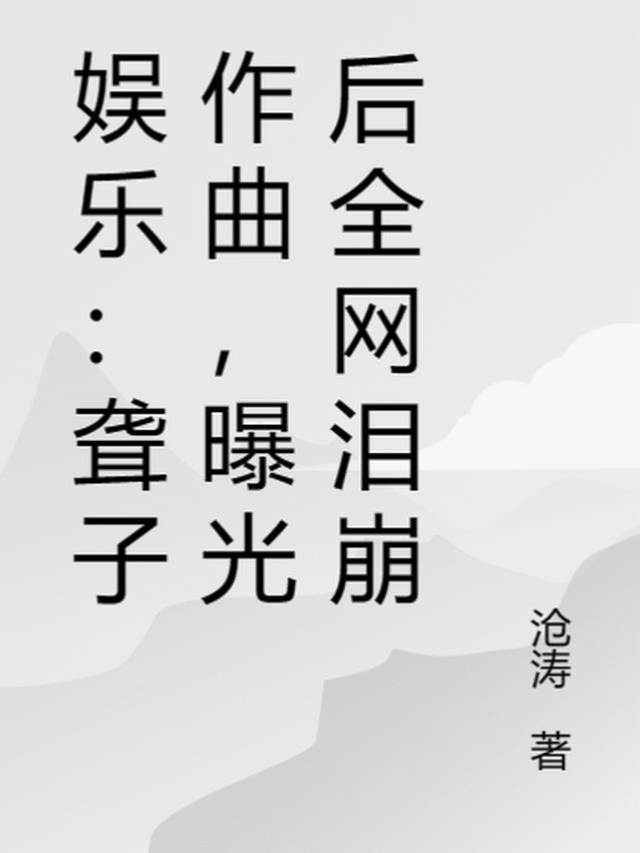《我曾於你心尖之上》 第123章 說愛他
如果哪天我把紋洗掉了,那就代表,我真的不你了。
意在,紋在。
如今紋不在了。
那對他的意自然也不在了。
原來真的不他了。
或許從決定洗掉紋的那一刻,就不再他了。
霍衍的眼底蒙上了一層薄薄的水霧,有那麽一瞬間,他似乎快哭了。
霍衍閉眼,滿眼痛楚。
明明都說過那麽多次不他了。
為什麽看到紋沒了的那一刻,他的心,仍舊如同被人撕碎了一般。
-
辦事才辦到一半。
俞晚的藥效沒有得到緩解。
尤其此時不上不下的,弄得俞晚更是難至極。
不滿霍衍走神的俞晚直接反撲霍衍。
過往俞晚也不是沒有過如此主狂熱的時候。
可一想到俞晚此時的主不過是藥驅使,霍衍的心,一陣悲哀,生不起任何歡喜。
明明曾經他們做這種事的時候,是那般的心靈合一,心靈相通。
無論是還是心,都能到大大的愉悅。
可為什麽。
此時此刻的他,卻難過得像要死掉一般。
俞晚知道他是誰嗎?
霍衍的腦海裏忽然冒出了這麽一個念頭。
這個念頭如同野火一般,迅速燒了起來。
霍衍握住俞晚的腰,猛地翻將在下。
霍衍雙目猩紅地看著俞晚,手不輕不重地上的臉頰,“俞晚,我是誰?”
俞晚雙目迷離的看著他,眸底帶著濃濃的不解,“嗯?”
“我是誰?”
霍衍又問。
俞晚盯著他看了十幾秒,隨後吐了兩個字,“阿衍。”
見認得自己,霍衍麵不由一喜,“對,我是阿衍,是你的阿衍。”
霍衍低頭親吻俞晚妖豔的紅。
像一個著別人給他糖吃的小孩子似的,他對俞晚說,“俞晚,說你我。”
Advertisement
俞晚一雙目風萬千地看著他,好似聽不懂他說的話。
隻顧難地呢喃,“好難,快給我開心。”
得不到想要的答案,霍衍不肯罷休。
他半哄半地說,“說你我,我就給你開心。”
說他就給開心?
俞晚立馬如他所願地說,“嗯,你。”
態度很是敷衍。
霍衍不滿意俞晚的態度,他又重新說了遍,“說俞晚霍衍。”
的空虛迫使俞晚本能地迎合霍衍的喜好,吐氣如蘭地說道,“俞晚霍衍。”
“對,俞晚霍衍。”
霍衍就像是一個被刺激的野馬,忽然就發起了狠來。
他的狂野刺激到了俞晚,俞晚如貓的聲音驀地口而出。
忽然聽到一聲到骨子裏的聲。
門外的趙子裕哆嗦了一下,嚇得跑出了好幾米遠。
房間裏。
霍衍大概是意識到俞晚得太大聲,他抬手捂住了的,作卻並沒有因此緩慢下來。
俞晚中的藥遠比霍衍以為的還要難解。
他本以為一次就能搞定了。
可他剛結束不到一分鍾,俞晚就像是那懾人魄的小妖,立馬又纏了上來。
霍衍顧不上氣,連忙又繼續與糾纏。
最後快天亮的時候,霍衍才終於讓俞晚昏昏沉沉地睡去。
忙活了一晚上,霍衍也累,也困。
但他睡不著。
明明得到了巨大的滿足。
他也得到了許久未曾有過的快。
可為什麽。
他卻覺得空虛得厲害。
明明俞晚此時就在他懷裏,可他卻覺自己離好遠。
即便他剛剛哄著俞晚說了很多句他。
他還是覺得心裏空的。
許是因為他知道,那句俞晚霍衍不是俞晚本人想說的。
隻是迫於自己的威,不得不迎合自己才說的而已。
Advertisement
俞晚霍衍。
這五個字,他此生怕是再也無法聽俞晚真心實意的說了。
曾經唾手可得的甜言語,如今竟然得靠著這種方式,才能聽到。
他可真夠悲哀的。
霍衍自嘲地勾了勾,神很是落寞。
腰腹下方作痛,霍衍約猜到自己好不容易愈合的肋骨又裂開了。
醫生說過他三個月不能劇烈運的。
如今一個月不到。
不,半個月都沒到。
他不僅運了,他還負荷運。
明日估又得去一趟醫院。
這裏到底不是私人住所。
霍衍實在是忍不了讓俞晚在這過夜。
起來將服穿好,然後又將俞晚的服給套上。
然後抱著走出了房間。
不遠的走廊上。
趙子裕蹲在那。
他聽了一夜的牆角,整個心又酸又。
要命的是,蹲了一夜。
他腳麻了!
見霍衍抱著俞晚,額頭都滲出細汗,好像很吃力的樣子,腳麻需要靠扶著牆壁才勉強站起來的趙子裕忍不住賤地說了句,“霍哥,不是吧,才一夜而已,你就虛了?”
霍衍直接冷冷地瞪了他一眼,“你要是覺得北城的空氣不好,我不介意讓你到奧洲去。”
趙子裕哆嗦了一下,尬笑,“不了,北城空氣好的。”
霍衍看都不看他一眼,直接抱著俞晚往外走。
趙子裕連忙跟上。
回去的路上,趙子裕鬱悶地問霍衍,“好端端的,俞晚怎麽會出現這裏?”
霍衍低眸看著懷裏閉著眼,睡得很沉的俞晚,並沒有回話。
他也想知道為什麽會出現在這種場合。
趙子裕見霍衍沉默不答,索也沒有再多言,他專心開車。
-
當霍衍抱著俞晚回來時,許君羨正好從對門出來。
因為俞晚出門前,特意將許君羨給的那條有定位追蹤的項鏈解了下來,所以許君羨並不知道俞晚昨晚出去了,而且還一夜未歸。
Advertisement
此時看到霍衍抱著俞晚回來,而且兩人裳都不算端正,尤其是俞晚脖頸上,還有著可疑的痕跡。
許君羨瞇了瞇眼,眼底升起了莫大的寒意。
許是因為顧及霍衍懷裏的俞晚,許君羨忍著脾氣未怒,他隻是一言不發地看著霍衍將俞晚抱進公寓,而抬腳跟了進去。
許君羨在霍衍將俞晚放下來後,無意間看清俞晚脖頸上的痕跡是吻痕時,他才氣得揮拳朝霍衍揮了過去。
“混蛋,你對晚兒做了什麽!”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連載757 章

婚期365天(慕淺霍靳西)
(此書已斷更,請觀看本站另一本同名書籍)——————————————————————————————————————————————————————————————————————————————————————————————————————————————————————————————————慕淺十歲那年被帶到了霍家,她是孤苦無依的霍家養女,所以隻能小心翼翼的藏著自己的心思。從她愛上霍靳西的那一刻起,她的情緒,她的心跳,就再也沒有為任何一個男人跳動過。
133.4萬字8 22440 -
完結1376 章

萌寶集結令,爹地快來寵
她被人陷害,稀里糊涂的爬上了他的床,不僅失身,還被人搶了兒子! 五年后,許方寧帶著三個同款萌寶,強勢回國,當年的陰謀慢慢被揭開。 除了找回被搶走的娃,她還意外發現,孩子們的爹不光帥的逆天,而且還權勢滔天。 許方寧:孩子還我,你可以走了! 唐謹言冷冷勾起嘴角,一把將身前人抱起:“先生個女兒再說!”
254.3萬字8.18 17924 -
連載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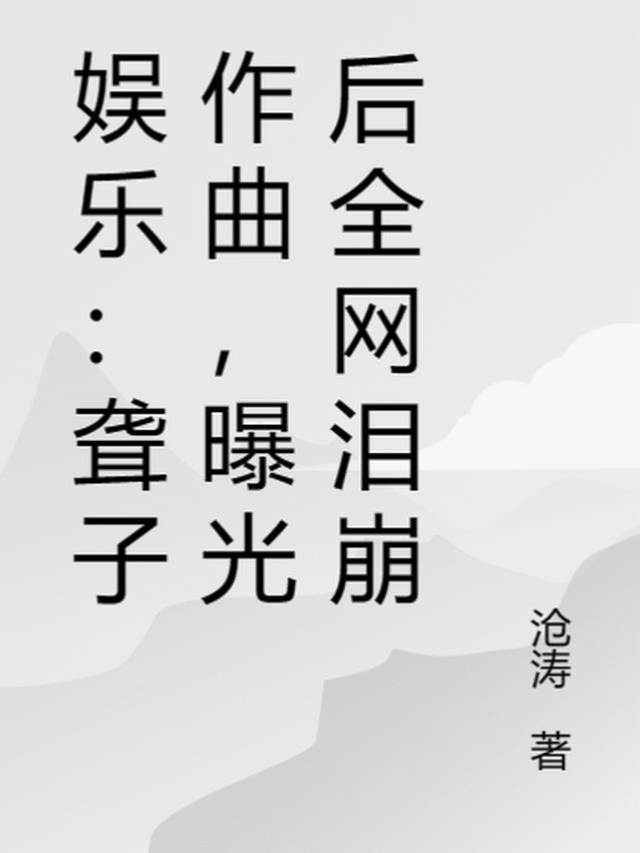
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
微風小說網提供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在線閱讀,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由滄濤創作,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最新章節及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目錄在線無彈窗閱讀,看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就上微風小說網。
23.8萬字8.18 5622 -
完結483 章

豪門盛婚:總裁老公太會撩
權傾京城的薄以澤,在雨夜里撿了一位薄太太回家。“薄先生這麼缺女人嗎?” “我缺薄太太,不缺女人。” 人人都羨慕她命好,剛從顏家千金的位置跌落,轉眼就被安上薄太太的頭銜,三媒六聘,風光大嫁。 薄以澤說,他的妻子可以在京城橫著走,顏一晴信了。 薄以澤還說,他愛她,顏一晴也信了。 后來,她死了,他不信,挖墳刨碑,死要見尸。 多年后,小團子指著英俊挺拔的男人:“麻麻,那是爹地嗎?”
78.1萬字8 1061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