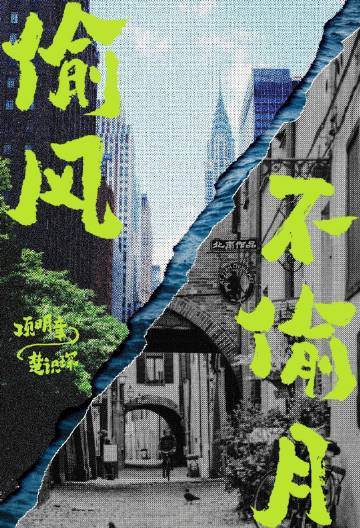《言歡》 第 103 章 紀丞
拉完鉤了,岑鳶這才放心,哽咽了幾聲,還不忘問他:“你們學校封閉訓練也可以出來嗎?”
紀丞替眼淚:“不可以。”
一直哭,眼淚怎麼也不完,紀丞干脆就先不了,等哭完。
岑鳶哭了很久,哭累了,就不哭了。
接過紀丞手里的紙巾,自己把臉上的淚水干:“那你請假了嗎?”
紀丞搖頭:“我翻墻跑出來的。”
校的圍墻有兩米多高,岑鳶想象不到他是怎麼翻出來的。但想到他的高,似乎也不難。
岑鳶又開始訓他了,責怪他總是胡來。
學校因為他是名列前茅的優等生,所以一再的放寬對他的束縛,給他開綠燈。
但這也不代表他可以一直胡來,容忍到底是有限的。
紀丞從書包里拿出一盒草莓牛,拆開吸管,扎破錫紙封口遞給:“我說了,我不怕被罰,也不怕被開除。”
岑鳶沒接,還有點生氣,氣紀丞做事不顧后果:“那你怕什麼?”
紀丞的眼睛很好看,他不近視,眼里有,尤其是看岑鳶的時候。
真誠,又認真。
現在的他就是用這種眼神在看岑鳶,他說:“怕岑鳶哭。”
----
紀丞在醫院陪了岑鳶一晚上,有在,岑鳶就不會害怕。
也不需要害怕。
從小到大,遇到的風風雨雨,都是紀丞替擋下的。
他有時候是一座山,有時候是一把傘。
渺小或者偉大,都是岑鳶的英雄。
睡覺的時候,紀丞就在旁邊陪。
岑鳶睡的太沉了,甚至連張存琳來了也不知道。
還是醒了以后,沒看到紀丞。周悠然告訴:“你張阿姨過來送飯,正好看到紀丞那孩子,氣的揪著他的耳朵把他趕去學校了。”
Advertisement
岑鳶大概能想象到那樣的畫面。
紀丞不聽話,一直都不聽話,紀叔叔因為工作的原因,很在家里。
紀丞算是張阿姨獨自帶大的,再溫的子也被他的叛逆磨的日漸暴躁。
周悠然回想起剛才的場景了,無奈的笑了笑:“紀丞那孩子別的都好,就是玩心大了點。”
岑鳶沒說話,給倒了半杯熱水,又注冷水兌溫,然后才端給。大風小說
周悠然喝完以后,也開始催促:“我已經沒事了,你先去學校吧,已經耽誤這麼久了,不能再不去了。”
岑鳶點了點頭,走過去收拾書包:“那我放學了再來看你。”
周悠然說:“在學校專心上課,不用擔心我,我沒事的。”
岑鳶:“嗯,知道了。”
昨天一整天沒來學校,進教室前,班主任看了一眼,沒說話,照常上課。
下課以后才把去辦公室,單獨詢問的況,為什麼昨天沒來學校。
岑鳶說明了自己家里的況,并和班主任道歉。
班主任并沒想過要罰,岑鳶雖然績一般,但很聽話,這也是為什麼周冽提出讓當副班長時,自己沒反對的原因。
他安了岑鳶幾句,讓別多想,這些天首要的任務就是期末考試。
這次的考試事關到高二的分班。
如果能分到重點班,肯定對績提升有幫助。
說完這些他就讓岑鳶回班了。
剛從辦公室出來,就看到了站在外面的周冽。
從班主任把岑鳶進辦公室以后他就一直等在這里。
沒和學校請假,忘記了。
周冽給家里打電話也沒人接,岑鳶沒有手機,他聯系不到。
一整天都很擔心。
還好今天來了。
Advertisement
剛剛無意中聽到和班主任的對話,他才知道家里發生了這樣的事。
他擔憂的問:“阿姨還好吧?”
岑鳶點頭:“好多了。”
繞過他離開,周冽跟上去,他沉了很久,最終還是鼓起勇氣開了口:“岑鳶,你以后遇到困難了,都可以跟我講的,不管是學習上的還是生活中的。”
他漲紅了臉,好像這一件十分難以啟齒的事。
對于三好學生的他來說,這已經是他做過最越界的事了。
岑鳶深看了他一眼,聽明白他話里的意思。
語氣稍微緩和了些,至不像從前那麼冷淡了。
但說出的話,卻字字誅心:“謝謝你,但不需要。”
周冽愣在那里,看著轉離開的影。過了很久很久,他才無聲走向男廁所。
那次之后,周冽沒有再煩岑鳶了。
岑鳶也落了個清凈。同桌是數學課代表,偏科雖然嚴重,但數學這門績一直都是全校第一。
偶爾會給岑鳶補補課,但岑鳶腦子笨,很多題目得講很多遍才能聽懂。
岑鳶很努力的在學習,從小耳濡目染接到的事和讓知道,窮人只有讀書這一條路。
不然的會,只有一個下場。
看著大街上游的那些人。
頭發染的五六,上穿的服也是松松垮垮的,外套拉鏈沒拉,子的很低。
這麼冷的天,腳踝還了半截在外面。
下車的時候天還是的,走了兩步就開始下雨。
岑鳶沒帶傘,只能先站著躲會雨。
旁邊是賣魚的小攤位,老板正低著頭在看書,新華字典那麼厚,約可以看見書脊上的修真字眼。
盆里死了幾條魚,腥臭味有點刺鼻,風一吹,熏眼睛。
Advertisement
岑鳶站在那里發呆,什麼也沒想。
上穿的是高中的校服,寬寬大大也能看出的清瘦纖細。
簡單的高馬尾,白皙的天鵝頸修長,哪怕只是安靜的站在那里,仍舊的挪不開視線。
未施黛的清純往往是最能讓人記住的。
那幾個游手好閑的小混混走過來,問要不要一起去冰。
“前面開了個溜冰場,哥哥帶你去玩會啊。”
他應該煙,而且煙癮很重,笑起來的時候,牙齒是不健康的黃。
岑鳶覺得他上的味道甚至比這魚塘里的腥臭還讓人難以忍。
想吐。
也不顧雨還在下,繞過他們離開了。
那群人卻不依不饒,跟了過來:“有什麼好害的,不會我們可以教你啊。”
“對啊,不想溜冰我們去上網,QQ炫舞你玩嗎,我紫鉆六級。”
“高幾的,看你這發育,高一吧?”
岑鳶越走越快,看到醫院了,一路跑過去的。
手都在抖。
那群人經常在看見,太顯眼了,想不注意到都難。
整天在街上游手好閑的。
聽周楚楚說,他們中某個人在附近的人里面加了隔壁班一個生,兩個人每天在QQ里聊天。
前些日子那個生沒回宿舍,好像是被那個男生騎托車接走了,一晚上沒回來。
岑鳶不是一個喜歡打聽別人私事的人,但周楚楚的話卻讓在意。
“聽說那個生回來以后上全是傷,每天晚上都在宿舍哭,問發生了什麼也不肯說。”
岑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但肯定不是太好的事。
偏僻的地方,文化程度普遍都不高。
窮山惡水出刁民,這話一點也不假。
醫院有點冷,岑鳶把書包里的外套拿出來穿上。
Advertisement
這是紀丞昨天給的,他今天走的時候也忘了拿,岑鳶原本打算洗干凈了,等下次看到他的時候再還給他的。
因為害怕,所以一路跑進的醫院,想快點甩開那群人。
以至于現在還在氣。
周悠然看見了,臉擔憂的問:“怎麼回事,的這麼厲害。”
因為跑的太急,都有點泛白了。
紀丞的服穿在上太大了,把袖子往上卷了幾截,才出自己的手。
說:“下雨了,我又沒帶傘,所以就跑過來了。”
周悠然忙問:“淋了沒,別又冒了。”
岑鳶笑道:“沒呢,我跑的快,雨淋不到我。”
周悠然看見臉上的笑,這才稍微放下心。
看向窗外,雨好像停了,天空沉沉的,能看見的地方都是一片抑的灰。
嘆了口氣,又將目收回。
岑鳶乖巧的坐在椅子上,認真的看著那些藥的說明書。
周悠然有時候覺得自己很沒用,岑鳶明明還這麼小,卻不得不替一起承擔家里的困難。
像這麼大的孩子只需要為了自己的績而煩惱,可卻過早的就開始直面貧窮帶來的悲哀。
這次住院,不知道又花了多錢,以后每個月還得復查,又將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岑鳶為了替家里減輕負擔,每次放假都會出去打工做兼職。
這些周悠然都知道,同樣的,也知道,自己再怎麼勸,岑鳶只會口頭上答應。
還是會去。
很懂事,但周悠然卻不希懂事。
應該有自己的年的。
醫生的建議是希周悠然再多住幾天,這樣也好觀察病的后續發展。
周悠然卻心疼這一天幾百的住院費,無論如何都要出院。
出院那天,岑鳶過來接,周悠然走路還不是很順當,得岑鳶扶著。
們下了公車以后還得走上很長一段路。
鄉下都睡得早,六點以后就不在外面活了。
家家戶戶關上門,只能過那扇窄窗看見里面的。
偶爾會有蟲鳴犬吠的聲音大破寂靜。
岑鳶扶著周悠然,緩慢的往前走。又抬頭看天,漆黑一片,沒有星星。
突然很想知道,未來的自己,會變什麼樣的人。
讓媽媽過上好日子了嗎,脾氣有稍微變好一點嗎。
還有,應該嫁給自己喜歡的人了吧。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816 章
傅先生,別來無恙
"三年前她九死一生的從產房出來,扔下剛出生的兒子和一紙離婚協議黯然離開,三年後薄情前夫帶著軟糯萌寶找上門……傅雲深:"放你任性了三年,也該鬧夠了,晚晚,你該回來了!"慕安晚冷笑,關門……"媽咪,你是不是不喜歡我!"軟糯萌寶拽著她的袖子可憐兮兮的擠著眼淚,慕安晚握著門把手的手一鬆……*整個江城的人都道盛景總裁傅雲深被一個女人勾的瘋魔了,不僅替她養兒子,還為了她將未婚妻的父親送進了監獄。流言蜚語,議論紛紛,傅大總裁巋然不動,那一向清冷的眸裡在看向女人的背影時帶著化不開的柔情。"晚晚,你儘管向前走,我會為你斬掉前方所有的荊棘,為你鋪一條平平坦坦的道路,讓你一步一步走到最高處。""
152.3萬字8 29672 -
完結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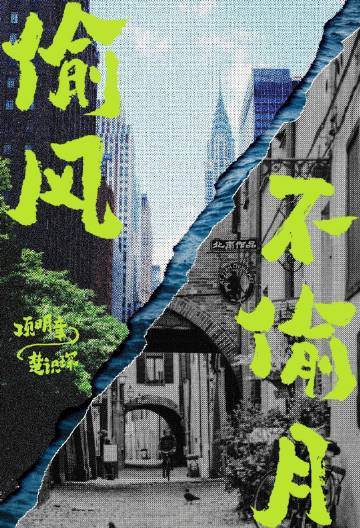
偷風不偷月
穿越(身穿),he,1v11945年春,沈若臻秘密送出最后一批抗幣,關閉復華銀行,卻在進行安全轉移時遭遇海難在徹底失去意識之前,他以為自己必死無疑……后來他聽見有人在身邊說話,貌似念了一對挽聯。沈若臻睜開眼躺在21世紀的高級病房,床邊立著一…
39.3萬字8 6359 -
完結420 章

莫少逼婚,新妻難招架
沈南喬成功嫁給了莫北丞,婚後,兩人相敬如冰。 他憎惡她,討厭她,夜不歸宿,卻又在她受人欺辱時將她護在身後,「沈南喬,你是不是有病?我給你莫家三少夫人的頭銜,是讓你頂著被這群不三不四的人欺負的?」 直到真相揭開。 莫北丞猩紅著眼睛,將她抵在陽臺的護欄上,「沈南喬,這就是你當初設計嫁給我的理由?」 這個女人,不愛他,不愛錢,不愛他的身份給她帶來的光環和便意。 他一直疑惑,為什麼要非他不嫁。 莫北丞想,自己一定是瘋了,才會在這種時候,還想聽她的解釋,聽她道歉,聽她軟軟的叫自己『三哥』。 然而,沈南喬只一臉平靜的道:「sorry,我們離婚吧」
108.5萬字8 44387 -
完結211 章

重逢大佬紅了眼,吻纏她,說情話
那年裴京墨像一場甜蜜風暴強勢攻陷了許南音的身體和心。 浪蕩不羈的豪門貴公子放下身段,寵她入骨,她亦瘋狂迷戀他。毫無預兆收到他和另一個女人的訂婚帖,她才知道自己多好騙…… 四年後再重逢,清貴俊美的男人將她壓在牆上,眼尾泛了紅,熱吻如密網落下。 許南音冷漠推開他,“我老公要來了,接我回家奶孩子。” “?”男人狠揉眉心,薄紅的唇再次欺近:“奶什麼?嗯?” 沒人相信裴京墨愛她,包括她自己。 直到那場轟動全城的求婚儀式,震撼所有人,一夜之間,他們領了證,裴公子將名下數百億資產全部轉給了她。 許南音看著手邊的紅本本和巨額財產清單,陷入沉思。 某天無意中看到他舊手機給她發的簡訊:“心肝,我快病入膏肓了,除了你,找不到解藥。你在哪裡?求你回來。”她紅了眼眶。 後來她才明白,他玩世不恭的外表下藏著多濃烈的愛和真心。 他愛了她十年,只愛她。
38.8萬字8.33 6925 -
完結105 章

被讀心后,她發瘋創飛所有人!
溫馨提示:女主真的又瘋又癲!接受不了的,切勿觀看!(全文已完結)【微搞笑+玩梗+系統+無cp+讀心術+一心求死“瘋癲”又“兇殘”女主+火葬場+發瘋文學】 她,盛清筱一心求死的擺爛少女,有朝一日即將得償所愿,卻被傻逼系統綁定,穿越進小說世界! 一絲Q死咪?是統否? 強行綁定是吧?無所謂,我會擺爛! 盛清筱決心擺爛,遠離劇情,研究自殺的101種辦法,系統卻不干了,又是開金手指讀心術,又是給她回檔! 很好! 既然如此,那大家都別活了! 果斷發瘋創飛所有人,上演現實版的皇帝登基! 后來,幡然醒悟的家人分分祈求少女不要死! 對此,盛清筱表示:關我屁事! 死局無解,救贖無用,唯有死亡! 最想活的系統綁定最想死的宿主,開局則死局! 【女主一款精神極不穩定的小瘋子,永遠不按套路出牌,隨心所欲,瘋癲至極,一心求死最終得償所愿!】 本小說是在作者精神狀態極度不穩定下所創造出來的癲文,沒有邏輯,就是癲。 *回檔很重要
19萬字8 600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