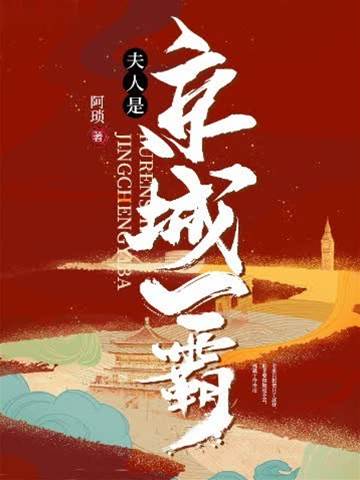《寵妃的演技大賞》 第99章 機緣 封她為繼後?
蕭韞慢吞吞道:“我也想要妹妹……”
秦婈看著他的眼神,不由想起了長寧進宮那日。
那天,他便是這樣眼目送蘇佑臨和蘇令儀離宮的。
怪不得……
怪不得這兩日他一直盯著自己的肚子打轉。
坐在一旁的男人眉宇輕提,並不言語,隻偏頭去看秦婈,似乎想聽怎麼答。
四歲的小皇子已經漸漸懂事,正是求知最旺盛的時候,秦婈沒法隨意應付他,不然即便今日應付過去,明日他還是會重提。
秦婈思忖片刻,忽然覺得凌雲道長的話,用在此刻甚好,便聲道:“韞兒,這事阿娘沒法答應你,妹妹……這是要等機緣的。”
“妹妹”這兩個字,已小皇子的腦袋瓜裡嗡嗡作響多日,蕭韞拉住秦婈的角,認真道:“母妃,那我該怎麼做?還要等多久……”
蕭聿角帶了點笑,一把將兒子抱起來。
蕭韞坐在父皇的手臂上,低聲道:“父皇……”
蕭聿道:“朕答應你便是。”
在小皇子眼裡,他的父皇無所不能,父皇答應了,他的妹妹便有著落了。
蕭韞角也帶了笑,道:“多謝父皇!”
秦婈看著表一樣,又一唱一和的兩人,下意識捂住了自己被盯上的肚子。
蕭聿偏頭對袁嬤嬤道:“眼下何時了?”
袁嬤嬤道:“戌時三刻。”
蕭韞立馬接話:“兒臣這就跟嬤嬤去淨室洗漱。”
蕭聿把他放下,袁嬤嬤忍笑牽起小皇子的手。
得了承諾,兩條小短,心滿意足地離開了殿。
如今景仁宮史的眼不是一般的好,燭火一燃,立馬匐而去。
蕭聿坐回到邊,用手去纏繞的發,呼吸瞬間近了。
秦婈偏頭問他,“陛下喝藥了嗎?”
Advertisement
蕭聿點頭,胡地“嗯”了一聲,隨後便自己手解了腰封,裳接連落在帳外。
事實證明,這男人對於生孩子的過程,總是熱又積極。
夜風浮,芙蓉帳暖。
他手替秦婈卸下金釵,烏黑的長發散落下來,襯的愈發瑩白嬈,纖長筆直的落在男人手裡,彎了心的弧度。
他俯去親,輕輕又淺淺,指腹來回試探。
帳中雖無語,但在這事上,他從不對來,與彤冊上一筆一劃記錄的秦昭儀侍寢不同,蕭聿待,一向與尋常夫妻無異。
疼了他會停,要是哼唧,他也會笑著快些。
事畢,他還得給拿水喝。
正如此刻。
秦婈握著杯盞,眼睛霧蒙蒙地看著他,“我想去沐浴。”
蕭聿從手中接過空杯盞,放到一旁,回頭認真道:“不是說好了要個兒,等會再去。”
秦婈忍著黏膩,失力般地躺回去,蕭聿用手掐了掐的腰,湊過去,輕啄的耳垂。
秦婈以為他還要再來,立馬躲開,抬起手,滿眼防備地抵住了他的膛。
“不要了。”小聲說。
他目灼灼地看著,就跟看不夠似的,但上卻故意笑道:“你想什麼呢?”
男人的壞心思顯而易見,秦婈懶得理他,乾脆閉上了眼睛。
良久之後,他將打橫抱起去了淨室。
人被他圈在懷裡,相,秦婈的手剛好在他口的疤痕上,凹凸不平的讓緩緩睜開了眼,看了好一會兒……
在淨室折騰了好半晌才折返。
熄燈上榻,四周陷一片漆黑。
秦婈抬起手,的指腹過大小不一的疤痕,輕聲道:“陛下是因為這些舊傷,才喝的那些藥?”
Advertisement
輕的語氣耳,蕭聿子一僵,結跟著滾,“是,也不是。”
秦婈看他,疑道:“這是什麼話?”
蕭聿輕聲道:“帶兵打仗的人上哪有沒傷的,但你也知道太醫院那些人,向來喜歡誇大其詞,我喝那些藥,無非是為了耳子清淨。”
太醫院那些人,秦婈心裡也有數。
思忖片刻,又問道:“那逢天下雨,還會疼嗎?”
他攬過,若有若無地吻了下的發頂,“不疼。”
秦婈道:“當真?”
蕭聿正要答,就聽外面傳開一陣敲門聲——
盛公公道:“陛下,急奏。”
話音甫落,秦婈立馬坐起子。
眼下已過亥時,若無大事,以盛公公子,是絕不會影響皇帝歇息的。
蕭聿低聲道,“你歇息吧,今夜我就不回來了。”
說罷,他便披上衫離開了景仁宮。
——
陸則已在養心殿門外等候多時,腳步聲漸近,他拱手作輯,“臣見過陛下。”
蕭聿道:“禮就免了,進來說。”
走進養心殿,陸則將手中兩封急報遞了上去。
這兩封急報,一封是薛襄通過驛站遞回來的,一封是閬州總督快馬遞回京城的。
邊關軍報大過一切,蕭聿先拆了下面那封。
大概兩年前開始,蕭聿陸續往齊國安了些眼線,那些人都是商人份,雖說接不到齊國權臣,但也都有本事能打聽到一些風吹草。
齊國近來頻頻練兵,許是有意開戰。
陸則道:“這齊國還是賊心不死啊。”
蕭聿道:“這些年,到底是給了他們休養生息的機會。”
提起這些年,陸則不由道:“四年前若虧了陛下英明,退他們就撤了兵,真要是聽那些謀士話乘勝追擊,還不知會如何……”
Advertisement
陸則十分清楚,延熙元年,當皇帝把旌旗清州角樓時,大周的後備力可謂是彈盡糧絕。
那年的大周本就軍心不穩,再加之帑空虛,八萬戰兵行不到一月便需要近三十萬石糧食,是輜重自消耗就已是吃不消。
蕭聿了手上的白玉扳指,“言清,大周與齊國,遲早都有一戰。”
陸則點了點頭,“臣明白。”
若非為了這一戰,皇上不會大費周章與蒙古修好,澹臺易亦是不會存心挑唆兩國關系。
從周、齊、蒙古的地形來看。
大周在下,蒙古在中,而齊國在上。
四年前蒙古趕上政權更迭,正逢,無暇坐收漁翁之利,如今已是大有不同。周齊一旦開戰,握有草原雄兵猛將的蒙古,偏向誰就變得格外重要。
蕭聿此番在驪山救了吉達一條命,便有挾救命之恩,老可汗出兵的意思。
蕭聿看著陸則道:“近來吉達如何?”
想到吉達,陸則不由苦笑道:“陛下,那二王子傷時還算消停,這傷一好,天天拉著臣陪他喝酒,這幾日他走街串巷,臣都吐了三回了,這二王子是個中人,提起齊國此番行徑,也是恨之骨。”
他堂堂錦衛指揮使,都已淪落了陪酒的小?
蕭聿又道:“他們打算何時返回蒙古?”
“十日後。”陸則輕咳一聲道。
蕭聿道:“盛康海。”
盛公公匐走過來,道:“奴才在。”
蕭聿道:“立即派人道與鴻臚寺、祿寺,準備給二王子設宴送行。”
盛公公道:“奴才領命,這就吩咐下去。”
蕭聿著急報,掂了掂,與陸則又道:“時已秋,就算齊國想起兵,最快也得是秋末,北地苦寒,這場仗不會比四年前容易,步兵的棉服,也該提前預備了。”
Advertisement
陸則道:“陛下準備調遣何的兵力?”
這些年,皇權與世家劍拔弩張,朝堂上文的烏紗帽換了一批又一批,但武卻仍是四年前的那些人。
老的老、的、不中用的不中用。
也就閬州、禹州兩個總督還算是可用,但齊國將領用兵詭詐,方恕為人魯莽,何子宸又未與之過手……
陸則見皇帝沉默,心裡咯噔一聲,道:“陛下莫不是還想親征?”
蕭聿低頭了下鼻梁,“此事再議。”
說罷,蕭聿拆開了薛襄的函,裡面羅列著楚家私運的罪證。
刑部尚書親自去戌州查證,自然人證證俱全。
默了許久,蕭聿才道:“你繼續盯著楚盧偉,切勿打草驚蛇。”
“是。”
——
秋的幾場大雨,令楚太后的病越發嚴重。
太醫院整日往慈寧宮跑,誰都不能眼瞎當瞧不見。
蕭聿一連去慈寧宮請安七日。
皇帝給了態度,楚太后那震天的咳嗽聲才弱了下去。
章公公笑著道:“要奴才說,太后娘娘之前實在是多慮了,娘娘待陛下如親子,陛下怎可能不念仁孝二字。”
楚太后著手中的佛珠,嗤笑,“仁孝,他若真仁孝,四年前就該讓瀠姐兒宮,他防著楚家,這是與哀家隔著心呢。”
提及自個兒的侄,楚太后不由深吸一口氣。
楚瀠從十二歲,等蕭聿等到了十九歲。
眼下太子已立,這懸著的後位,只怕皇帝心裡也早有打算。
一個區區五品小吏之,不到一年的功夫,轉眼了承恩伯府的長。
這是真要封為繼後不?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連載337 章

獵戶農妻寵上癮
一覺醒來,竟成了古代某山村的惡臭毒婦,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就算了,還被扣上了勾搭野漢子的帽子,這如何能忍? 好在有醫術傍身,於是,穿越而來的她扮豬吃虎,走上了惡鬥極品,開鋪種田帶領全家脫貧致富的道路。當然更少不了美容塑身,抱得良人歸。 隻是某一天,忽然得知,整日跟在身後的丈夫,竟是朝廷當紅的大將軍……
58.4萬字8 5668 -
完結7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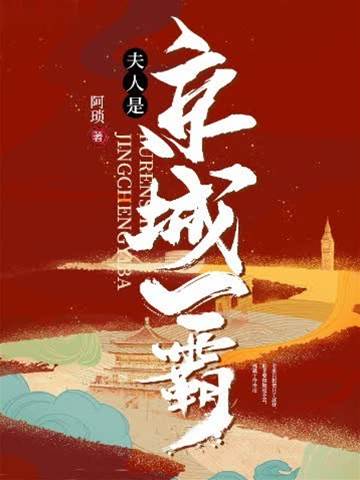
夫人是京城一霸
七姜只想把日子過好,誰非要和她過不去,那就十倍奉還…
123.2萬字8 19066 -
完結808 章

毒妃禍國不殃民
偶買噶,穿越成了惡毒女配?還作天作地作得人神共憤犯在了超級渣男手上! 好吧,既然擔了惡毒的名頭,她蘇陌涵就讓那些渣渣好好看看,什麼叫做“最毒婦人心!” 管她什麼白蓮,圣母還是綠茶,她蘇陌涵沒二話,就是一個字,干! 至于渣男嘛!嘿嘿,還是只有一個字,干!
173.5萬字8 19998 -
完結2428 章

農家娘子致富記
穿越到惡毒倒霉的肥婆身上,明九娘欲哭無淚——前身想謀殺親夫卻作死了自己……醒來時家徒四壁,兒子面黃肌瘦,相公蕭鐵策恨她入骨。 別人穿越懂醫懂葯懂軍火,她懂個鳥……語。 擼起袖子加油干,發家致富奔小康,相夫教子做誥命! 蕭鐵策:為了殿下,熬過這一次……這個毒婦總想攻略我,我抵死不從……從了從了,我給娘子暖被窩!
225.6萬字8.33 452725 -
完結185 章

權相養妻日常
重回豆蔻年少,令容只求美食为伴,安稳度日。 谁知一道圣旨颁下,竟将她赐婚给了韩蛰。 听到消息的令容狠狠打了个哆嗦。 韩蛰这人心狠手辣,冷面无情,前世谋朝篡位当了皇帝,野心勃勃。造反前还曾“克死”两位未过门的妻子,在令容看来,其中必有猫腻。 婚后令容小心翼翼躲着他,不敢乱戳老虎鼻。 直到韩蛰将她困在床榻角落,沉声问道:“为何躲着我?” 禁欲厨神相爷X吃货美娇娘,女主只负责美美美,架空勿考 前世所嫁非人,这辈子1V1;部分设定参考晚唐,男十五女十三听婚嫁,介意慎入哈
51.6萬字8.25 19300 -
完結258 章

抄家流放后,我搬空了敵人的庫房
【種田】+【流放】+【基建】+【雙潔】+【架空】開局穿成丞相府不受寵的嫡女,還是在新婚夜就被抄家的王妃。溫阮阮:我要逃!!!帶著我的空間先收王府的庫房,再去渣爹的府上逛一逛,順便去皇宮收一收,給皇帝和渣爹送份大禮。流放就流放吧,一路上順便罵渣爹,懟白蓮,好不樂哉。等到了蠻荒之地,再和自己的便宜夫君和離,逍遙自在去!“王爺,王妃又逃了!”“找,快去找!”入夜,蕭塵淵猩紅著一雙眼,在她耳邊輕語,“阮阮,不是說好了,會一直陪著我嗎?”
45.1萬字5 4466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