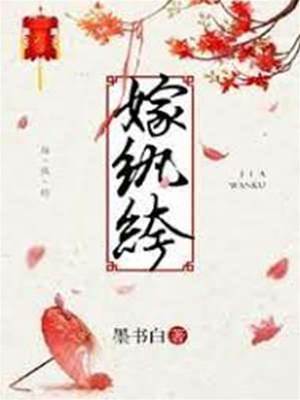《燼歡》 第96章 蔓延
自古大災之后往往有大疫,陸縉一貫謹慎,故而特意吩咐了人留心。
但事果真發生的時候,還是極為出乎人意料。
錢副將神亦是前所未有的凝重,他搖頭:“尚未。隨軍的大夫里有個資歷極老的,說癸酉年綏州曾有過一次洪水,水患過后發了時疫,溫氣疫癘,千戶滅門,那一回死了上萬人,震朝野。這一回的病癥,同那一年的瘟疫,癥狀極像。”
綏州大疫,死亡枕藉,十室九空,鼎鼎大名,陸縉自然聽過。
如今戰未平,再加上時疫,本就的西南怕是要淪為人間煉獄了。
陸縉緩緩負手,眉梢冷峭:“有多人出現癥狀了,是何表現?”
“前日大約五六個,昨日增了一倍,今日已經有二十多,皆是先干咳,后高熱,持續不退,直把人燒的四肢搐,昏厥不醒。胡大夫說,這癥狀看起來比之當年的綏州還要嚴重。錢副將越說,心里越沒底,“恐怕不容樂觀。”
“知道了。”陸縉沉聲,眉間卻微微蹙著,語氣低沉,“偏在這個節骨眼上。”
如今,他們大軍境,只等著天回暖,雪化之后便大舉攻山,收拾殘局。
“除了營地,別的地方可曾有類似的消息?陸縉抬了下眼。
“現在派人去打聽打聽,尤其綏州州城和周邊幾個州。陸縉吩咐。
說完,又補了句:“勿要張揚,以免搖軍心。”
暫時代完之后,陸縉又道:“你先去外面守著,我換裳,待會兒一起去看看。”
“局勢尚不明,您親自去,恐會有危險,要不”錢副將試圖勸諫。
“無妨。”陸縉打斷,“事關重大,我親自過去。”
“是。”錢副將便只好暫且出去,退后時,風拂簾子,他約看到了簾后地上堆著一件鵝黃的衫,分明是子的。
Advertisement
他眼皮跳了下,狀似不知地掀了帳子出去。
陸縉摁了下眉心,也快步回了簾后,拿起搭在架子上的外,一件件穿好。
江晚半跪在榻邊,替他扣著腰帶。
服穿好的時候,陸縉握著江晚的肩將人放倒,掖好了被角:“你先睡,我去看看。
江晚不肯,爬起來:“我同你一起去。”
“別鬧,外邊恐是瘟疫,不可小覷。”
江晚卻又抱上他手臂:“我知道,所以才要去。”
并未遲疑,抬眼看向陸縉,將知道的一切和盤托出:“其實,當年,哥哥曾與我說過,他母親當年便是積勞疾,死于當時的一場瘟疫,我曾經也親眼見過那場瘟疫,你讓我去看看,說不定我能幫上忙。”
當聽到裴絮當年是死于瘟疫時,陸縉一頓,猜疑又加重三分。
但神仍是沒半分松,只江晚發頂:“知道了,你躺下,瘟疫會傳人,此事與你無關。”
江晚卻搖頭:“若真是瘟疫,遲早是免不了的,我遠遠的看一眼,嗎?”
“不許去。”
陸縉一貫縱著,這回卻無論如何不許,直接吹滅了燈。
“先睡,等我回來。”
江晚手去拉,卻只扯到了一片角,眼底落寞,只好又躺下。
前前后后不到一刻鐘,此刻,收容傷兵的營帳里已經人心惶惶。
有個本就斷了一條的士兵不巧也患了疫癥,高燒驚厥,驟然猝死過去,死前噴了一大口,濺的帳子上猩紅一片帳瞬間大。
出現癥狀的士卒,蜷著子直哆嗦。
尚未出現癥狀的,發了瘋似的在帳前,嚷著要出去。
“死人了!”
“我沒病,快放我出去!”
“這是瘟疫!”
Advertisement
“退后!”
守在帳子前的士兵大喝,長矛一錯,死死地擋住門。
卻反倒激的里面的人反應愈發激烈。
眼看要起手來時,錢副將陪著一玄勁裝的陸縉一同到了帳前。
看見,錢副將立即斷喝一聲:你們這什麼做什麼,反了不?”
幾個士卒看見錢副將,又看見陸縉親自來了,趕跪下:“將軍,我們不想死!
陸縉掃視一圈,正看見那暴斃的士卒和帳上飛濺的,面愈發凝重。
聲音卻仍是鎮定。
他抬手制住如臨大敵的守衛,上前一步:“病因仍在查,你們不必憂心,無論是與否,我皆會給你們一個代。”
這三月來,這些人跟著陸縉一路攻城拔寨,勢如破竹,自然明白他一貫說到做到。
幾個人聞言原本躁的緒慢慢平復下來,只跪地應是。
又走了幾個帳子,安完患病的士卒,陸縉掃了一眼那病死的人,命人抬起去就地火化。
而后,令人用石灰將帳子徹底消殺一遍,又吩咐周圍的營帳撤離,暫時將這群患病之人與普通士卒隔開。
隨行的醫一看陸縉利落又直接的做法,便明白他是個有經驗的,上前遞上了用紗布制的面罩。
“將軍,據卑職觀測,此病大約是經由飛沫相傳,需覆面方能隔絕。”
好。陸縉接過后,又令人連夜趕制,分發三軍。
軍中尋常的補給還算充裕,但布匹并不,剛好林氏開的是布行,除了捐贈春,又另外送了幾十匹紗布來,剛好派上了用場。
也算是差錯了。
“確認是疫癥麼?”陸縉一貫謹慎。
胡大夫忙拱手:“隨行的醫皆是從上京來的,鮮接疫病,先前老夫還憂心是否是誤診,但剛剛又找了幾個當年經歷過綏州大疫的人,他們皆說這病癥同當初相像,且這病傳人如此之快,多半是差不離了。”
Advertisement
胡大夫一下定論,在場人心底皆是一沉。
果真是瘟疫,西南,怕是要大了。
既已基本確證,眼下需盡快溯源,隔斷一切。
第一個患上此病的人是誰?是如何患上的,先前他又接過那些人?
陸縉一件一件的吩咐著,命人去查。
這一查不要,沒多久,查出來的結果令人大驚失。
頭一個患病的竟是個俘虜,剛十六歲,正巧是從山上逃下來的。
胡大夫思忖道:“雖是疫癥,但總不會無緣無故的出現,西南一帶毒最是多,那群人又最是心狠手辣,不分是非,此事會否是紅蓮教義軍故意養出來的,有意在這個時候投毒,阻止咱們攻山?”
“不是無可能。”陸縉淡淡嗯一聲。
自從知道了裴絮的死法之后,他便起了猜疑。
于是便命人去問問那第一個發病的人究竟是如何逃出來的。
那士兵還是個年,燒的渾虛,勉力回想著:“當時捆著我的繩索斷了,我一路避著人,從山林里逃了回來。”
“斷了?”
天底下哪有那麼巧的事,繩索剛好斷了,剛好一路上都無人撞見,這孩子,分明是故意被放回來的。
恐怕,早在他被放回之前便被人下了毒了。
難怪,如今天已回暖,平南王又被圍,裴時序卻毫沒有異。
他分明是留了后手了。
只是瘟疫一旦蔓延開,危及的可不止是軍隊,而是整個西南,甚至全天下。
這才剛剛三日,便有人暴斃,此次瘟疫蔓延速度如此之快,發病如此洶涌,比之當年的綏州大疫還要可怖,到時恐會生靈涂炭。
胡大夫長嘆一聲:“無論如何,也不該對尋常百姓手啊。”
折騰了半夜,此時,剛剛派去附近州城探聽消息的人也收到了信鴿,說是州城一切如常,并未發現異樣。
Advertisement
如此一來,又添一分確證。
陸縉未再猶豫,迅速命人排查軍中所有出現癥狀之人,收容到癘所,與眾人隔開。
又當即了所有副將和主事的將領到了主帳。
一群人深夜被起,眼角還耷拉著。
再一聽到瘟疫,瞬間個個繃了神,分坐在營帳兩側的圈椅上。
陸縉坐在上首,命胡大夫將剛剛的來龍去脈一一告知。
“瘋了,這人簡直是瘋子!趙監軍大罵,“他這是要拉全天下陪葬啊!”
幾個副將也跟著怒斥。
江晚并未睡,當聽到外面的靜時,緩緩睜開了眼,亦是沒料到裴時序竟已淡漠到如此地步,全然視人命如草芥。
說話間,癘所那邊傳來消息,已經排查出上百個出現寒癥的人。
且又有一個患了病弱的士卒生生咳亡。
眾人聞言愈發沉重。
陸縉點了幾位醫出來:“此次的疫癥你們可有辦法?”
“這疫癥來勢洶洶,我等醫不,暫未尋到治法,只按照風寒之癥和先前綏州的方子暫時抑制,但此法治標不治本,若是沒有解藥,恐怕遲早會蔓延開。”
領頭的胡大夫面慚。
“沒有法子?趙監軍急,噌的站了起來,“可如今已經是發病的第三日了,這些人這幾日來與軍中的將士們一起同吃同住,不知接了多人,雖則目前只有二三十人有了癥狀,但實則患病之人恐怕早已不知凡幾。”
“是啊,聽聞這疫癥又是同綏州當年一樣,經由言談飛沫相傳,這可如何防的住?”
“已經得了病又該如何是好?就地焚燒?”
“如今咱們大軍有三萬之眾,是山腳下,便駐扎了五千,軍中集,一旦蔓延開,后果恐怕不堪設想。”
“正是,我看到時莫說是攻山,只怕倒下的先是咱們了!”
“那你說如何是好,難不,都這個節骨眼了,還要退兵,正好合了他們的意?
“我何時說退兵了?”
“你分明是覺著自己年紀大了,染了病第一個要出事,貪生怕死,不肯久留罷了!”
“你”
在場人你一言我一語,議論紛紛,卻互相攻訐,沒一個人能拿出辦法。
江晚站在簾后,心里緩緩冒出一個念頭,掀開簾,過簾看了一眼,卻見陸縉神不變,只端坐著,任憑他們吵鬧。
好半晌,眾人吵的口干舌燥,天已將明的時候,陸縉著杯子,抿了一口,重重放下。
“吵完了?”
帳中瞬間安靜下來。
“都下去。”
陸縉斥道,疲倦地摁摁眉心。
此時,另有一雙的手搭到他眉上,緩緩地。
“累嗎?”
“怎麼還不睡?”陸縉按住的手。
“睡不著。”江晚環住他的頸。
陸縉沒再說什麼,搭在腰上的手一勾,攬著人坐到他膝上,將塞在江晚底的里拉出來,一手掰開膝彎,細致地了,確認上沒殘留他的味道。
“天晚了,不便沐浴,今晚先將就著睡。”
說罷,陸縉拍拍的腰,要將人抱回去。
江晚卻不肯,攥住陸縉的手:“我興許能幫到你。”
“你?”陸縉抬眼。
江晚解下了收在荷包里的玉,解釋道:“其實不久前,哥哥剛托人給我送過生辰禮。旁人他不在意,倘若我也染上了疫病,他興許,會拿出藥來。”
“我想試一試,嗎?”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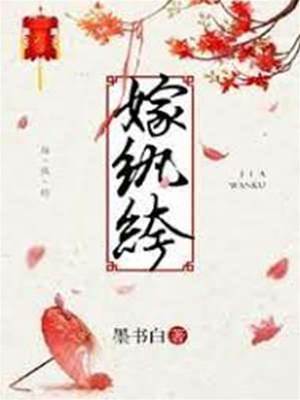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50163 -
完結1598 章
沖喜王妃:王爺有病我來治!
上一世,蘇洛被渣男挖走了心臟,被親生妹妹設計陷害全家慘死!重生后,她心灰意能不再相信任何人,嫁給了馬上要咽氣的病弱王爺。本想等他死了好繼承遺產保護家人,讓那些傷害她的人付出代價。可這位病入膏肓的王爺到了時間,居然還不死……這下好了,不僅僅要照顧病秧子,還得賺銀子給他看病,說好的繼承遺產變成了倒貼嫁妝。直到有一天,仇人找上門來,病懨懨的王爺將她護在身后,佛擋殺佛,神擋殺神!她才知道,身邊睡著的哪里是個病秧子,分明是一只扮豬吃老虎的腹黑大魔王。聞人陌摟著蘇洛,將那些傷害過她的人都踩在腳底,邪魅的在...
176.4萬字8 4279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