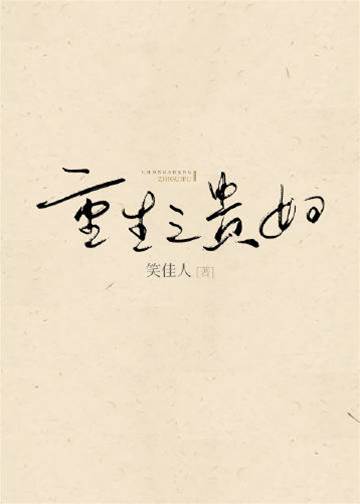《燼歡》 第53章 收拾
一個極度潔的人被吐了一。
這比給了一刀, 還讓陸縉難。
教養使然,他沒對江晚做什麼。
一抬眸,眼底滿是山雨來的沉。
“吐完了?”
聲音寒浸浸的。
江晚著心口, 被他的冷臉一瞥,張著開口, 一, 心口又涌上來一反胃。
陸縉發覺不妙, 立即制止。
“行了, 你先別說話——
然“話”字剛說到一半。
手臂上又是一熱。
比剛剛還熱。
那一刻, 陸縉把右手砍了的心都有了。
臉上皮笑不笑的:“江晚,你故意的?”
“我沒有。”
江晚蹙著眉,現在可難了。
又恥又難, 眼淚啪嗒的,一滴一滴砸到陸縉手臂上。
陸縉被燙的指尖一蜷。
再往茅屋里看了看,只見那對老夫婦也著眉。
雖不像江晚這麼嚴重,但大約也不太舒服,忍了忍,他到底還是沒對江晚說重話, 只命道:“趕, 吐完我去里面看看。”
說罷, 他單手握著江晚的脖子擰到另一邊。
“快。”
江晚本來是極想吐的。
但這自己想吐, 和別人催吐, 完全不是一回事。
捂著心口, 干嘔了幾聲,忽然又吐不出來了。
反而眼的看著陸縉的手臂。
陸縉敏銳地發覺了的看, 手臂一繃:“你什麼意思?”
“我、我吐不出來。”
江晚誠實地道。
“你吐不出來看我做什麼?”
陸縉發覺不對。
“沒怎麼……”
江晚輕聲道, 眼神卻輕飄飄地卻覷著他的手臂。
看一眼, 捂著心口輕嘔一聲。
“你該不會……”陸縉凜了凜眉,“該不會還想吐我手上?”
Advertisement
江晚不說話,但眼里分明寫滿了兩個字。
沒、錯。
“還敢?你把我的手臂當是潲水桶了,一看見就想吐?”
“我也不想的,可是……”江晚小聲辯白,“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急的可憐的,鼻尖都紅了。
陸縉深吸一口氣。
這一瞬間腦中百般掙扎。
一邊是江晚的淚眼,一邊是已經救不回的手臂。
吐一回,和吐十回也沒區別。
他閉了閉眼,將石化的右臂遞了過去。
“吐吧,趕。”
“真、真的?”江晚抬頭。
“你再猶豫,就是假的了。”陸縉冷聲道。
江晚也沒再賣乖,老老實實地抱著他手臂。
陸縉閉著眼,默念清心咒。
另一只手則繞上腰帶,掌心一握,捆了整整三圈。
——防止自己控制不住,將掀出去。
然等了許久,卻沒等到悉的溫熱。
這種要殺不殺的覺,更加折磨人。
半刻后,陸縉掀了掀眼皮:“又怎麼了?”
江晚試了試自己的口:“我好像又不想吐了。”
“你……”陸縉幽幽地道,眼神惻惻的。
“不是……”江晚連忙擺手,擰著眉沉思道,“大約是沒東西吐了吧。”
“這麼說,你還憾?”
陸縉似笑非笑的,一俯,正要跟算賬。
忽然,里屋的蔣阿嬤探出了頭:“這是怎麼了?”
陸縉眉間一松,暫時將江晚撂在一邊,問兩個老人:“這菌湯似乎有毒,我家這位中毒了,腦子不大清楚,剛剛吐了我一手,阿嬤,你們怎麼樣?”
“我們沒什麼。”蔣阿嬤道,“我們吃的不多,就是有些頭暈。就是丫頭,吃的最多。”
又仔細瞧了一眼,果然發現江晚雙目遲滯,整個人仿佛被了骨頭似的,綿綿地倚在陸縉上。
Advertisement
“吐了也好,吐出來就沒什麼事了。”蔣阿嬤嘆了口氣,“都是我不好,老眼昏花了,一定是丫頭采到了毒蘑菇,沒分出來。陸郎君,你怎麼樣?”
“我暫且無事。”陸縉謝過。
他對口腹之一向克制,食量節制,且他要比他們好上許多,是以并無異樣。
蔣阿嬤瞧了瞧,確認他沒事了,便道:“家里還有幾味草藥,我去煎一煎,清一清毒。”
陸縉略通醫,甫一發現便把了江晚的脈,沒看出大問題,便猜測這菌子大約毒并不大,只是致幻的作用的大了些,又聽見他們有藥,猜測這菌子大約是常吃,解毒的方法也多,于是謝過:“勞煩阿嬤。”
“不妨事,你們給了好大一粒珠子。”蔣阿嬤比劃道,“那值不錢呢,這點活計算什麼。”
“本就是我們叨擾,應該的。”
“用不著這麼客氣,不過是添雙筷子的事。”
蔣阿嬤并不計較,拉了蔣阿公進門去幫著燒火。
他們一走,江晚了眉心,指著不遠的背影忽然道:“咦,那里怎麼有個茶壺……”
“壺”字尚未說完,陸縉一把捂住的。
蔣阿嬤約聽到江晚的聲音,回頭了一眼:“丫頭說什麼?”
“沒說什麼,使小子,想喝茶了。”陸縉淡淡道,“不必管。”
蔣阿嬤哦了一聲,沒當回事地拉了老伴一起進了草蘆。
陸縉確認他們走了,這才松開捂住江晚的手。
江晚臉憋的通紅,哀怨地瞥了陸縉一眼:“你捂著我做什麼?”
“我不捂著,你怕是要得罪人。”陸縉道。
他從前一直沒發現,江晚利的。
蔣阿嬤不過是型圓潤了些,肚子鼓了些,便將人認了大肚茶壺。
Advertisement
陸縉手將垂下來的發繞到耳朵上,又問道:“在你眼里,蔣阿公又是什麼?”
“是……”江晚微微偏著頭,回憶了一下,才道“筷子。”
的確,蔣阿公瘦的跟竹竿似的。
陸縉了的發。
不清醒是真的,卻又沒那麼不清醒。
那他呢?
陸縉輕輕笑了,接著,他又讓江晚站著別,自己到了河邊洗一洗。
河邊無人,又是夜晚,陸縉直接解了外,在水里沖了七八遍手臂。
用完一把皂角,的手臂都泛紅了才罷休。
洗完后,他低頭聞了聞,確認沒味道了,才拎著江晚回去。
這時,蔣阿嬤的藥也好了,江晚喝完藥,陸縉方帶著回房。
一進門,陸縉便將的臟掉外了下來,從窗戶里丟了出去。
接著,又倒了杯水,按著的脖子,一遍遍讓漱口。
漱了一壺水,江晚要被他破了,偏著頭一直喊疼。
陸縉方撂了帕子。
漱完口,江晚上基本已無異樣。
陸縉卻仍是過不了心里這關,端了一盆溫水,遞到面前。
“洗。”
江晚哦了一聲,乖乖的去。
此時,誤食毒菌子的另一個影響也顯了出來,頭暈乎乎的,腦子一塌糊涂。
陸縉讓洗手,直接手去扯頸后心的系帶。
陸縉原本背著,余里瞥見的作,手按住:“你做什麼?”
“你不是讓我洗?”江晚仰著頭。
“我讓你洗的是手。”陸縉了下手臂。
江晚這才放下,慢吞吞地去洗手。
慢的跟烏似的,濺的上都了。
陸縉看不下去,干脆握著的手,用皂角細細過指。
洗完手,挽著發的簪子一拔,又幫去發。
Advertisement
為了方便,陸縉手一提,直接抱了江晚坐在他膝上,帕子一搭,從后面整個包住。
江晚一頭青如瀑,如緞,又堅韌,同的子一樣。
陸縉作利落,卻細致,從上到下,一一,捋過每一發。
山里只點了一豆油燈,燭昏黃,影影綽綽。
江晚偏頭看著他的側臉,忽然手了上去,輕輕了一聲:“哥哥。”
陸縉手一頓,緩緩抬頭:“什麼哥哥?”
“不是嗎?”江晚著他廓分明的側臉,指尖流連。
陸縉只以為還昏著頭腦,又繼續幫發:“你糊涂了,你沒哥哥,只有一個弟弟。”
“不對,有的。”江晚卻固執地搖頭,“我們從小一起長大的。”
從小到大?陸縉意識到不對,手底的作慢了下來:“你從小長在哪里?”
“舅舅家啊。”江晚很自然地答道。
“不是莊子上?”陸縉又問。
“不是的,舅舅很早便把我接回去了。”
陸縉盯著的眼,約明白了過來。
原來長在舅舅家,難怪,養的這麼好。
江晚似乎也意識到了不對,收回了手:“舅舅說了,不能告訴別人的。”
“我是別人?”陸縉卻捉住指尖。
江晚盯著他的臉,眉間微微擰著,仿佛在糾結:“也不算。”
“那我是什麼?”陸縉問。
“姐1夫。”江晚答道。
“沒了?”陸縉繼續追問。
江晚著他的臉似是在辨認,糾結了好一會兒,忽然趴在了他肩上,很小聲地說了句:“夫君。”
這一聲極輕,陸縉還是聽見了。
他著的下頜,微微抬起來:“江晚,有沒有人說過,你很會撒?”
“有。”
“誰?”
“你啊。”
江晚誠實地道。
陸縉忽然笑了,著發的手緩緩往下,落到不盈一握的腰上時突然一把攥住,重重往他前一按:“你現在清醒嗎?”
江晚不控制地仰起了上。
趕,雙臂撐在陸縉肩上,又拉開半拳距離。
“清醒。”微微著眼皮。
“不對,清醒的人不會說自己清醒。”陸縉輕輕笑了一聲。
“不過,不清醒也有不清醒的好。”陸縉著下頜的手緩緩下,食指一屈,指骨掠過的修長的脖頸,停在領上,“聽聞中毒后人的記憶會錯,也就是說,今晚我對你做什麼,你明天都可能記不得。”
江晚微微著:“所以呢?”
“所以,我現在吻你,你應當也不會記得罷。”
陸縉似喟似嘆,一俯,雙臂撐在側。
江晚莫名張,眼睜睜看著他靠近,越近,連眼睛都忘了眨。
干燥的過的那一刻,陸縉扣在后腰上的手驟然抓,忽然抱著站了起來。
江晚陡然懸空,雙手攥了他的領。
“你干……”
話未說完,陸縉一低頭,封住的。
將的話,一個字,一個字反堵回去。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2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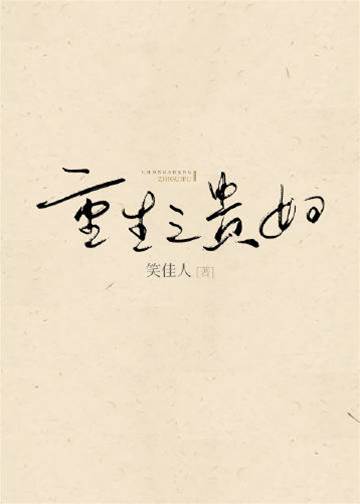
重生之貴婦
人人都夸殷蕙是貴婦命,殷蕙也的確嫁進燕王府,成了一位皇孫媳。只是她的夫君早出晚歸,很少會與她說句貼心話。殷蕙使出渾身解數想焐熱他的心,最后他帶回一個寡婦表妹,想照顧人家。殷蕙:沒門!夫君:先睡吧,明早再說。…
66.6萬字8.72 195765 -
完結263 章

表姑娘
陳家有個生父不詳的表姑娘,還和京城的煞神許嘉玄結了仇。 眾人都看表姑娘熱鬧的時候,陳家卻在為這表姑娘張羅親事。 許嘉玄表示:誰娶誰倒霉。 沒過多久,給表姑娘賜婚的圣旨就砸到他頭上。 許嘉玄:???!!! 成親前的許煞神:士可殺不可辱。 成親后的許煞神:求辱。 ””追妻火葬場系
40萬字8 18547 -
完結397 章

嫁給權臣後,女配被嬌寵了
《嫁給權臣後,女配被嬌寵了》在魏國賤民唯一一次前往上界,經受鑑鏡鑑相時,鑑鏡中出現了天地始成以來,傳說中才有的那隻絕色傾城的獨鳳,所有人都在為魏相府的三小姐歡呼,樣貌平凡的我納悶地看著手,如果沒有看錯的話,在鑑鏡從我身上掃過的那一息間,鑑鏡中的鳳凰,與我做著同一個動作……
72.5萬字8 2559 -
連載1029 章

穿成大佬黑月光,在種田文里穩定發瘋
丈夫當著你的面行兇,怎麼辦?在線等,挺急的!許寧穿成了爹不疼娘不愛還被渣男拋棄的可憐蟲,為了報復渣男,使詭計嫁給了清水村的瘸子書生。 她一睜眼,就看見她的便宜丈夫正用石頭一下一下的砸爛一個人的頭,紅白的腦漿濺了一臉。 目睹了整個過程…… 她是該裝死?還是真死? 便宜丈夫又窮又瘸又可憐,可他長的好又嘴甜……嗯……也不是不能原諒…… 面對窮的叮當響的破家,許寧擼起袖子準備大干一場,賺錢養家,治好瘸子的腿,送他去書院,然后坐等休妻。 一不下心,便宜夫君就考中了秀才,再不小心,他成了舉人,再再不小心成了皇帝欽點的探花郎,再再再再不小心,便宜夫君做了首輔…… 許寧:“喂喂喂,你到底什麼時候休妻?” 裴濯:“下輩子吧!”
143.6萬字8.18 1928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