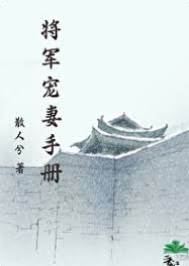《燼歡》 第52章 中毒
明明是再尋常不過的作, 但被陸縉做出來,卻有了幾分驚心魄的味道。
江晚眼神掠過他用帕子拭過的角,心思浮, 連陸縉將帕子遞給都忘了接。
“在想什麼?”陸縉問, 似乎并未覺察出的異常。
聽見他清冽的嗓音,江晚亦是覺得自己魔怔了。
抿了抿:“沒什麼, 只是想問問您, 這梨子甜嗎?”
陸縉沒說話。
他單手將頭頂上的半個黃梨擰了下來,遞到面前:“你嘗嘗不就知道了?”
那梨子只剩了半個。
江晚暈著耳,緩緩別過眼。
正要想個理由拒絕,這時候草屋里的蔣阿嬤了聲炊飯煮好了,江晚如蒙大赦, 急急地推了開。
“不嘗了,飯好了。”
說罷,連學箭也顧不上了,匆匆回去
陸縉笑了笑, 將濺到肩上的梨一點點撣了干凈。
山里不比國公府, 煮的是尋常的黍米粥,用陶碗盛著。
不算糯, 喝起來略有些扎嗓子。
江晚喝不習慣,卻知道這是他們能拿出的最好的招待的東西了。
且山里人一貫節儉,便是不習慣也不能浪費。
于是江晚還是捧著陶碗一口一口地往下咽。
一碗喝完,蔣阿嬤又熱地給添了一勺:“你病剛好,多吃點補補子。”
江晚看著蔣阿嬤的作, 言又止。
又不好拒絕旁人的熱, 糾結地秀氣的彎眉微微蹙著, 好半晌才出手。
陸縉輕易看出所想, 先一步從蔣阿嬤手中接了過來:“我沒飽,這碗我來吧。”
“哎郎君你別客氣!”蔣阿嬤道,“咱們山里沒有好東西,但這黍米粥還是供的起的,里面還多著呢。”
Advertisement
“不是,飯量小,吃不消。”陸縉語氣尋常,從容地接了江晚的碗。
這回到江晚詫異了。
那碗是吃過的啊。
陸縉這人,最是潔,他怎麼肯?
“你別……”江晚紅著臉小聲去勸。
陸縉卻按住的手,低聲道:“山里人日子苦,見不得浪費。”
江晚也沒別的辦法了,只好輕輕嗯了一聲。
眼睜睜看著他將那碗粥吃凈。
陸縉似乎完全不介意,作從容。
反倒讓江晚覺得愧,怪自己太過氣,連累了他。
吃了飯,時候還早,蔣阿嬤對江晚道:“昨晚剛下了雨,樹林里出了蘑菇,配上這雉最是鮮,小娘子你不是一直想出去走走,不如陪我去采一點?”
江晚從前只吃過,倒是沒見過這蘑菇是怎麼長出來的,頗有些好奇,便隨著一起進了山。
九亭山不高,山上多是一些櫸樹,了秋,堆了一地的落葉。
又是雨后,走起來松松的。
“這蘑菇多是長在樹,落葉底下,須得一。”
蔣阿嬤挎著個籃子手里執著一樹枝拉著。
江晚學著的模樣,果然到了一叢白蘑菇,呀了一聲:“這里好多!”
說著便手去摘,蔣阿嬤連忙制止:“小娘子,這可使不得,這是鵝膏菌,一點點就會死人的!”
“是麼。”江晚小心得了手,拿帕子了又,卻一頭霧水,“可是阿嬤,我這個,和你籃子里的有什麼不同?”
“那可多了去了!”蔣阿嬤拿起兩個一一跟解釋道,然后又叮囑,“你記住,這愈艷麗的,尤其紅的紫的,毒愈大,奇形怪狀的,也盡量不要采。若是誤食了毒蘑菇,輕的幻視,吐一通便罷了,重的可是要命的!”
Advertisement
江晚一一記著,接下來小心了許多。
采了一上午,籃子底下方鋪了淺淺的一層,然后又隨蔣阿嬤一起去林中采了些野菜一同回去。
陸縉正在替老獵戶改進弓弩和長矛,看見江晚提著籃子回來的時候,微微挑了眉:“這是你采的?”
“是啊,阿嬤說我很聰慧,學的很快。”
江晚將籃子遞給他看,頗有些邀功的意思。
陸縉見的比多,提醒道:“這山里菌子種類多,小心挑一挑,別采到毒蘑菇了。”
“阿嬤都說了沒事。”
江晚小心的將蘑菇倒在太下晾著,不以為意。
陸縉檢查了一遍,暫未看出異樣來,便由著去。
山里無事,連日子也比外面的長。
午后的日暖暖的照著,照在陸縉的側臉上,中和了他平日的冷冽之氣。
兩個人極有默契,也不覺著無聊,一下午很快便過去。
山里人只吃兩頓,睡的也早,日頭剛偏西,便要準備炊食了。
在旁人家里借宿,自然要殷勤些,陸縉便主下了廚。
江晚這幾日發現了太多從前不知的地方,當聽到陸縉下廚的時候已經不震驚了。
心想哪怕他現在說他會補天,也只會哦一聲。
只是想,陸縉的手藝恐怕這世上沒幾人嘗過,若不是因緣際會,也不能白白便宜了。
于是江晚便搬了杌子乖乖在灶臺前候著。
陸縉一回頭,便看見江晚殷切的眼。
“你來做什麼?”
拿人手,吃人短,江晚很機靈地站了起來:“我幫您打下手。”
“你?”陸縉瞥了一眼的連拉弓都能勒出紅痕的手,挑了挑眉,“老實坐著,別添。”
江晚很有些不忿,怎麼就添了?
Advertisement
但陸縉做什麼都格外有條理,連切菜都說不出的優雅,好似切的不是野菜,而是執筆潑墨一般。
江晚實在找不到手的地方,便擰著帕子,隨時替他手。
還算有眼見,陸縉無聲地笑笑,坦然地將手遞過去。
因著出好,陸縉盡管不熱衷,也很懂得吃。
山菌本就鮮,配上雉,無需太多的佐料,熬夠一個時辰,鮮味撲鼻。
連蔣阿嬤見了都直夸好。
江晚等了一下午,早已口舌生津。
這三個月來,日日被長姐過度喂食,胃口并不算好。
這幾日自從被擄走后,更是好幾日沒好好吃上一頓了。
此時,看著白的湯,捧著湯碗作雖還得,卻絕不算慢,小口小口地抿著,一碗湯很快便見了底。
“還要?”陸縉坐在旁邊。
“再來一碗。”江晚靦腆地點了頭,將空碗遞過去。
陸縉又替盛了一碗。
一直到了第三碗,江晚喝干之后,又著那咕嚕咕嚕的砂鍋。
陸縉一眼便看穿所想,提醒道:“可以了,食不過量。”
江晚留的看了眼,立馬便打消念頭,只好放下了碗,秀氣地了角。
生的好,子又乖,蔣阿嬤在一旁看著有些不忍,勸陸縉道:“你是把當囡囡養了?難得這小娘子喜歡,愿意吃就讓吃,又沒什麼大不了的。”
陸縉卻不松口:“阿嬤,您有所不知,這幾日進食太,一次吃太多容易出事。”
蔣阿嬤瞧著他年紀比江晚大了一些,是個有分寸的,便沒再勸。
江晚知道陸縉說的對,然這語氣總覺他好像在管教不懂事的兒一樣,莫名又有點恥,便坐在一旁不說話,余時不時地瞥他一眼。
Advertisement
的,有幾分委屈。
陸縉余看一眼,好似他不是夫君,而是冷無的酷吏。
三眼過后。
陸縉吃不下了,了角,瞥了江晚一眼:“你當真沒飽?”
江晚很聰明,并不直接說,反而夸他:“是你手藝太好。”
陸縉明知是在討好,卻仍十分用,到底還是松了口。
他豎起一手指,又屈了一半。
“半碗。不能更多了。”
“只有一半啊。”
江晚眼可見的失落。
“不要?那算……”
“要。”
江晚趕道,生怕連這半碗也沒了。
陸縉抿了口茶,嗯了一聲,杯下的微微勾著。
又喝了半碗,江晚終于滿足了。
但很快,就笑不出來了。
果然被陸縉料中了,吃的有點多,腹中微脹。
又不想在陸縉面前落了面子,便尋了個借口在外面繞著茅屋一圈一圈的踱步。
陸縉也沒拆穿,只站在窗邊看著,角微微勾著。
好大一會兒后,江晚忽然抱膝坐在了屋外的石階上。
陸縉沒當回事,只當是累了。
又過了一會兒,他完之后,一掀窗發覺江晚還是石像一般的坐著,一不,才意識到些許不對。
“怎麼坐在這里?”陸縉出了門,走過去問。
江晚卻沒回答,反倒偏著頭打量了他一眼,指著他的肩迷地道:“姐夫,你肩膀怎麼有小人?”
“什麼小人?”
陸縉低頭,肩上卻空無一。
他·皺眉:“你看錯了。”
“沒有錯,一排呢!”江晚又往下指了指,“手臂上也有,你看,他們正在手拉手的轉圈。”
陸縉一貫不信鬼神,但聽說的煞有其事,頗有幾分骨悚然。
沉片刻,他手試試的額:“你又燒了?”
“沒有!”江晚見他不信,偏頭躲開,有些生氣。
陸縉也沒跟計較:“不早了,回去。”
“不回去,我熱。”江晚聲音慢吞吞的。
“你坐的是石板,上面涼,不回去也不能坐著。”陸縉提醒道。
“我就要涼的。”江晚卻不肯。
陸縉以為是在鬧脾氣,沒搭理,直接上前拉了的手。
然他手剛一到的肩,江晚忽然很激靈地推了開:“你別我,我會灑出來的!”
“……你說什麼?”
陸縉倏地抬頭,以為自己聽錯了。
江晚卻很認真地重復了一遍:“你別我。我剛滿了,會灑出來。”
邊說,邊比劃了一下,手抵在眉上:“有……這麼滿。”
陸縉忽然想起一個傳聞,聽聞有人菌子中毒后會出現幻覺。
江晚剛剛吃的最多,這語氣,這胡攪蠻纏的樣子,還有那小人……
多半是了。
陸縉又仔細看了看,發覺好像是把自己認了一個杯子。
吃菌子把自己吃中毒了,可真是夠能耐的!
“江晚,你是什麼?”陸縉問。
“我是杯子啊。”江晚很坦然。
“那我是什麼?”陸縉又問。
江晚偏著頭打量了他一眼:“你是……勺子啊。”
陸縉笑了一聲。
“你笑什麼?”
江晚反倒覺得他奇怪,一個勺子竟然會笑!
“你中毒了,我不是勺子,你也不是杯子,外面冷,回去說。”
陸縉見毒的不輕,解開服替圍上。
江晚卻固執地推了開:“杯子是不用披服的。”
“不披服,你不冷?”陸縉問。
“我不冷,我是熱的。”江晚試圖跟他比劃,“我里面盛的是熱水。”
陸縉挑了挑眉:“你不走,也不披服,那是要在這里坐一整夜?”
江晚鄭重地嗯了一聲。
陸縉對付過無數棘手的事,這還是頭一回讓他束手無策的。
罵也罵不得,說也說不通,只能順著來。
無奈之下,他俯著,一本正經地跟江晚解釋:“是這樣,杯子也是需要睡覺的,咱們先回去,回去一樣可以坐著。”
“真的嗎?”
江晚茫然地看了他一眼,似乎在分辨真假。
“真的。”
趁著這一瞬,陸縉俯,一手穿過的膝,試圖將抱起來。
江晚卻不肯,抓住了手邊的青石板:“不行,我會灑出來的!”
“灑不了,我雙手端著你,很穩。”陸縉又添了一只手,攬著后背。
江晚還是不肯:“我很燙的,會燙到你的手,你快松開。”
陸縉拿沒辦法,再抱,眼淚就要漫出來了。
他袖了手:“江晚,你故意的?”
江晚不明白地看著他。
陸縉盯著懵懂的眼看了一會,覺得自己魔怔了。
夜風吹,明月高懸,不遠,遠山重重,鳥鳴深澗。
陸縉規規矩矩的活了二十三年,從未想過自己會有這麼荒唐的一天。
很奇怪,卻也沒什麼不好。
“算了。”
他到底還是低了頭,陪著胡鬧。
站了好一會兒,江晚似乎覺得自己已經涼下來了,手扯了扯陸縉的袖:“我涼好了。”
陸縉的發,準備抱著離開。
江晚攥著他手臂,卻忽然幽幽地來了一句:“你要不要飲我?”
“飲?”陸縉角微勾。
江晚很認真地道:“我很甜的。”
陸縉結一:“你里面裝的什麼?”
“冰糖雪梨。”
江晚想了想,微微啟著。
瓣瑩潤,格外的適合親。
陸縉心念一,單手扣著后腦,緩緩俯。
鼻尖相抵,氣息瞬間大。
他正含住的瓣,江晚卻忽然偏頭,捂著輕嘔了一聲。
陸縉陡然意識到不對。
他極度潔,一貫對各種可能污穢沾的況敬而遠之。
他眉間一凜,迅速握住江晚的肩推開。
然到底差了一步——
袖口忽然一熱。
陸縉頓時手臂僵直,緩緩抬起頭,面沉如水。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730 章

報告王爺,王妃又在裝柔弱
聽說,容王殿下點名要娶太傅府的那位花癡嫡女,全城百姓直言,這太驚悚了! 這幾個月前,容王殿下不是還揚言,要殺了這個花癡嗎? 太傅府,某花癡女看著滿滿一屋的聘禮,卻哭喪著臉,“來人啊,能不能給我退回去?” 京城貴女們紛紛爆起粗口,“你他媽要點臉!”
130.7萬字8.64 2426690 -
完結815 章
暴君他綁定了讀心術
穿成了瑪麗蘇小說里大反派暴君的炮灰寵妃,司玲瓏告訴自己不要慌,反正暴君就要狗帶了。 卻不想,暴君他突然綁定了讀心術。 暴君要殺女主自救,司玲瓏內心瘋狂吐槽,【狗皇帝快住手,這是女主!】 司玲瓏替受傷的暴君縫傷包扎,暴君夸她手法正宗,卻聽她內心得意,【那必須的,咱是專業獸醫!】 夜里,司玲瓏睡不著在腦內唱歌,忍無可忍的暴君直接將人攬進懷里。 “閉嘴!再吵就辦了你。” 司玲瓏:……我都沒出聲!
95.2萬字8.33 12726 -
完結1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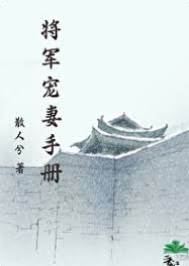
將軍寵妻手冊
雲府長女玉貌清姿,嬌美動人,春宴上一曲陽春白雪豔驚四座,名動京城。及笄之年,上門求娶的踏破了門檻。 可惜雲父眼高,通通婉拒。 衆人皆好奇究竟誰才能娶到這個玉人。 後來陽州大勝,洛家軍凱旋迴京那日,一道賜婚聖旨敲開雲府大門。 貌美如花的嬌娘子竟是要配傳聞中無心無情、滿手血污的冷面戰神。 全京譁然。 “洛少將軍雖戰無不勝,可不解風情,還常年征戰不歸家,嫁過去定是要守活寡。” “聽聞少將軍生得虎背熊腰異常兇狠,啼哭小兒見了都當場變乖,雲姑娘這般柔弱只怕是……嘖嘖。” “呵,再美有何用,嫁得不還是不如我們好。” “蹉跎一年,這京城第一美人的位子怕是就要換人了。” 雲父也拍腿懊悔不已。 若知如此,他就不該捨不得,早早應了章國公家的提親,哪至於讓愛女淪落至此。 盛和七年,京城裏有人失意,有人唏噓,還有人幸災樂禍等着看好戲。 直至翌年花燈節。 衆人再見那位小娘子,卻不是預料中的清瘦哀苦模樣。雖已爲人婦,卻半分美貌不減,妙姿豐腴,眉目如畫,像謫仙般美得脫俗,細看還多了些韻味。 再瞧那守在她身旁寸步不離的俊美年輕公子。 雖眉眼含霜,冷面不近人情,可處處將人護得仔細。怕她摔着,怕她碰着,又怕她無聊乏悶,惹得周旁陣陣豔羨。 衆人正問那公子是何人,只聽得美婦人低眉垂眼嬌嬌喊了聲:“夫君。”
17萬字8.33 5690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