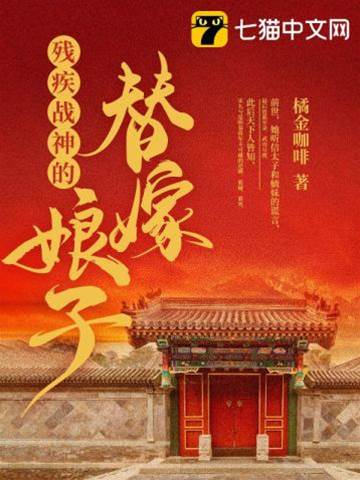《嫁給奸雄的日子》 第40章
第40章 懷抱
傅煜顯然沒這等自覺, 甚至角不知何時了點笑意。
眼神亦帶著溫度,粘在攸桐臉上。
屋裡燈燭昏黃,坐在桌畔, 上是一襲海棠紅的立領寢, 每一粒盤扣都系得牢固。滿頭青晾得半幹, 墨緞般披在肩上, 漆黑的頭髮襯著白膩的,比素絹勾勒的水墨還好看。
那雙帶點詫異的妙麗眉眼低垂下去,姿態旖。
而秀致的臉頰, 不知是何時攀上了可疑的微紅,白的耳廓梢也染了暈紅。
傅煜心領神會, 卻不聲, 隻緩步走過去。
「怎麼,不想去赴宴?」他又問。
「沒, 我等的就是這請帖。」攸桐埋頭, 看著他趿著鞋走過來, 寢輕晃。眼皮微抬, 看到傅煜前的寢仍敞著,走得近了,燭火晃了下,他腹實的廓被照得清晰分明, 縱橫的紋路瞧著邦邦的, 似蓄滿了力道。
不愧是令人聞風喪膽的戰神悍將, 這容貌材, 嘖嘖。
攸桐幷非青燈古佛心如止水,擔著夫妻的名聲共一室,他滿熱氣,只穿了寢,沾著未幹的水珠,這著實容易人心猿意馬。好在不是令智昏的人,這男人深沉難測,又心高氣傲,律己自持苛刻,待人也未必寬厚,他背後的傅家更是規矩束縛、眷難纏,想起來就人頭疼。
渾上下,除了那鐵腕,傅煜大概也就只剩這一優點了。
看看就好,看看就好。
攸桐眼觀鼻鼻觀心,思緒往佛寺裡逛了一圈,住冒出來的念頭,喝了口茶。
傅煜還不肯走,甚至躬下來,取了那請帖慢看。
他一躬,沒系的寢便兜敞開些,出半幅膛,一一縷都沒遮掩。
Advertisement
男人熱乎乎的氣息,立時將籠罩,目瞥過去,裡面風更是燙人的眼睛。
攸桐簡直想喊救命,躲逃一般站起,偏頭對著他,狀若無事地道:「徐淑做賊心虛,抵死不肯承認從前造謠的事。不過在留園時,我曾提到,要和睿王幫我洗清上的髒水。這宴席是絕佳的時機,我很想去。」
「好。」傅煜沉聲,看著臉頰上愈染愈紅的顔,眼底都攀上笑意。
攸桐能覺到他的目,如芒在背。
斜眼瞥了瞥,那人仍然沒有穿好裳的意思。
忍無可忍,提醒道:「屋裡沒籠炭盆,穿好裳,當心著涼。」
「唔。」傅煜垂目看了看寢,用一種近乎無辜的聲音說道:「盤扣鬆了。」
攸桐詫然瞧過去。方才的目被裡頭腹勾著,幾乎沒留意寢,此刻細瞧,果然看到盤扣鬆垮垮地吊在哪裡,對面的扣環也鬆了一半。也不知道傅煜究竟怎麼睡覺得,一樣用細綫著的盤扣,這兒牢固結實,他卻穿了那樣!
不過,這也算是這名義上的夫人疏忽了。
攸桐沒辦法,只好向帳外道:「春草,拿笸籮來。」
春草應命送進來,傅煜卻忽然踱步走向床榻,背朝著們,只留個後腦勺。
攸桐有種扶額的衝。
……
婚小半年,對傅煜此人,攸桐如今也有了點淺的瞭解。
在外是威風凜凜的兵馬副使,手腕狠厲,鐵騎所向披靡,行事嚴毅端肅,齊州外無人敢攖其鋒芒。到了宅,才會流出些小心思——譬如在吃火鍋時將蝦藏起來慢慢吃,譬如在被拂了臉面後故意威脅嚇唬,譬如此時掉頭朝,顯然不肯讓外人瞧見寢裡的膛。
Advertisement
攸桐無法,只好讓春草穿好針綫,再退出去。
簾帳垂落,屋裡只剩夫妻獨對。
攸桐拿著針綫過去,想讓傅煜把裳下來,轉念一想,傅煜寢裡估計只穿了,若這會兒個,氣氛怕是要尷尬到極致了。遂打消這念頭,隻提醒道:「夫君坐吧,我先上,湊合著用,明兒再人拿去換個新的。」
傅煜回過神,瞥一眼,「湊合著用?」
「能耐有限,慚愧。」攸桐厚著臉,揪住他寢,慢慢補。
傅煜便站在那裡,敞了領,任由擺弄。
兩人離得近,將青披散在肩,垂首在他跟前,認真補的姿態曼妙。也不知沐浴時用了哪種香湯,發間清香幽淡,很是好聞。
傅煜忍不住,輕嗅了一口。
這靜沒能逃過攸桐敏的耳朵,怕氣氛尷尬,著頭皮想輒,很快就有了話題。
「十六那日設宴,若是太過突兀,未必能旁人信服。我聽說過兩日城外的金壇寺有祈福法會,每年都有許多宦和公侯府邸的人過去,也有百姓進香。不如咱們先邀睿王往那裡走一趟,先傳出點風聲。京城裡嚼舌的人不,事兒傳出去,等睿王府設宴時,旁人有意打聽,這事兒就能事半功倍了。」
說完時,手底下也蛛網般倉促好了盤扣,便拿銀剪剪斷,抬頭道:「夫君覺得如何?」
傅煜不置可否,隻調侃道:「倒是煞費苦心。」
「爲這些誣陷的駡名,我沒苦。既要洗清,自然該徹底乾淨,比潑髒水時還熱鬧。」
正當妙齡的人盈盈立在紅綃帳旁,眉眼麗婉轉,眼波天然妖嬈,言語神裡,卻著勢在必得的決然。無端讓人想起那回在壽安堂時,跟青竹般站著,不張揚鋒銳,也不卑屈退,外而剛。
Advertisement
在齊州的是非驟然涌上心頭,的委屈,他都知道。
當時無意於攸桐,這些事便不上心,留自去置。
如今心思漸被羈絆牽繫,回想彼時形,卻覺心疼歉疚。
在遠嫁齊州之前,行走在京城,上背負著滿城污蔑議論、指指點點時,又是何等難熬?被人捨棄、背叛、算計,那些槍舌劍、損挖苦,落在年方十四的上,未必就比戰場上的槍林箭雨好扛。
傅煜十年戎馬,決斷剛,手上債累累,從不知心是何滋味。
此刻,瞧著窈窕卻單薄的影,心裡卻有種異樣的滋味涌起。
他眸漸漸深濃,等攸桐放好笸籮,回到榻邊準備歇息時,忽然臂攬住。很突兀的擁抱,他勾著按在口,默不作聲,作也不重。
攸桐毫無防備地撞進他懷裡,那位還沒系領,的臉蛋過去,雙穩穩親在他的膛。寬厚卻不算冷的,帶著炙熱滾燙的溫度,連同男人雄健的氣息,排山倒海般撲過來,幾乎能令人溺斃。
腦子裡嗡的一聲,足足楞了兩息,才察覺此舉不妥。
臉上熱意遽然涌來,像是被爐火烤著,幾乎令滿面通紅。
攸桐從他懷裡逃出來,漂亮的眼睛跟小鹿似的瞪著傅煜,懊惱而不解。
兩人大眼瞪小眼,氣氛有點微妙。
傅煜鐵錚錚的悍將,心高氣傲地活了二十年,不近、挑剔苛刻,更不曾對誰過。他也不明白方才發的哪門子瘋,乾咳了一聲,多年養的冷令他沒法解釋方才複雜的心緒,跟對視了片刻後,才著頭髮道:「好香。」
這理由來得莫名其妙。
攸桐覺得他在說謊,卻猜不他剛才忽然反常的緣故。
Advertisement
沒經歷過這般形,只覺氣氛曖昧而古怪。四目相對,似乎從傅煜眼底捕捉到些許類似溫的東西,心跳得有點快,不知是驚慌還是爲何。總之腦子裡糟糟的,充斥著傅煜的膛、氣息、眼神、材……沒法冷靜思考!
攸桐傻站了片刻,才負氣道:「睡了!」
而後沒理會傅煜,踢開珠鞋爬到榻上鑽進錦被裡,裹著屬的那半邊,面朝裡躺下。
傅煜瞧著那明顯氣哼哼的後腦勺,慢慢系上盤扣,而後熄了燈燭睡在旁。
覺得,他好像得罪了。
……
攸桐是次日清晨才察覺端倪的。
昨晚被傅煜那突兀的擁抱衝昏頭腦,上榻後都沒敢,鴕鳥般藏著腦袋。
好在傅煜也自察覺舉止欠妥,沒。
相安無事地睡了一晚,今晨他很早就起了,那件該死的勾曖昧的寢換下來扔在榻上,倉促的蛛網般的綫頗爲醒目。攸桐到底擔負著夫人的職責,想叮囑春草拿去補,話沒出口,清晨剛睡醒、頗爲清醒的腦子裡,忽然閃過一個念頭——
好端端的,寢的扣環怎會磨斷?
傅家雄踞齊州,雖不像皇家奢靡鋪張,起居用卻都是上等的,沒人敢疏忽。
尤其是傅煜這心和份,誰敢怠慢?
這寢是周姑親自盯著人做好了送來的,周姑心細如發,若當真有瑕疵,哪會送到傅煜面前?旁的盤扣都完好無損,就那兩顆半殘綫,傅煜又不在睡覺時撕扯寢玩,哪能到磨斷綫的地步。
想來想去,攸桐總覺得,這盤扣是傅煜故意弄斷的。
思及昨晚他故意敞著膛,到跟前晃來晃去的樣子,攸桐更是有了八分篤定。
像是那晚他借酒遮臉,將困在榻上時一樣,逗玩!
這猜測愈來愈清晰,攸桐咬了咬牙。
深更半夜的,捉弄人很好玩嗎!
鼓著腮幫,將那寢狠狠瞪了會兒,才負氣地摔在榻上。
既是故意扯斷的,便湊合用著吧,懶得給他修補了!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451 章

醫判
【医生+探案】【双C冤家】在山里养病十年的叶四小姐回家了,所有人都在等她的笑话。才子郭允肯定要退婚了,毕竟叶四小姐蠢丑。叶老太爷要撵她父女,因为不养闲人。叶家虎狼们准备“吃”了她,解决分家产的孽障。可怎么着,要退婚的求婚了、撵人的变黏人的、孽障反吃了虎狼了呢?“有不服的?一起上!”叶四小姐道。沈翼打量叶文初:“给我治病的神医,是你吧!”“您有证据吗?没有的话咱们就继续谈生意好吗?”叶文初道。
122.2萬字8 42476 -
連載1915 章

王爺,聽說你要斷袖了!
傳聞,冥王殿下戰功赫赫,殺人如麻,令人聞風喪膽!傳聞,冥王殿下長相絕美,乃是東陵國第一美男子!傳聞,冥王不近女色,有斷袖之癖,看上了蘇家廢材大少爺!都說那蘇九男生女相,卻是個又軟又弱,任打任罵的廢物。只見某人搖身一變,恢復女兒之身,傾國之姿...
196.5萬字8 29382 -
完結52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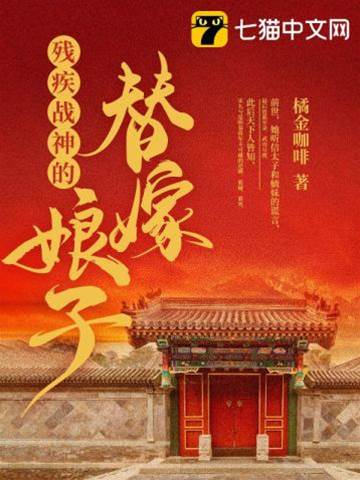
殘疾戰神的替嫁娘子
【重生+男強女強+瘋批+打臉】前世,她聽信太子和嫡妹的謊言,連累至親慘死,最后自己武功盡廢,被一杯毒酒送走。重生后她答應替嫁給命不久矣的戰神,對所謂的侯府沒有絲毫親情。嘲笑她、欺辱她的人,她照打不誤,絕不手軟。傳言戰神將軍殺孽太重,活不過一…
97.6萬字8.18 35390 -
完結63 章

長燁無月
【和親公主vs偏執太子】【小短文】將軍戰死沙場,公主遠嫁和親。——青梅竹馬的少年郎永遠留在了大漠的戰場,她身為一國公主遠嫁大晉和親。大漠的戰場留下了年輕的周小將軍,明豔張揚的嫡公主凋零於大晉。“周燁,你食言了”“抱歉公主,臣食言了”——“景澤辰,願你我生生世世不複相見”“月月,哪怕是死,你也要跟朕葬在一起”【男主愛的瘋狂又卑微,女主從未愛過男主,一心隻有男二】(男主有後宮但並無宮鬥)(深宮裏一群女孩子的互相救贖)(朝代均為架空)
20.9萬字8.18 170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