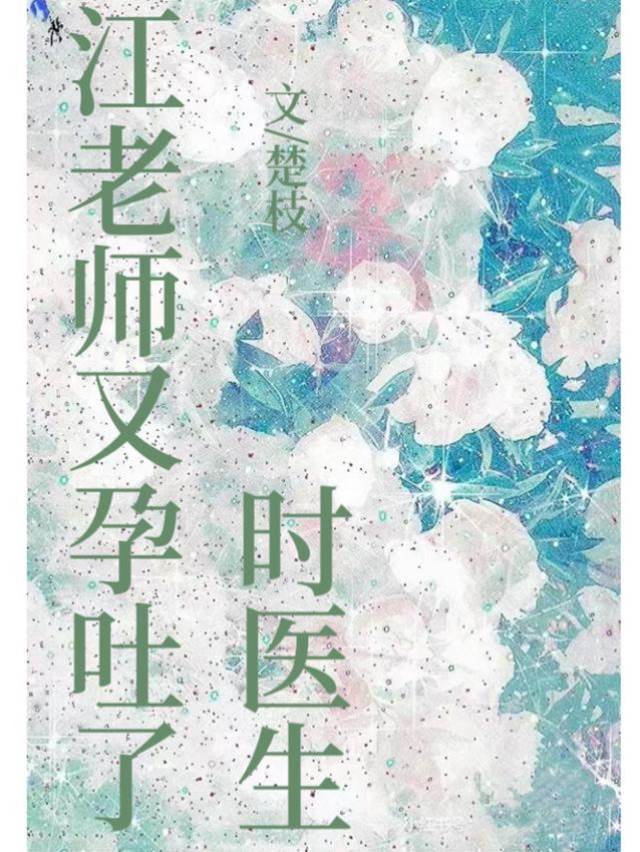《君心》 第 11 節 碎京華
是沈袖。
今日穿著一火紅的勁裝,提著長劍,這打扮看上去,倒是與謝重樓頗為相配。
只是謝重樓一見到,神便冷淡下來:「你怎麼能進我的演武場?關副將,帶出去!」
「謝小將軍有所不知,臣來這里,是皇上的旨意。」
「哦。」
謝重樓面無表道,「既然如此,京郊那麼多演武場,你隨意挑一個就是。我這里不歡迎你。」
他拒絕得直白又不留,沈袖一僵,臉上的笑幾乎要掛不住:
「謝小將軍莫非是覺得我一介流,不配待在你的演武場?連皇上都——」
謝重樓不耐煩地撇下,徑直走到我邊:
「任憑你說破天去,小爺的演武場就是不要人,你若不滿,大可以去皇上面前告我一狀!」
沈袖朝我這邊斜睨了一眼,忽然道:
「謝小將軍,你既說你的演武場不能進人,為何陸姑娘能進來?你這是雙重標準!」
謝重樓沉了臉:
「廢話。你既然這麼想進來,就別想著那幾招花拳繡能打我。來吧,若你能在我手下十招不敗,我就答應你。」
我雖未學過幾天武藝,卻也能看出沈袖無力,招式虛浮,宮宴上的劍舞,也不過幾招花架子。
前世亦是如此,可前世謝重樓卻視如珠似寶,甚至時不時用的武藝譏諷我:
「陸大小姐這種養在閨閣的金雀,又哪里知道巾幗子的颯爽迷人?」
他似乎全然忘記了,我的劍法和馬,還是從前他教給我的。
而如今,謝重樓毫不留的招式下,沈袖毫無回擊之力,兩招便被他反剪雙臂,死死按在了地上。
沈袖惱怒,回頭道:「謝小將軍如此欺負我一介流,就沒有半點憐香惜玉之心嗎?」
Advertisement
謝重樓嗤笑一聲:
「你親口在皇上面前說,你不比那些花玉般的閨閣子,自己說過的話都不記得了?」
「你要上戰場,莫非指北羌人也對你憐香惜玉一番?」
沈袖咬著,楚楚可憐地仰起頭,低聲說了些什麼。
那一瞬間,我心中忽然涌上奇怪的不安,下意識往過走了幾步。
接著便聽到了謝重樓不掩驕傲的聲音:
「我謝重樓追回心上人,從來正大明,還需要你所謂的刺激?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沈小姐。」
9
從演武場回去,是謝重樓送我的。
離開前我掀開車簾看了一眼,沈袖正提劍站在門口,目奇異地向我過來。
我形容不出的眼神,只覺得輕蔑之中,又帶有一高高在上的憐憫。
正心下不安之時,謝重樓卻手過來握住我,挑眉:「昭昭,不必理會無關要的人。」
這一世不知為何,他好像對沈袖一點興趣都沒有,與前世在我面前極盡所能維護的行徑截然相反。
大概是前世的五年折磨太過刻骨,縱然現實并非那般,縱然謝重樓也說那只是夢,我卻仍覺不安。
也不知該如何面對謝重樓,只好默默從他邊挪開。
他眸一暗,有些然道:「陸昭懿,你真要為那樣一個虛無縹緲的夢,就徹底冷落我嗎?」
回府后,母親瞧出了我緒不佳,提出三日后去城外若華山上的金陵寺祈福進香。
結果不知誰走了風聲,到那日,我又在金陵寺門口遇上了謝重樓。
扭頭去,母親著我:
「昭昭,我先同太師夫人去廂房用些素齋,你們若是說完了話,只管過來找我。」
我與謝重樓之間的奇怪氛圍,想必都看在眼里,才想了這樣一個辦法。
Advertisement
謝重樓迎上來,規矩行禮:「請伯母放心,我定然會將昭昭照顧妥帖。」
等母親離開,他從懷中取出一支煙紫的翡翠發簪,遞到我手里:
「深秋已至,春海棠難尋,我便雕刻了一支送你。」
我低頭看了看:「這是你親手雕的?」
「對啊。」謝重樓說著,低咳一聲,「我知道你也學過一些金玉雕刻之,大可評價一番,實話實說就是。」
既然他這麼說了,我也只好再細細打量一番,然后誠實道:
「雕工淺,行刀過度,上好的春翡料子卻……」
「陸昭懿!」
話沒說完,謝重樓已經不滿地盯著我,著重強調了一遍,
「這是我跑遍京城尋來的料子,一整夜才雕刻完。」
「……但心意難得,細看便覺
春海棠栩栩如生,實乃世間凡品。」我只好轉了話鋒。
謝重樓顯然滿意了,手接過簪子就往我發髻上:「既然你這般喜歡,我現在便為你戴上。」
他溫熱的指尖拂過我鬢邊,又輕輕掠過耳尖。
那像是落在心上的羽,一陣麻,我忽然臉紅發燙。
說話間,我們已經并肩穿過金陵寺中庭那片梨花樹林,來到后殿。
眼前線驀然和,繚繞在鼻息間淡淡的檀香味,讓我不安的心忽然沉靜下來。
坐在玄塵大師對面,我恭敬施禮后,便聽到他的聲音:
「施主心有疑慮,卻又不知何解,故而終日憂心。」
他雙手合十,沖我微一低頭,「紅塵紛擾,人心卻可貴。施主大可遵從本心,此局便也可破。」
「可我從前遵從本心,卻將自己陷囹圄,上了絕路。」
「那施主可知,你既已到了絕路,又為何還能到這里來?」
Advertisement
玄塵大師緩緩睜眼,目慈和卻平靜,
「人心易變,人心卻也最不易變。此局不比從前,置之死地而后生,方得云開月明。」
我謝過玄塵大師出去,謝重樓在門外等我。
「那老和尚同你說了什麼?」
「他讓我遵從本心。」我見他神并不好看,不由多問了一句,「他又跟你說了什麼,你不開心嗎?」
謝重樓瞇了瞇眼睛,桀驁道:「他讓我不必執念太深,有些事有緣無分。」
「……然后呢?」
「然后我將他臭罵了一頓,告訴他這種事由我心,既不由緣分,更不由命。」
果然是謝重樓這樣的格會做出來的事。
他從不信神佛。
我輕輕嘆了口氣:「或許他說得對,你是執念太深,退一步也沒什麼不好——唔!」
一聲驚呼,是謝重樓扣著我的手腕,將我按在了后涼亭的柱子上,目結一抹旖:
「退一步——陸昭懿,我從十二歲起就日日盼著娶你過門,現在你讓我退一步,讓我莫名其妙放棄?」
「我說了,那只是你的夢!我什麼都沒做過,你卻因為一個夢就給我判了死刑,可曾想過是否對我公平?」
說到最后,他眼尾微微發紅,嗓音里也裹挾了一輕微的抖。
心尖延綿不絕的痛泛上來,我張了張,發現自己幾乎發不出聲音。
我又何嘗不知,這樣的冷落對于什麼都不知道的謝重樓來說,并不公平。
可那并不是夢,那是我親經歷過的五年。
一千多個日夜,如同鈍刀一點點裁下我心頭十六載的熱切。
那種模糊的痛,至今想起來,依舊心有余悸。
我深吸一口氣,抬眼著謝重樓,緩緩道:「如果,那不是夢呢?」
Advertisement
10
他神驀然一凜。
我卻短短一瞬就卸了力,無奈地著額頭:「罷了,你只當我在胡說八道。」
氣氛安靜片刻,一時間,掠過我們耳畔的只有風聲。
「你夢中除了我們與沈袖,旁人呢?」
謝重樓忽然又問我,
「倘若我真要與你退婚,我爹娘第一個不同意。你夢里的他們呢?」
他們……
謝伯父謝伯母,在我嫁過去不到一年時,便雙雙病逝。
臨行前,謝伯母還握著我的手,低聲說:
「昭昭,你不要太難過了。不知為何,我一直覺得,自那日提出退婚后,重樓便也不再是我的孩子了。」
「如今我要去了,你便只當他跟我一同去了吧!」
我把前世的這些都告訴了謝重樓,他聽完,沉默片刻,篤定地告訴我:「我娘說得對。」
「昭昭,縱使傷了自己,我也不舍得傷你分毫,更不會做出那樣的事。」
「除非你夢里那個人,本就不是謝重樓。」
說完這句話,他低頭凝視我的眼睛,然后著我的下,吻了上來。
這個吻溫但熱烈,是前世婚五年,我也未從謝重樓那里得到的。
我揪住他襟,嗓音發:「……謝重樓,這是佛門凈地。」
「我不信神佛,更不信天命。」
他退開了一點,仍然在很近的地方盯著我,
「但我相信心意不可變,相信人定勝天,相信——只要你不放開我,那個夢,無論如何我都不會令它真。」
后來山間零零落落下起小雨,他將我一路送到廂房,與母親相會,又拒絕了母親的邀請,不撐傘便往山下走。
走了兩步,謝重樓忽然停住,轉頭向我:
「西南邊陲,圣上已下旨命我帶兵平——昭昭,我去給你掙誥命了,等我回來,我就去請旨重新賜婚,好不好?」
這道嗓音,奇異地與四年前年跪在雪地里的承諾相合。
我難以抑制心頭悸,倚著走廊用力點頭,也莊重應聲:「好!」
可隔著雨簾,一團模糊里,我卻始終無法看清謝重樓的眼睛。
他走后不足半月,西南便有捷報頻頻傳出。
父親上朝回來時總會帶些消息。
例如他不慎中了埋伏,千鈞一發之際被一小兵所救,已將對方提為副將。
寥寥幾語,聽上去已經足夠驚心魄。
我握著篆刻刀,細細雕刻著手里的長簪,想等謝重樓凱旋之日送給他。
日子流水般過去,我想或許前世種種不過大夢一場。
而我與謝重樓的婚事,也會如我從前無數次幻想的那樣,順順利利地進行下去。
就在這時,父親告訴我,他要班師回朝了。
那一日是初冬,京中飄著細碎的雪花。
我系著滾白的艷紅斗篷,發間著謝重樓送的春海棠發簪,站在城門外等他。
小織勸我在馬車等,我搖搖頭:「也不算太冷,就在外面等著吧。」
臨近午時,遠遠的有兵馬越走越近,我不知怎麼的,忽然想起——
前世,似乎就是這一日,謝重樓來太傅府提了退親。
下一瞬,兵馬最前方,一匹四蹄踏雪的烏黑駿馬馱著兩個人直奔過來。
馬蹄踏雪,濺起細碎的白。
我一瞬間如墜冰窟。
坐在前面一襲藍、腰佩長劍的,是神采飛揚的沈袖。
而后,用斗篷將攬在懷中,目冰冷又漠然地向我掃過來的年,正是謝重樓。
11
馬在我面前驀然停住,高高揚起前蹄。
我躲也不躲,只是定定瞧著謝重樓。
未從我臉上看到驚慌與悲,他似乎有些意外,沖我挑了挑眉:「陸大小姐,你在等誰?」
「自然是等你。」
不等謝重樓答話,他前的沈袖已經輕笑一聲,向后靠了靠,姿態親昵:
「陸姑娘既然與謝將軍退婚,你們之間便再無瓜葛。你自去尋你的良人,怎麼又來糾纏舊?」
眼里是藏都藏不住的自得。
我攏了攏披風,安靜道:「這是我和謝重樓的事,與你何干?」
「當然與我有關,我在西南戰場救他一命,謝將軍打算以相許,來回報這份救命之恩呢。」
前世的記憶里,這分明是該一年后發生的事,如今卻提前了如此之久。
我腦中有什麼東西一閃而過,卻快得令人捉不住。
「你是這麼想的嗎,謝重樓?」
我不再看沈袖,只將目落在謝重樓上,他側頭看了沈袖一眼,眼中萬千:
「阿袖的心意,自然就是我的心意。」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350 章
人魚陷落
战术指挥大佬(撒娇白狮alpha)×武力值top呆呆美人突击手(高贵人鱼omega) 两人从前都是研究院的实验体,相依为命但又相互利用。因为一场误会,白狮被人鱼所伤,嘴上嚷嚷着报仇再见时却难以下手,终究还是想要保护他的小人鱼……
84.1萬字8 6879 -
完結1090 章

偏愛
佟言嫁給了周南川,新婚夜被迫大了肚子。她恨他恨得發瘋,拼了命逃離西北,而她不知道,他愛了她十余年,娶她是他費盡心思求來的......佟言:“你的錢給我干嘛?”周南川:“男人的錢不都是給給老婆保管?”“我聽說很多結了婚的女人手里握著錢才有安全感,希望你也能有。”周南川一手摟著她,“你想花就花,我努力賺錢。”
163萬字8 9606 -
完結177 章

帝王恩
柔安是將軍的養女。 將軍老了,彌留之際,將柔安託付給自己的得意門生,信王李邵修。 李邵修是戰場上的殺神,手段狠戾,性子恣睢涼薄。 許多人都怕他,柔安也怕。 老將軍對柔安說,好好跟着信王殿下,他會護她周全。 無助的柔安點頭答應,燭光下含淚的一雙眼睛瀲灩,脖頸低垂成柔軟纖細的弧度。 李邵修是對柔安很好。 以至於後來,誰也不知道,柔安的肚子裏被種上了龍種。 李邵修慢慢摩挲着她的脖頸,強勢低聲哄道:“給我生個孩子。”
27.2萬字8.18 22139 -
完結19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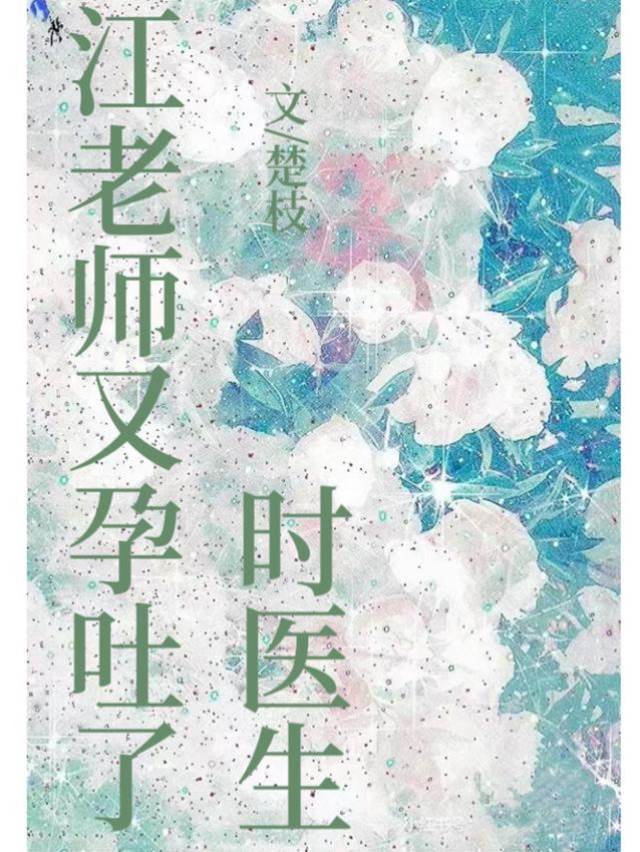
時醫生,江老師又孕吐了
【雙初戀:意外懷孕 先婚後愛 暗戀 甜寵 治愈】男主:高冷 控製欲 占有欲 禁欲撩人的醫生女主:純欲嬌軟大美人 內向善良溫暖的老師*被好友背叛設計,江知念意外懷了時曄的孩子,麵對暗戀多年的男神,她原本打算一個人默默承擔一切,結果男神竟然主動跟她求婚!*江知念原以為兩人會是貌合神離的契約夫妻,結果時曄竟然對她越來越好,害她一步一步沉淪其中。“怎麽又哭了。”他從口袋裏拿出一根棒棒糖,“吃糖嗎?”“這不是哄小孩的嗎?”“對啊,所以我拿來哄你。”*他們都不是完美的人,缺失的童年,不被接受的少數,讓兩個人彼此治愈。“我……真的能成為一個好爸爸嗎?”江知念抓著他的手,放到自己肚子上:“時曄,你摸摸,寶寶動了。”*堅定的,溫柔的。像夏日晚風,落日餘暉,所有人都見證了它的動人,可這一刻的溫柔繾綣卻隻屬於你。雖然二十歲的時曄沒有聽到,但二十五歲的時曄聽到了。他替他接受了這份遲到的心意。*因為你,從此生活隻有晴天,沒有風雨。我永遠相信你,正如我愛你。*「甜蜜懷孕日常,溫馨生活向,有一點點波動,但是兩個人都長嘴,彼此相信。」「小夫妻從陌生到熟悉,慢慢磨合,彼此相愛,相互治愈,細水長流的故事。」
35萬字8 30977 -
完結189 章

雪意昭昭
你聽說過蝴蝶效應嗎,黎枝和宋斯寒的初遇,就像是一場蝴蝶振翅。 黎宋兩家分落京城兩端,王不見王,沒人知道其中真實緣由。 初見宋斯寒,是在香港舉辦的蘇富比拍賣會上。 風吹簾動,斑駁光影之下,眉目英挺,優雅矜貴的男人在黎枝眼前一閃而過。 男人容顏如玉,瀟灑恣意,一擲千金只爲博身旁美人一笑。 他是北歐富人圈裏令人望而生畏的存在。 是名動歐亞的萊昂特私人宅邸,惟一的座上賓。 更是玩弄雪月,縱火芳心的一把好手。 異國他鄉的夜,他隔着雨幕看她,玩世不恭的眉眼裏偏又透着幾許深情,輕易引人沉醉。 迷人的也愈危險。 黎枝不知道他是即將回國接手偌大家業的宋氏太子爺。 硬生生沉溺。 後來一切都在一個雪夜昭然。 宋斯寒隱在濃重的霜靄裏,語含嗤笑,“玩玩而已,有必要當真?” 那一刻,黎枝知道,宋斯寒根本沒有心。 - 那年雪滿望京,黎家老爺子溘然長逝,黎枝三步一叩,孤身前往東郊的寺廟爲祖父祈福。 父親以命逼她,“發誓,再也不見他。” “否則你祖父這輩子都合不上眼。” 寒意刺骨,大雪荒涼,黎枝暈倒在半路上。 後來據人說,是宋斯寒將黎枝抱在懷裏,一步一跪,到了寺廟爲祖父誦經一整夜。 一別兩寬。 黎枝乘了一艘不靠岸的船,漂泊無歸期。 再見面是在蘇黎世舉辦的一場盛宴。 衣香鬢影之間,他一身凜冽黑衣,淨白指骨撐傘而來,爲她遮擋海上飛舞的雨雪。 恍恍然間,兩人好像回到很久以前,初見那日。 她看見他垂着眸子,嗓音於無聲處嘶啞,“阿黎,要不要和我再試一次?” 困住他的,從來都不是家族恩怨。 從始至終,都是她,也只是她。
27.1萬字8 292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