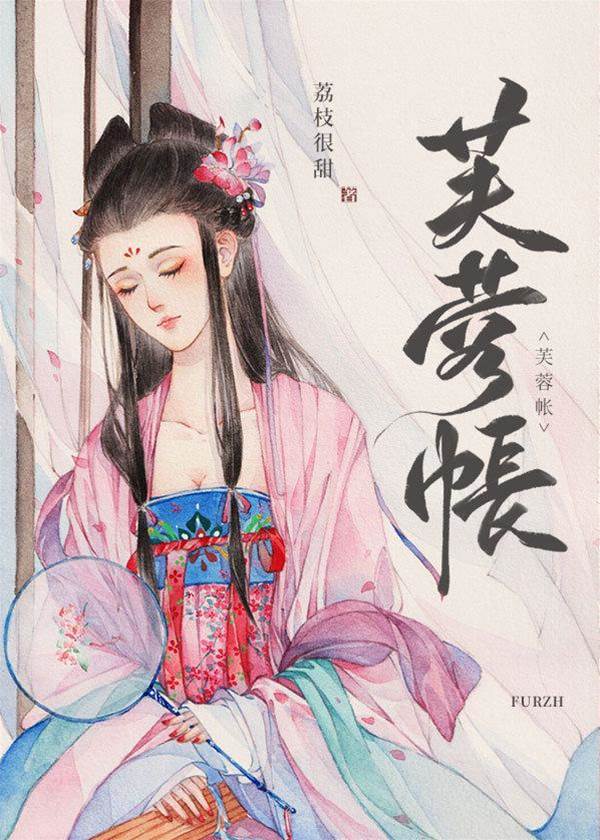《通房寵》 第 6 章
納征后,日子仿佛過得很快,冬后,晝短夜長。
外頭天寒地凍的,屋里卻是溫暖如春,阿梨揣著銅手爐,一邊聽著云潤和香婉在耳邊說著閑話。
阿梨不大出門,一來是沒可去,二來也是因為李玄是個極重規矩的主子,怕是不喜四鉆營。
好在阿梨也是待得住的子,半個月不出門都不覺得悶,很能給自己找樂子。
云潤卻是十分活潑的子,最四找人聊天說話,知道的也多。著肩,將兩只手搭在暖爐上取暖,邊如同小黃鶯一般,里念念有詞,說著柳眠院的趣事。
“昨兒柳眠院那邊靜可大了!聽說二公子從勾欄里帶了個子回來,非要納進門,把侯爺給氣壞了,險些了家法。柳姨娘也給氣病了,大半夜喊了大夫,整個院子人仰馬翻的。不過那子生得是真好看,那雙眼啊,就跟帶了鉤子一樣,那子啊……”
香婉掀了銅蓋,用長銅勺撥了撥碳,笑著打趣,“你又沒見過,怎麼就知道好看了?”
云潤不服氣道,“要是不好看,二公子怎麼挨打也要納進門?”
香婉笑盈盈問,“那是咱們主子好看,還是那姑娘好看?”
云潤想都沒想道,“那自然是主子好看了!我才不信,有誰能勝過主子!主子是我見過生得最的人!”
阿梨原本只懶懶聽著兩人拌,聞言打斷,“云潤,還沒說完呢。”
云潤見主子想聽,忙繼續道,“最后,侯爺和柳姨娘還是拗不過二公子,點頭讓那子進侯府了。”
阿梨聽罷,倒不覺得稀奇,二公子本就是個風流、肆意妄為的子,他做什麼,阿梨都不覺得稀奇。至于柳姨娘,也是個子如命的。
Advertisement
只是,溺子如殺子,柳姨娘遲早有一天要后悔的。
阿梨也就是那麼一想,柳眠院的事,同沒半點干系,倒是另一樁事,同很有些關系。
阿梨垂下眼,盯著那燒紅的炭火,橘紅的火照在的面上,將的臉襯得溫又嫻靜。
香婉和云潤看著這一幕,兩人彼此看了眼對方,不自覺便沒了聲兒。
阿梨算了算日子,自從李元娘征納那日后,快有半個月,李玄都沒來這兒了。
以往也不是沒有這樣的況,刑部有大案的時候,李玄夜夜宿在刑部,十天半個月不回侯府。但這一次顯然不大一樣。
進了十二月,刑部幾乎沒什麼案子,李玄每日都是按時回來的。按照他往日的習慣,每三日來一次,便是那日有事,也會派人來同說一句。
這一回,李玄就像把忘了一樣。
不僅他不來了,也沒派人來傳個話。兩人住在一個院里,半個月下來,愣是連照面都沒打一個。
阿梨前思后想,終于得出了個結論,李玄生氣了。
回憶起那日,李玄側還站了兩人,其中一人,阿梨見過幾面,是侯府大公子李崇。另一人,卻覺得十分眼生,應當不是府里的人。
李玄同人在那兒說話,傻傻闖了進去,打斷了幾人,鬧了笑話,害得李玄失了面。一貫重規矩的世子爺不高興了,便不樂意過來了。
阿梨前前后后一想,勉勉強強猜出這麼個原因來。
都說子的心思不好猜,要說,男子的心思也不遑多讓,尤其是惜字如金的世子爺,更是難上加難。
相通這一出,阿梨也不糾結了。
世子生氣了,能怎麼辦,又不敢晾著這位爺,還不是只能示個好,把人哄高興了,自己才能過個安穩年。
Advertisement
否則那頭侯夫人曉得,自己兒子因著個通房鬧得不快了,怕是又要把喊過去了。
想到這幾日世安院上下關于失寵的風言風語,和在外了冷待還要瞞著的云潤香婉,阿梨心中默默做了決定,抬起頭,輕輕對云潤道,“等會兒送罐桂花去北屋。”
北屋便是正房,也是李玄住的地方。
云潤一怔,忙忍住笑容,大力點頭,“嗯!”
哪里都是如此,拜高踩低,世子爺這才幾日沒來,連膳房那頭都敢欺負們了,取個膳都推三阻四。更別提伺候著全府上下的刺繡房那群老仆婦了,以往姑娘姑娘得親熱,現如今們送了料子去,刺繡房給主子做過年的新,竟連門都進不去了。
可真翻臉比翻書還快。
傍晚,李玄回府,云潤過去送了罐桂花,去的時候惴惴不安,回來時,卻是一臉的笑容。
一進門,香婉就抓著問,“怎麼樣?”
云潤笑瞇瞇,得意洋洋道,“世子爺一聽是主子送的,便我進去了。東西也收下了。”
阿梨溫點了點頭,香婉替梳妝,說是梳妝,都夜了,也沒折騰得太華麗致,只在發上灑了些花,將發攏到前,打了個散散的辮子。
松的黑發散落在前,縈繞著淡淡的梨花香,辮子尾用一枚梨花扣束住,看上去是要睡的打扮,實際上暗藏心機。
阿梨對著鏡子照了照,從鬢角挑出幾縷碎發,微微凌的姿態,恰到好將雪白的面頰和耳垂出來,襯得溫婉乖順。
香婉打開妝篋,問阿梨,“主子要什麼耳飾?”
阿梨挑了一會兒,選了個最簡單的,珍珠耳飾,兩枚圓潤的珍珠,只小米粒大小,“就這個。”
Advertisement
香婉立刻取出來,給阿梨戴上。
珍珠圓潤細膩,夜下燭的照拂下,乍一看并不顯眼,仔細瞧,卻又覺得澤流,勾得人不由得將目落到那泛著的耳垂上。
戌時,院外傳來梆子聲,一慢一塊,連敲了三下,便是落更了。
香婉和云潤兩個眼守在門邊,盼著外頭傳來腳步聲。
倒是阿梨,還安安靜靜坐著。
終于,在兩人焦灼的等待中,影影綽綽的腳步聲隔著木門傳進來了。
敲門聲一響,云潤便立即開了門,屈膝福,“世子。”
阿梨亦走過來,看見李玄在屋外站著,他雙手背在后,長而立,穿著件暗圓領云錦袍,神淡漠,漆黑的眸子猶如深深的寒潭,人一眼不到底。
半月未見,阿梨心里竟也有幾分不合時宜的張,但今日是打定主意要把人哄高興的,下心里那些緒,屈膝,輕聲道,“世子。”
李玄盯著看了會兒,淡淡道,“起來。”
阿梨直起膝蓋,香婉和云潤兩個已經趁機出去了,四下無人,連院子都是空的,只屋檐下的燈籠被寒風吹得直晃。
阿梨穿得單薄,有些冷,微微瑟了一下,纖細瘦弱的肩,在朦朧的燭火下,顯得惹人憐惜。
李玄看在眼里,下意識抬步進了屋,反手將門關上了,隔絕來自屋外的寒風。
這半個月,他是有意冷落的,或者說,更為主要的原因,是要冷一冷自己。
因為他發現,自己對薛梨的寵,似乎超過了那個度,越過了他心里的那條線。
他自小見到的,便是父親武安侯如何寵妾滅妻,將柳姨娘捧得囂張跋扈,母親被得毫無還手之力,武安侯府一片混,規矩盡失。若非外祖家地位擺在那里,他又在陛下面前嶄頭角,世子之位,未必會是他的。
Advertisement
即便如此,旁人只覺得他走運,了陛下的眼,卻不知道,他是如何熬過來的。父親的漠視、母親的忽視、需要他保護的妹妹……一切都是因為父親對妾室的過度寵。
他不會重蹈父親的覆轍。妾便是妾,正妻便是正妻。庶出便是庶出,嫡出便是嫡出。這是規矩,是禮數,若是了,便是帷不治、私德不修。
他絕不允許自己犯這樣的錯,更不允許武安侯府再一次為整個京城的笑談。有違祖宗,更有違他這些年讀的圣言賢語。
對于薛梨,他可以寵,庇佑,給一個容之所,等日后時機合適,再給一個或者幾個孩子。
在此之前,他以為自己做得很好,直到那日,邵昀見到薛梨后滿眼的驚艷和覬覦,讓他起了殺心。
他才意識到,自己對薛梨的占有,似乎超過了對于一個小小通房的程度。
所以,這半個月,李玄一直克制著自己踏足西屋。
直到今日,那罐帶著邀寵意味的桂花,才他打破了自己的原則,沒忍住朝這邊來了。
阿梨瞧見他晦暗不明的神,不明所以,只以為他還在生氣,捧了盞茶,遞過去,沒靠得太近,隔著不遠不近的距離。
李玄回神,看見遞到面前的那盞茶,抬起眼,目落到阿梨攏在前的發,向上移,便是那雙黑白分明的眼,平日里總是帶著溫笑意的眼,此時微微垂著,眼里似是摻雜著細碎的驚慌無措。
李玄心口莫名一滯,心防霎時被擊破了,他心中嘆了口氣,抬手接了過去,隨手擱在圓桌上,朝阿梨沉聲道,“過來。”
阿梨聞聲,稍稍抬起眼,試探著走近了些,下一秒,便被男人拉進了懷里。
男人的下輕輕抵著的發,清冷的聲音,從頭頂的方向傳來。
他道,“怕我?”
阿梨先搖搖頭,繼而又點點頭,偏他抱很,阿梨猶如只小雀兒似的,在他前蹭了蹭腦袋,那子梨花香便漸漸暈開了。
小聲地道,“奴婢上回給世子丟臉了,還以為世子今日也不會過來了。”
李玄心里覺得阿梨笨,又覺得笨得可,口仿佛被這句話,塞滿了鼓鼓囊囊的棉絮,說不上來的滋味。
算了……
李玄心里想,他同一個小子折騰什麼。相一年了,枕邊人是什麼子,他早都琢磨了,溫順無害,猶如一株菟花一樣,離了他,怕是連活下去都難。生著這樣一張臉,子又弱得沒任何攻擊力,出了侯府,沒了庇護,怕是用不了幾日,便被算計得連骨頭渣子都不剩了。
自己刻意冷落,也只知道默默承著,連邀寵都笨得很,眼送一罐子桂花來。
也不想想,他何時吃那甜膩膩的玩意兒了,若不是看辛辛苦苦也只折騰出那幾罐子,他怎麼會吃。
就像自己養的貓,氣又無害,溫順又膽小,從來不敢求什麼,就像只要能待在他邊,便別無所求般。
他都寵了一年了,也沒見驕縱半分,連膳房和繡房那群刁奴,欺負到頭上,都束手無策,毫無反抗之力。
李玄想著,又覺得薛梨的子太溫順了,也不是什麼好事,他的人,被人欺負這樣,他不替撐腰,不護著,能指誰?
.
李玄心中這番念頭,除他之外,旁人自然無法揣測。
即便是阿梨,自認對李玄的子有五六分的了解,也猜不出他此時在想些什麼,估著時機,紅著臉,在李玄的上輕輕了一下。
潤紅的,未涂抹什麼口脂,只一下,便男人立即回過神,對那的,仍有不舍之。
阿梨潤著眼,溫溫順順著李玄,“三爺不要生氣了,我知錯了。”
阿梨很喚李玄三爺,除了在榻上的時候,被得不了時,才會從嗓子眼里出一句支離破碎的、幾不可聞的三爺。
下了榻,阿梨從來都是板板正正、規規矩矩的一句“世子爺”。
也因此,聽到這一句溫順的“三爺”,李玄漆黑的眸子,猶如寒潭中黑龍翻滾般,直視著阿梨,旋即低頭,左手扶住的后腦,不帶一點遲疑的吻下去。
“好。”
阿梨被親得迷迷糊糊,似乎聽到男人說了一句好,又有點懷疑是自己的錯覺。
不過,李玄既然都了,總不至于還為了那點小事生氣吧?
這算是把人哄好了吧?
還……還好哄的……
-

宗門開山之日,無名小伙一舉頓悟混沌體嚇得老祖們紛紛趕來叩拜
-

她崩潰的怒吼:“你不愛我!”他一把將她按在床上:“不愛,孩子哪來的,偷心又偷崽,你還真是膽大包天!”
-

你聽過最浪漫的話是什麼?“今夜雨至,許我愛你。”
-

人人都等著看我成為豪門棄婦,他卻發了條熱搜:不可能離婚,望周知!
-

大婚之夜她捧起毒酒。他嘶吼: “你若敢喝。本王要全天下陪你”她冷笑一飲而盡
-

她重生在花轎里,還被前世冤家搶了親。冤家瞇著陰戾雙眸撂下狠話:你注定只能是我的女人!
-
穆總的霸愛成癮:她是孤兒,他是仇人。究竟十年後的重逢,是結束還是開始?
-
新人辦公室誤發笑話給滅絕師太,險被淘汰!竟被卷入神秘生意,一夜暴富?
-

你一夜之間殺盡同門師兄弟,還把美女師尊煉化成萬鬼幡的主魂。
-

一夜放縱,竟然搞出了人命?!四年後,我帶娃歸來,卻撞見了那個人!
-

身為郡主,前世,我被親哥哥害死。重生後,全家火葬場?
-

我只是在始皇陵發送了一條消息,竟然穿越成了千古一帝——秦始皇!
猜你喜歡
-
完結1814 章
醫妃逆天:腹黑鬼王猛纏妻
她,21世紀的天才鬼醫,一刀在手,天下任她走。一朝穿越,成了宰相府人人可欺的廢材大小姐。 他,鐵血無情的戰神王爺,亦是行走在生死邊緣的黑暗之王,卻因功高震主而被害成殘廢。 一場算計之下,她被賜給雙腿殘廢的王爺,成了整個北齊茶餘飯後的笑料。 初見,她一臉嫌棄:“玄王爺,我爹說你不舉,莫非你軟到連椅子也舉不起來?” 再見,他欺上她的身:“女人,感受到硬度了?” 感受到身下某物的變化,慕容千千嬌軀一顫:“王爺,你咋不上天呢?” 夜景玄麵色一寒:“女人,本王這就讓你爽上天!”
171萬字8 51238 -
完結1833 章

惡後歸來:陛下,娘娘又動手啦!(半支菸頭)
“陛下,娘娘已關在後宮三天了!”“悔過了嗎?”“她把後宮燒完了……”穆王府嫡女重生。一個想法:複仇。一個目標:當今四皇子。傳言四皇子腰間玉佩號令雄獅,價值黃金萬萬兩。穆岑一眼,四皇子便給了。傳言四皇子留戀花叢,夜夜笙歌,奢靡無度。穆岑一言,四皇子後宮再無其他女子。於是越國傳聞,穆岑是蘇妲己轉世,禍害江山社稷。穆岑無畏,見佛殺佛,見神殺神,利刃浸染仇人鮮血,手中繡花針翻轉江山社稷,光複天下第一繡房。眾臣聯名要賜穆岑死罪。四皇子卻大筆一揮,十裡紅妝,後座相賜。後來,世人皆知。他們的後,隻負責虐渣,他們的王,隻負責虐狗。
320.6萬字8 34351 -
完結600 章

娶妃后,我有了讀心術
【異能】大雍十三年六月,雍帝選秀,從四品御史之女顧婉寧,使計想要躲過選秀,原以為計謀得逞能歸家時,其父因扶了當今圣上一把,被賜入六皇子府為繼皇子妃。夫妻二人大婚之后相敬如冰,直到六皇子中了藥被奴才送回正妃院中。隔日,六皇子竟是能聽到別人的心…
110.2萬字8 15504 -
完結12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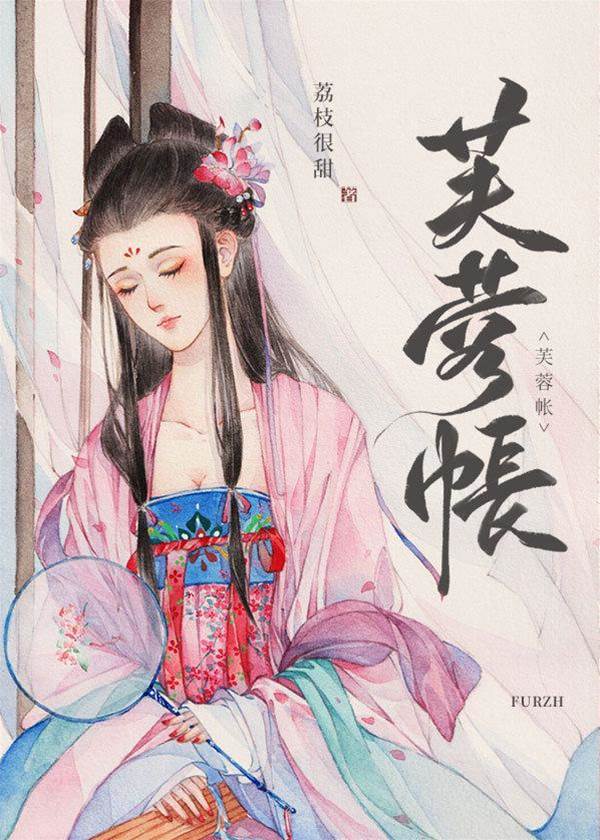
芙蓉妝
文案:錦州商戶沈家有一女,長得國色天香,如出水芙蓉。偏偏命不好,被賣進了京都花地——花想樓。石媽媽調了個把月,沈時葶不依,最后被下了藥酒,送入房中。房里的人乃國公府庶子,惡名昭彰。她跌跌撞撞推門而出,求了不該求的人。只見陸九霄垂眸,唇角漾起一抹笑,蹲下身子,輕輕捏住姑娘的下巴。“想跟他,還是跟我?”后來外頭都傳,永定侯世子風流京都,最后還不是栽了。陸九霄不以為意,撿起床下的藕粉色褻衣,似笑非笑地倚在芙蓉帳內。嘖。何止是栽,他能死在她身上。-陸九霄的狐朋狗友都知道,這位浪上天的世子爺有三個“不”...
37.3萬字8 29264 -
完結191 章

新婚夜,瘋批太子奪我入宮
【強取豪奪+追妻火葬場+瘋狗男主】十六歲前,姜容音是嫡公主,受萬人敬仰,貴不可攀。十六歲后,姜容音是姜昀的掌中嬌雀,逃脫不了。世人稱贊太子殿下清風霽月,君子如珩
34.6萬字8 3881 -
完結121 章

假千金和真少爺在一起了
薛瑛在一次風寒後,意外夢到前世。 生母是侯府僕人,當年鬼迷心竅,夥同產婆換了大夫人的孩子,薛瑛這才成了侯府的大小姐,受盡寵愛,性子也養得嬌縱刁蠻。 可後來,那個被換走的真少爺拿着信物與老僕的遺書上京認親,一家人終於相認,薛瑛怕自己會被拋棄,作得一手好死,各種爭寵陷害的手段都做了出來,最後,父母對她失望,兄長不肯再認她這個妹妹,一向疼愛她的祖母說:到底不是薛家的血脈,真是半分風骨也無。 薛瑛從雲端跌落泥沼,最後落了個悽慘死去的下場。 一朝夢醒,薛瑛驚出一身冷汗,爲避免重蹈覆轍,薛瑛乾脆一不做二不休,重金僱殺手取對方性命。 缺德是缺德了一點,但人總得爲自己謀劃。 誰知次次被那人躲過,他還是進了京,成了父親看重的學生,被帶進侯府做客。 薛瑛處處防範,日夜警惕,怕自己假千金的身份暴露,終於尋到一個良機,欲在無人之際,將那人推下河,怎知自己先腳底一滑,噗通掉入水中,再醒來時,自己衣衫盡溼,被那人抱在懷中,趕來救人的爹孃,下人全都看到他們渾身溼透抱在一起了! 父親紅着老臉,當日便定下二人婚事。 天殺的! 被迫成婚後的薛瑛:好想當寡婦啊。
31.3萬字8 11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